《奥本海默》剧情介绍
当我们为权力金钱焦虑、兴奋与愤怒时,却根本想象不到“他们”在谈论着怎样更重要的事情。 随着战争阴云笼罩世界上空,各国紧锣密鼓抓紧军事竞赛。为了抢占先机,美国陆军中将莱斯利·格罗夫斯(马特·达蒙 Matt Damon 饰)找到量子力学与核物理学领域的扛鼎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基里安·墨菲 Cillian Murphy 饰),力荐其担任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总负责人。经过两年争分夺秒的研发,硕大的蘑菇云终于在荒原的上空腾起,也宣告着绞肉机一般的二战即将落下帷幕。奥本海默有如将火种带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可是对人性的参悟和对未来的担忧迫使他走向与政府相悖的道路。更可悲的是,凡人钟情的物欲也将一世天才裹挟至炼狱之中,永世燃烧……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最强阴阳师的异世界转生记两个女人的故事深入敌后2:邪恶轴心死水死亡录像3:创世纪歌剧魅影阿碧的恩典七木乃伊你并不特别第二个妈妈四重星满月酒芭比之美人鱼历险记2电话亭情缘虫不知九州·天空城2你能原谅我吗?恕不原谅幸福伽菜子的快乐杀手生活断林镇谜案第五季团团奇米莫保姆与保安荡寇风云真相魔法少女毁灭者狐狸小姐不好惹飞常日志反恐特战队之猎影雪国列车金沙血
《奥本海默》长篇影评
1 ) 《奥本海默》观影小指南——历史人物篇
剧透警告(不是)!
看着那么多响当当的历史人物一个个出现,但无奈于有限的高中物理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对白密集,港版翻译也总有与内地不同之处,所以映后自己查的时候,看到《为什么要看《奥本海默》——历史人物与演员篇》已经有了一些介绍,但还没有更全的人物,就干脆写一个小指南,以供想去看的朋友们提前简单了解,也抛砖引玉,希望有大神做更全面的背景与事件介绍。
本文图片多搬运于外网,但较难全部凑齐演员本人、剧中形象和历史影像三者的比较,介绍内容均取自维基百科。
个人整理难免遗漏,有朋友感兴趣的话,请提出宝贵意见,我再进行补充完善。
2023年7月29日,新增几位人物。
2024年1月17日,修改与补充。
感谢评论区诸位豆友的指正。
当时只是简单做了下维基百科搬运工,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与点赞,内容中不免有些遗失与错漏的地方,很是惭愧。
现在各大流媒体已上线,相信有更多的大神做出更准确、更丰富、更精致的资料整理与介绍。
感谢大家的厚爱。
此外还收集了一些事件与地点的资料,欢迎跳转阅读。
《奥本海默》观影小指南——事件与地点篇
朱利叶斯·罗伯特·奧本海默朱利叶斯·罗伯特·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4年4月22日—1967年2月18日),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奧本海默领导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其参与的曼哈顿计划最终研发出用于轰炸广岛与长崎的首批核武器,因此他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战后,奧本海默在新成立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中担任总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利用这一身份游说国际社会对核能进行管控,从而避免美国与苏联发生核军备竞赛以及防止核扩散。
第二次红色恐慌期间,他公开发表的观点激怒了不少政治人士,他的安全许可也因此在1954年被撤销,意味着他无法再直接影响政治。
奧本海默仍继续演讲、写作及研究物理。
九年之后,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授予奧本海默恩里科·费米奖(由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颁发)。
但费米奖的颁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为奥本海默平反,直到2022年12月16日,电影的预告片都已经发布了,美国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下令撤销1954年吊销罗伯特·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才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获得平反。
在物理方面,奧本海默的研究成果包括分子波函数的玻恩–奧本海默近似法、电子和正子理论、核聚变中的奧本海默-菲利浦斯过程以及首次预测量子隧穿效应。
他和学生的共同研究还对现代中子星和黑洞理论、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及宇宙射线相互作用等范畴有重大贡献。
奧本海默作为一名老师,普及科学、一生志业,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建立的伯克利理论物理学中心是数一数二的理论物理学中心。
二战后,他长期担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
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Katherine “Kitty” Oppenheimer、婚前姓氏为普宁(Puening);1910年8月8日—1972年10月27日)是一名德裔美国生物学家、植物学家,也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
在洛斯阿拉莫斯期间,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运用自己的生物学知识,在健康小组中协助主管路易斯·亨佩尔曼进行血液测试,评估辐射的危险性。
小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小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 Jr.,1896年8月17日—1970年7月13日)是美国陆军中将,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领美国陆军工兵部队监督五角大楼建设和领导开发原子弹的绝密研究项目“曼哈顿计划”。
虽然有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提名,但格罗夫斯因考试未能取得够高的分数而落榜西点军校。
他并未放弃,入读麻省理工学院,并计划重新参加西点军校入学考试。
1916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取得及格分数,被西点军校录取。
1918年,他以全班第四名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并获任命为工兵部队的一员。
1929年,他率领工兵部队一连前往尼加拉瓜并勘测跨洋尼加拉瓜运河。
1931年尼加拉瓜地震后,他接手负责马拿瓜的供水系统,为此他获得尼加拉瓜总统功绩勋章。
1941年,他受命为战争部四万名员工建造巨型办公大楼,这座建筑日后被称为五角大楼。
1942年9月,格罗夫斯接管了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除了参与大部分研制工作外,他还选定了数处研究和生产地点,包括田纳西州橡树岭、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华盛顿州汉福德区。
他指挥了巨大的建设工作,在各种同位素分离方法的优先次序和获取科学家和工程师所需的原材料方面作出重要决定,提高计划在获取原材料方面的优先评级,创立阿尔索斯任务收集有关轴心国原子研究的军事情报,并与其他军方高层一同决定应该核打击哪些日本城市。
刘易斯·利希滕斯坦·施特劳斯刘易斯·利希滕斯坦·施特劳斯(Lewis Lichtenstein Strauss ,1896年1月31日—1974年1月21日)是一位美国商人、慈善家和海军军官,曾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任职两届,第二届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他是核武器发展、美国核能政策和美国核电发展的重要人物。
作为冷战初期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创始委员,施特劳斯强调有必要保护美国的原子机密,并监控并保持领先于苏联境内的原子发展。
因此,他是发展氢弹的坚定支持者。
在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主席期间,施特劳斯敦促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预测原子能将使电力“太便宜而无法计量”。
与此同时,他刻意淡化了放射性尘埃可能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例如布拉沃城堡热核试验后太平洋岛民所经历的情况。
施特劳斯是 1954 年 4 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人员安全委员会举行的备受争议的听证会的推动者,在这次听证会上,物理学家J.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因此,施特劳斯经常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恶棍。
1959 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施特劳斯担任美国商务部长,这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开政治斗争,但施特劳斯的任命并未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
琼·弗朗西斯·塔特洛克琼·弗朗西斯·塔特洛克(Jean Frances Tatlock,1914年2月21日—1944年1月4日)是一位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内科医生。
她是美利坚合众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党刊《西部工人》记者、撰稿人。
她还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计划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J. 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的浪漫关系而闻名。
塔特洛克是著名古英语学家、杰弗里·乔叟研究专家约翰·斯特朗·佩里·塔特洛克的女儿,毕业于瓦萨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并在那里学习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
塔特洛克于 1936 年开始见到奥本海默,当时她还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奥本海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教授。
由于他们的关系以及她的共产党身份,她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她的电话也被窃听。
塔特洛克患有严重抑郁症。
1944年1月5日下午1点左右,她的父亲来到她位于蒙哥马利街1405号的公寓。
按门铃无人回应,他便从窗户爬了进去,发现塔特洛克躺在浴室的一堆垫子上,头浸在半满的浴缸里。
有一封未署名的遗书,内容如下:我恨透这一切了......对于爱过我、帮助过我的人,向你们致以我全部的爱与勇气。
我想过活命,想过奉献,但不知为何,我麻木了。
我用尽全力去理解,但就是不能够......我觉得我会为自己的整个人生负责——至少我可以从这个纷扰的世界中卸下灵魂麻木的负担。
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1901年8月8日—1958年8月27日),美国物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
劳伦斯于1930年代初在伯克利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因此获得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劳伦斯于1931年创立了加州大学放射实验室,该实验室后来更名为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并由此开创了由大型研究团队开展大科学研究的模式。
曼哈顿计划期间,基于回旋加速器,劳伦斯又发明了电磁型同位素分离器(Calutron),该仪器被广泛利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铀浓缩。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伯克利的化学家共发现了16种化学元素、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第97号元素锫(Berkelium)以伯克利命名,103号化学元素铹(Lawrencium)即以欧内斯特·劳伦斯命名纪念。
著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是欧内斯特·劳伦斯在伯克利的博士研究生。
鲍里斯·西奥多·帕什鲍里斯·西奥多·帕什( Boris Theodore Pash,原名鲍里斯·费多罗维奇·帕什科夫斯基,1900年6月20日—1995年5月11日)是一名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官员。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帕什科夫斯的父亲是西奥多·帕什科夫斯基牧师(1934 年至 1950 年成为大都会提奥菲勒斯大主教),一位俄罗斯东正教牧师,于 1894 年被教会派往加利福尼亚州。
1906 年,他的父亲被召回俄罗斯。
1916 年至 1917 年,父子俩加入了俄罗斯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西奥多作为一名军事牧师,16 岁的鲍里斯作为一名炮兵列兵。
俄罗斯革命期间, 1918年至1920年,他在黑海白军服役,对抗布尔什维克。
1920 年 7 月 1 日,他与在布尔什维克巩固权力的情况变得明显时选择返回美国。
1940 年,帕什应征入伍,并成为位于旧金山要塞的第九军地区总部的反情报主管。
他负责在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调查涉嫌苏联间谍活动。
他审问了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内的工作人员,他得出的结论是“可能仍然与共产党有联系”。
帕什不相信奥本海默是间谍。
他认为奥本海默的个人荣誉和对自己声誉的担忧会阻止他采取这种行动。
因此,帕什并不建议奥本海默退出曼哈顿计划,只是建议奥本海默由反情报特工陪同。
大卫·希尔大卫·希尔 (David L. Hill,1919年11月11日—2008年12月14日) 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于 1942 年毕业。
随后,他被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Met Lab”)聘为副实验物理学家。
他在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 (Enrico Fermi) 的指导下工作直至 1946 年,为曼哈顿计划做出了贡献。
1942 年 12 月 2 日,费米领导的实验成功地在世界上第一个人造核反应堆 CP-1 中实现了自持核链式反应,大卫·希尔是参与人员之一。
希尔也是西拉德请愿书的七十位签署者之一,该请愿书敦促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希尔加入了一个致力于解决原子弹对政治和社会影响的组织。
希尔与该小组领导人小约翰·辛普森 (John A. Simpson, Jr.) 和尤金·拉比诺维奇 (Eugene Rabinowitch) 共同撰写了文章《原子科学家大声疾呼:核物理学家说原子弹不存在秘密,也无法防御它》。
文章强调,科学家有责任确保不再研制原子弹。
1954 年,希尔决定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在加州大学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理论物理部工作。
在此后的五十年间,希尔创建并监管了多家科学研发公司。
希尔于 2008 年 12 月 14 日去世。
享年 89 岁。
尼尔斯·亨里克·达维德·玻尔尼尔斯·亨里克·达维德·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年10月7日—1962年11月18日),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因“他对原子结构以及从原子发射出的辐射的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尔发展出原子的玻尔模型。
这一模型利用量子化的概念来合理地解释了氢原子的光谱。
他还提出量子力学中的互补原理。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量子力学及相关课题研究者的活动中心,哥本哈根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名尼尔斯·玻尔研究所),也是由玻尔在1921年创办的。
20世纪30年代,玻尔积极帮助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者。
在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玻尔与主持德国核武器开发计划的海森堡进行了一次著名会谈。
他在得知可能被德国人逮捕后,经由瑞典流亡至英国,并于该国参与了合金管工程。
这是英国在曼哈顿计划中承担的任务。
战后,他呼吁各国就和平利用核能进行合作。
他参与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及丹麦原子能委员会里瑟研究部的创建,并于1957年成为北欧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首任主席。
为纪念玻尔,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107号元素,𬭛(Bohrium)。
爱德华·泰勒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908年1月15日—2003年9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
泰勒于1930年代移民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并成为曼哈顿计划的早期成员,参与研制第一颗原子弹。
这段期间,他还热衷于推动研制最早的核聚变武器(氢弹),不过这些构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实现。
在一场对于罗伯特·奥本海默背景调查的听证会上,泰勒对这位过去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作出一些具争议性的证词,此后他在科学界中变得不受欢迎。
他持续寻求美国政府与军事研究机构的援助。
泰勒是劳伦斯利福摩尔国家实验室的建立者之一,并于此机构担任多年的主管及助理主管,1959年还主持建立了伯克利空间科学实验室。
泰勒晚年对于一些军事与公共议题,发表了一些具争议性的技术解决方法,其中包括计划在阿拉斯加利用热核爆开凿港口。
他是罗纳德·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之热衷支持者。
泰勒的一生因其科学才能、欠佳的人际关系,以及善变的个性而知名。
此外也被认为是1964年电影《奇爱博士》的灵感来源之一。
罗杰·罗伯罗杰·罗伯(Roger Robb,1907年7月7日—1985年12月19日)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美国巡回法官和审判律师。
1954 年,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的特别顾问,该听证会导致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Frank Friedman Oppenheimer,1912年8月14日—1985年2月3日)是一位美国粒子物理学家、牧场主、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教授、旧金山探索博物馆的创始人。
弗兰克·奥本海默是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他在曼哈顿计划期间进行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并对铀浓缩做出了贡献。
战后,奥本海默早期参与美国共产党使他受到审查,他辞去了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学职位。
奥本海默是麦卡锡主义的目标,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在美国找到任何物理教学职位,直到 1957 年他被允许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所高中教授科学。
1969 年,奥本海默在旧金山创立了探索博物馆,并担任第一任馆长,直至 1985 年去世。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是出生于德国、拥有瑞士和美国国籍的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他创立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的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也是质能等价公式的发现者。
他在科学哲学领域颇具影响力。
因为“对理论物理的贡献,特别是发现了光电效应的原理”,他荣获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22年颁发)。
这一发现为量子理论的建立踏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爱因斯坦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发觉经典力学与电磁场无法相互共存,因而发展出狭义相对论。
他又发现,相对论原理可以延伸至重力场的建模。
根据研究出来的一些重力理论,他于1915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他持续研究统计力学与量子理论,这让他给出了粒子论与对于分子运动的解释。
1917年,爱因斯坦应用广义相对论来建立大尺度结构宇宙的模型。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开始掌权成为德国总理之时,爱因斯坦正在走访美国。
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裔人,所以尽管身为普鲁士科学院教授,他并没有返回德国。
1940年,他定居美国,随后成为美国公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在一封写给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里署名,信内提到德国可能发展出一种新式且深具威力的炸弹,因此建议美国也尽早进行相关研究,美国因此开启了曼哈顿计划。
爱因斯坦支持增强同盟国的武力,但谴责将当时新发现的核裂变用于武器用途的想法,后来爱因斯坦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共同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强调核武器的危险性。
帕特里克·梅纳德·斯图尔特·布莱克特 帕特里克·梅纳德·斯图尔特·布莱克特 (Patrick Maynard Stuart Blackett,1897 年 11 月 18 日—1974 年 7 月 13 日)是一位英国实验物理学家,因其在云室、宇宙射线和古地磁学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于 1948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5 年,他成为第一个证明放射性可以导致一种化学元素核转变为另一种化学元素的人。
他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军事战略提供建议和开展运筹学研究。
威廉·利斯库姆·博登威廉·利斯库姆·博登(William Liscum Borden,1920年2月6日—1985年10月8日)是一位美国律师和国会工作人员。
1949年至1953年担任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执行主任,成为美国政府中最有权势的核武器发展倡导者之一。
博登因写了一封信指控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是苏联特工而闻名,这一指控导致了1954 年的 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
战争期间的两项技术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博登的思维。
其中一次发生在 1944 年 11 月:在向荷兰抵抗组织空投物资后,在荷兰上空执行夜间任务返回时,他看到一枚德国V-2 火箭正在飞往伦敦。
“它就像一颗流星,流淌着红色火花,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就好像飞机一动不动……我开始相信,火箭将使美国遭受直接的跨洋攻击,这只是时间问题。
” 另一次是1945年8月得知日本原子弹爆炸后,他说这对他产生了“电流效应”。
针对奥本海默的行动常常与当时的麦卡锡主义联系在一起。
但博登其实是是一位干预主义、反共的自由民主党人,是共和党约瑟夫·麦卡锡的敌人而非支持者。
肯尼思·大卫·尼科尔斯肯尼思·大卫·尼科尔斯(Kenneth David "Nick" Nichols,1907 年 11 月 13 日——2000 年 2 月 21 日),也被称为尼克,是一名美国陆军军官,也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曾参与秘密曼哈顿计划,该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了原子弹。
他曾担任James C. Marshall的副地区工程师,并从 1943 年 8 月 13 日起担任曼哈顿工程师区的地区工程师。
尼科尔斯领导了田纳西州橡树岭克林顿工程师工厂的铀生产设施,以及华盛顿州汉福德工程师工厂的钚生产设施。
战后,尼科尔斯继续参与曼哈顿计划,直到 1947 年被原子能委员会接管。
1946年至 1947 年,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的军事联络官。
在美国西点军校短暂任教后,他晋升为少将,并成为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负责人,负责原子武器的军事方面,包括后勤、装卸和训练。
他曾担任陆军总参谋部原子能事务、计划和作战部副主任,也是与原子能委员会合作的军事联络委员会的高级陆军成员。
1950年,尼科尔斯将军出任国防部制导导弹司副司长。
1952年重组时,他被任命为研究开发主管。
1953年,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总经理,推动核电站建设。
他在针对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诉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在晚年,尼科尔斯成为私人核电站的工程顾问。
哈康·莫里斯·舍瓦利埃哈康·莫里斯·舍瓦利埃( Haakon Maurice Chevalier,1901 年 9 月 10 日—1985 年 7 月 4 日)是一位美国作家、翻译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文学教授,他因与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友谊而闻名。
1942 年,舍瓦利埃向奥本海默通报了他与乔治·埃尔滕顿的一次讨论,这让他相当不安,并认为奥本海默应该知道苏联试图通过埃尔滕顿渗透曼哈顿计划的情况。
那段简短的谈话、奥本海默迟来的报告以及掩盖舍瓦利埃身份的企图,后来成为奥本海默 1954 年在原子能委员会举行的安全听证会上的关键问题之一,导致他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后,舍瓦利埃于 1950 年失去了伯克利分校的工作,并且无法在美国找到另一个教授职位,因此搬到了法国,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翻译工作。
伊西多·艾萨克·拉比伊西多·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1898年7月29日—1988年1月11日),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因发现核磁共振(NMR)而获得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核磁共振成像(MRI)就是基于核磁共振技术的。
他也是其中一个最早研究多腔磁控管的美国科学家,多腔磁腔管可用于微波雷达和微波炉。
利奥·西拉德利奥·西拉德(英语:Leo Szilard,匈牙利语:Szilárd Leó,1898年2月11日—1964年5月30日),匈牙利裔美国核物理学家、发明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1933年他构想出了核链式反应,纳粹掌权后,他离开了自己长大的欧洲,并于1939年协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史称“爱因斯坦—西拉德信”),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启动。
利奥·西拉德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首席物理学家,1942年12月协助恩里科·费米等人建立了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转向研究生物物理学,并积极推动核能的和平利用、反对使用核武器。
万尼瓦尔·布什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1890年3月11日—1974年6月28日),美国工程师,发明家和科学行政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的负责人,几乎所有的战时军事研发都是通过该办公室进行的,包括雷达的重要发展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启动和早期管理。
他强调了科学研究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福祉的重要性,并敦促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
2021年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通过《无尽前沿法案》(现更名为《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其名称缘起万尼瓦尔·布什撰写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汉斯·阿尔布雷希特·贝特汉斯·阿尔布雷希特·贝特(Hans Albrecht Bethe,1906年7月2日—2005年3月6日),德国和美国犹太裔核物理学家,对于天体物理学,量子电动力学和固体物理学有很重要的贡献。
由于恒星核合成理论研究成果,他获得了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贝特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
他是秘密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理论部门的负责人。
后来,贝特与爱因斯坦和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开展了反对核试与核军备竞赛运动。
他帮助说服肯尼迪和尼克森政府分别签署了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SALT I)。
罗伯特·瑟伯尔罗伯特·瑟伯尔(Robert Serber,1909年3月14日—1997年6月1日)是名美国物理学家,曾参与过曼哈顿计划。
瑟伯尔的一次关于曼哈顿计划基本原理、任务目标的讲演被打印、分发给了全体科学工作者,并被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入门》。
《纽约时报》评价他为“原子弹降生时智慧的助产士”(the intellectual midwife at the birth of the atomic bomb)。
瑟伯尔的妻子夏洛特·瑟伯尔被奥本海默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图书馆的负责人,她是该图书馆唯一的战时女性部门领导。
根据瑟伯尔的回忆录(1998 年),瑟伯尔为所有三个设计项目创建了代号:“小男孩”(铀枪)、“瘦人”(钚枪)和“胖子”(钚内爆)。
这些名称是根据它们的设计形状而定的。
“瘦人”将是一个很长的装置,名字来自达希尔·哈米特侦探小说和同名系列电影;“胖子”炸弹是又圆又胖的,以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在《马耳他之鹰》(来自哈米特的小说)中的角色命名。
)。
“小男孩”将排在最后,其命名只是为了与“瘦子”炸弹形成对比。
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年5月11日—1988年2月15日),美国理论物理学家,以对量子力学的路径积分表述、量子电动力学、过冷液氦的超流性以及粒子物理学中部分子模型的研究闻名于世。
因对量子电动力学的贡献,费曼于1965年与朱利安·施温格及朝永振一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费曼发展了得到广泛应用的亚原子粒子行为的图像化数学表述——费曼图。
费曼在世时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
1999年,在英国学术期刊《物理世界》举办的130位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参与的票选活动中,费曼跻身十大有史以来最伟大物理学家之列。
费曼在二战期间曾参与协助原子弹的开发,而后在1980年代因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而为公众熟知。
在理论物理学研究之外,他还是量子计算领域的先驱,并提出了纳米技术的概念。
他曾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托尔曼理论物理学教授。
费曼热心参与物理学普及事业,为此写过大量书籍并举办讲座。
这其中包括于1959年做的有关自上而下的纳米技术的讲座《底部有的是地方》以及三卷本本科物理学讲义《费曼物理学讲义》。
现在知名的费曼学习法即出自他的理念。
肯尼思·汤普金斯·班布里奇肯尼思·汤普金斯·班布里奇(Kenneth Tompkins Bainbridge,1904年7月27日-1996年7月14日)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家,从事回旋加速器研究。
他对核同位素之间质量差异的精确测量使他证实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质能等效概念。
他是1945 年 7 月 16 日进行的曼哈顿计划核试验的负责人。
班布里奇将核试验爆炸描述为“肮脏而可怕的表演”。
测试结束后,他立即对奥本海默说道:“Now we are all sons of bitches.”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班布里奇仍然是民用控制核电和放弃核试验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
1950 年,他是向哈里·S·杜鲁门总统 请愿声明美国永远不会第一个使用氢弹的12 位杰出科学家之一。
莉莉·霍尼格莉莉·霍尼格(Lilli Hornig,1921年3月22日——2017年11月17日)是一位捷克裔美国科学家,曾参与曼哈顿计划,也是一位女权主义活动家。
霍尼格和她的丈夫一起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最初被要求参加打字测试后,她的科学技能得到了认可,并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一名科学家,在一个研究钚化学的小组中工作。
后来人们认为钚化学对女性来说太危险了,所以她转而从事高爆镜片的工作。
在洛斯阿拉莫斯期间,她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在无人岛上使用第一颗原子弹作为示威。
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霍尼格是 HERS(高等教育资源服务)的创始主任,该服务是由 Sheila Tobias 首次组织的新英格兰学院和大学妇女关注委员会的赞助。
她曾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平等机会委员会任职。
她曾担任哈佛大学妇女平等委员会的研究主席,并咨询并参与了许多有关女性科学教育和职业的研究。
恩里科·费米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1901年9月29日—1954年11月28日),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
他对量子力学、核物理、粒子物理以及统计力学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曼哈顿计划期间领导制造出世界首个核子反应堆,也是原子弹的设计师和缔造者之一,被誉为“原子能之父”。
费米拥有数项核能相关专利,并在1938年因研究由中子轰击产生的感生放射以及发现超铀元素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是物理学日渐专门化后少数几位在理论方面和实验方面皆能称作佼佼者的物理学家之一。
塞斯·亨利·内德迈尔塞斯·亨利·内德迈尔(Seth Henry Neddermeyer,1907年9月16日-1988年1月29日)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介子的共同发现者,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从事曼哈顿计划时倡导了内爆型核武器。
内德迈尔倡导的内爆方法被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胖子投在长崎的原子弹,以及几乎所有现代核武器。
路易斯·沃尔特·阿尔瓦雷斯路易斯·沃尔特·阿尔瓦雷斯(Luis Walter Alvarez,1911年6月13日-1988年9月1日)是一位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发明家、教授,因利用氢气泡室发现粒子物理学中的共振态而获得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与他的儿子、地质学家沃尔特·阿尔瓦雷斯 (Walter Alvarez)一起提出了阿尔瓦雷斯假说,该假说提出灭绝事件消灭非鸟类恐龙是小行星撞击的结果。
维尔纳·海森堡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代表性人物。
1933年,海森堡因为“创立量子力学以及由此导致的氢的同素异形体的发现”而获得1932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又称“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
他的《量子论的物理学原理》是量子力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
海森堡曾经是德国核武器开发计划研制的参与者,不过纳粹德国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力将核武器从理论变为现实。
海森堡本人提供的一种说法称,他其实并不信任希特勒政权,因此在尽力拖延纳粹德国的研究计划。
但曼哈顿计划重要领导人古德施密特等一些人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这也被称之为“海森堡之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和其他德国物理学家作为囚犯,被美国军队送往英国。
1946年重返德国后,他和他的同事们重建了哥廷根物理研究所,该研究所在1948年改名为马克斯-普朗克物理学研究所。
克劳斯·埃米尔·尤利乌斯·富克斯克劳斯·埃米尔·尤利乌斯·富克斯(Klaus Emil Julius Fuchs,1911年12月29日—1988年1月28日),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著名核武器间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美、苏、英三国的核武器研发计划。
1941年受鲁道夫·佩尔斯邀请加入英国原子弹研发计划合金管工程并成为其最信任的助手,同时开始向苏联提供情报。
1943年,他与佩尔斯同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参与曼哈顿计划。
次年8月,他前往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参与原子弹研发,在犹太裔德国物理学家汉斯·贝特手下工作并负责以内爆方式引爆钚芯原子弹(即后来投在长崎的胖子)的多项重要机密计算,也曾参与氢弹的早期理论发展。
二战结束后,他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参与十字路口行动核武试验的准备工作。
1946年8月,返回英国担任英国核能研究机构理论物理部主任参与英国原子弹研发项目。
富克斯于1941-1949年间向苏联提供了包括美、英两国原子弹设计方案、计算方法和大量相关实验数据在内的大量高价值情报,大大缩短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周期。
1945年9月,他向苏联提供了恩里科·费米1943年-1945年间介绍热核武器研究状态的一系列报告的总结。
1947年底至1949年五月,又向苏联提供了美国氢弹研究主要理论架构(恩里科·费米和爱德华·泰勒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和一部分早期草图等情报,以及原子弹测试结果和铀-235浓缩等技术信息。
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称他是自国家诞生以来破坏力最大的间谍。
1949年9月,英美情报机构确认其间谍身份;1950年1月,他向军情五处的调查人员认罪,3月被判四项指控成立,但出于苏联在二战中为英国的盟友而仅被处以14年监禁,但被剥夺英国国籍。
1959年6月提前获释后前往东德定居,供职于东德科研机构。
库尔特·弗雷德里希·哥德尔库尔特·弗雷德里希·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ödel,1906年4月28日—1978年1月14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小组)的成员。
哥德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之一,其最杰出的贡献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连续统假设的相对协调性证明。
哥德尔和爱因斯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一起长途步行往返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他们谈话的性质对研究所的其他成员来说是个谜。
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 (Oskar Morgenstern)回忆道,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坦言,他“自己的工作不再有多大意义,他来到研究所只是……为了有幸与哥德尔一起步行回家”。
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年9月21日—1950年10月20日)。
美国政治家,曾担任美国战争部长、菲律宾总督和美国国务卿。
1929年12月,曾回应中华民国调停中东路事件的请求,谴责苏联违反《非战公约》。
史汀生个人十分反对日军侵华的行为(九一八事变),而美国当时亦宣布不承认日军的行动,即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哈里·S·杜鲁门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是第34任美国副总统(1945年)、第33任美国总统(1945年-1953年)。
露丝·谢尔曼·托尔曼露丝·谢尔曼·托尔曼(Ruth Sherman Tolman,1893年10月9日-1957年9月18日)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教授。
二战期间,她在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担任了两年的舆论分析师(1942-1944)并在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担任临床心理学家(1944-1945),主要职责是评估测试外勤特工的心理稳定性。
尽管她嫁给了理查德·切斯·托尔曼,但据称她与她的好朋友 J·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一直有染。
菲利普·莫里森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1915年11月7日-2005年4月22日)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
他因二战期间曼哈顿计划的工作以及后来在量子物理学、核物理、高能天体物理学和SETI 计划(搜寻地外文明,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方面的工作而闻名。
1940 年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1943 年 1 月加入芝加哥大学的曼哈顿计划冶金实验室,与尤金·维格纳 (Eugene Wigner)一起设计核能反应堆。
1944 年转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他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确定一枚炸弹需要多少钚,他计算出 6 公斤(13 磅)就足够了。
之后,他与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合作研究引爆内爆式核武器所需的爆炸透镜。
莫里森在伯克利就读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他是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少数仍保持就业和学术活跃的前共产党员之一。
乔治·博格丹诺维奇·基斯蒂亚科夫斯基乔治·博格丹诺维奇·基斯蒂亚科夫斯基(George Bogdanovich Kistiakowsky,1900年12月1日-1982年12月7日),乌克兰裔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化学教授。
他在曼哈顿计划中负责开发内爆型核武器所需的爆炸透镜。
1962 年到 1965 年,基斯蒂亚科夫斯基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COSEPUP) 主席。
他获得了多项奖项,包括1957 年荣获空军杰出民事服务奖章。
1961 年,他被杜鲁门总统授予功绩勋章,1961年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授予自由勋章, 1967 年被林登·约翰逊总统授予国家科学奖章。
晚年,基斯蒂亚科夫斯基积极参与反战组织“宜居世界委员会”。
他断绝了与政府的联系,以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爱德华·乌勒·康登爱德华·乌勒·康登( Edward Uhler Condon,1902 年 3 月 2 日-1974 年 3 月 26 日)是一位美国核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了雷达的开发,以及作为战略的一部分的核武器的开发。
曼哈顿计划。
弗兰克-康登原理和斯莱特-康登规则均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麦卡锡时期,爱德华·康登也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哈特兰·斯威特·史奈德(Hartland Sweet Snyder,1913年—1962年),美国物理学家。
奥本海默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是他和史奈德在1939年9月1日发表的《论持续不停的引力相吸》(On Continued Gravitational Contraction)。
这篇文章预测了黑洞的存在,尽管他们当时没有用“黑洞”这个词。
但该日更广为人知的是,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0入侵波兰,一般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Giovanni Rossi Lomanitz,1921年10月10日-2002年12月31日),美国物理学家。
20 世纪 40 年代初,洛马尼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研究生。
在那里,他成为物理学家J.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得意门生。
在实验室期间,洛马尼茨帮助建立了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联合会(FAECT) 的小型工会。
1942-45 年参加曼哈顿计划。
由于被怀疑与共产党活动家史蒂夫·尼尔森存在密切联系被免职,随后应征入伍并在太平洋服役。
之后,在康奈尔大学由理查德·费曼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
战后,洛马尼茨被传唤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他的身份是奥本海默被暂停安全许可的重要证据。
由于怀疑与调查,洛马尼茨一度从事铁路维护工人。
1962年,他开始在新墨西哥州矿业技术学院工作,后来担任系主任,1991年因癌症退休。
最后再谈谈感受:1.影片完成度很高,对白很密集,需要全程集中注意力;2.35mm胶片版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过还想二刷一遍IMAX体会一下差别,杜比厅应该也不错,这部片音效与配乐也很重要;3.看电影千万别选第一排!!!
2 ) 巨匠的彷徨
将我锻炼成男子的不是那全能的时间和永恒的命运吗?它们是我的主人,也是你的主人。
——《普罗米修斯》,歌德作为一个一直以来反感诺兰造神运动的观众,我其实是非常享受大部分诺兰作品带来的观影体验的。
他前中期作品序列里的精巧设计的叙事结构,以及以结构为方法论延展出来的悬疑张力、人物的丰富层次,是以方法本身达成了某种对于时间性的精密操控,具备数学性美感的同时,也使得故事有了智识性的“好看”。
当然这样的手法到了诺兰上一步作品"Tenet”时,走火入魔式对结构和时间性的精密操控,已经显示出了其对作品本身的喧宾夺主,成为了公式性复杂剪辑的自娱,一种奇观性叙事手法的僭越与反噬。
而在一部传记片中,诺兰将如何用自己的标志性手法,来给予故事一个复杂但有意义的结构?
诺兰在“Oppenheimer”中的设计是是一个嵌套式的三幕式:早期生平与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一场精心构陷的安全许可听证会,以及另一场以黑白形式呈现的针对“反派”Strauss的听证会。
其中第一幕和第二幕利用大量的交叉剪辑,在叙事上紧密连接;第三幕的黑白呈现则是一种对主角不在场的提示设计,不时出现的回溯性,则给故事注入了政治悬疑元素,甚至在最后成为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大快人心式表达。
如果说复杂而精巧的结构是诺兰的方法论和基本盘,那与结构派生而来的交叉剪辑就是主干之上脉络的展开,是其电影技巧的精华。
这一手法在早期作品中可以打乱现实与记忆,成为人物混乱内心的绝佳外化表达("Insomnia", “Memento”),或者是更加商业化作品里带来的戏剧张力和悬疑感(“Inception”,蝙蝠侠系列)。
在“Oppenheimer”中,交叉剪辑被用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第一二幕之间,几乎交叉到了麻花绳的地步:无数次在听证会的询问和相关的事实本身中交叉,但这样的手法从我的观影体验而言是完全失败的,他让故事和人物变得破碎、单薄,让观影体验冗长而无趣。
原因很明显,交叉剪辑之前体现魔力的悬疑性和主观性消失了。
三个小时的篇幅中,似乎为了摆脱一些专业影评人对其交叉剪辑技术上的粗糙和笨拙的批评,剪辑点在“Oppenheimer”中设计得具备高度逻辑性,但在过长的篇幅中,这种工整的设计显得过于单调乏味,诺兰并没有设计若干个关键性事件成为剪辑的锚点,几乎是刻意地放弃了这种显而易见能带来悬疑感和戏剧张力的手法。
为什么我猜测是刻意的呢?
因为在第三幕与第二幕的嵌套中,这样的手法是纯熟而成功的,虽然我异常反感那个正义感十足,阴阳怪气满分的助手形象,但一个因妒生恨的政治构陷事件依然可以拍的非常“好看”。
同样消失的还有主观性,反复的交叉剪辑中,我们看到了主角碎片化的事件,他学习、猎艳、参与政治活动、接受质疑和荣誉,但这些事件之中是没有脉络相连的,我们没有从中看出他对这一切是什么样的感受和态度。
尤其是对于原子弹本身的态度,只有一场体育馆里的庆祝演讲的戏,充满着宏大的嘈杂,清晰而生硬地体现出了他的纠结和彷徨。
这是个关键性时刻吗?
从前后的表达上来说似乎是的,但这显然无法令人信服:这一刻特殊在哪?
这一刻何以使得曼哈顿计划执行过程中未曾出现的彷徨浮上水面?
即使强行要让观众相信就是此刻,但缺乏铺垫突然出现的此刻,在电影技法上也显得过于唐突。
这种没有悬疑感和主观心理探幽的交叉剪辑成了一个纯粹的文本游戏,是解答,是互文、隐喻和象征的文学手法的大甩卖。
长篇幅、碎片化、无张力的碎片式剪辑,叠加从未停止的配乐,使得影片大半篇幅的观感更像预告片甚至片花,让我这样的观众困惑直至失去注意力。
这样糟糕的观感,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通俗手法刻意放弃的结果。
Oppenheimer的故事太过家喻户晓,就连原著传记的题目都直白地说出了“普罗米修斯”的戏剧性隐喻,作为当代电影工业的巨匠,诺兰拒绝了一切直给的戏剧张力和情感表达,毅然采用了一个看似工整、但缺乏更深层叙事和情感连接的碎片式手法。
如果说早期的"Insomnia"的交叉剪辑是实现了“将观众置于主角脑中”的主观性叙事的话,那"Oppenheimer"则是彻底的反其道而行之,诺兰从未想将观众置于Oppenheimer的脑中,也许他觉得这样的心理探幽太过直白和Cheesy,从而彻底放弃具备传递感的表达。
他所希望的,也许是观众可以一次次地透过镜头凝望Cilian Murphy的双眼,逐渐看到他内心的裂变和聚变。
但一些观众如我,透过碎片看到的,就像影片中反复出现的Oppenheimer脑中原子核裂变的场景一样,似乎有能量,但意义不明。
所以到了第三幕时,回归了正常手法的影片,也就让如我这样的观众处在一个更熟悉更舒服的范式之中,其实我非常喜欢的倒数第二场戏,用的恰恰就是一个通俗的场景复现手法,揭开悬疑的同时做一个解答式的表达:没有人可以成为神,巨匠们被追捧,被非议乃至被迫害,但终将被人类以纪念的方式遗忘。
这恰也是我对诺兰造神运动的深恶痛绝的根源,巨匠也并非神,面对一个不熟悉的题材,只能继续拿出自己看家本领的“结构”来施展的同时,却因为巨匠的包袱,既主动又被动地放弃了“平庸”的技法,就好像一个中餐大师去做甜品,他必然是彷徨的,囿于自己的历史定位和一切创作之外的东西,无法接受自己按照食谱拿出一个工整却平庸的作品,执拗地在口感刀工火候上精益求精,但坚决摒弃诸如奶油烤箱这类大路货的使用,也许会在形式上具备“高级感”,但带给食客的感觉免不了是奇怪和不适。
这是否是所有食客的不幸我不确定,因为依然会有很多食客买账并追捧。
但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大师的不幸。
在这一点上,巨匠诺兰遭遇了与他作品中巨匠所遭遇的类似的彷徨,这大概就是全能的时间,与永恒的命运吧。
3 ) 为什么好像没人去讨论墨菲的表演
看完《奥本海默》,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表演,第二个是导演,也就是说如果这片子换了其他导演拍会怎样,是不是就像《我的左脚》《至暗时刻》那种传统的传记片模式:会将一切焦点放在主角的表演上。
所以说我心里想的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为什么好像很少有观众去讨论墨菲的表演?
或许因为导演是诺兰,世界影史的一个黄金招牌,他本身就代表着创新和激情。
他的电影永远是那么追求完美和真实。
当然我还是觉得也并不是因为导演名头太大 ,而不去关注墨菲。
墨菲本人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爱尔兰演员,他在金棕榈影片《风吹麦浪》担当主角,在英剧《浴血黑帮》更是大放异彩,圈粉无数。
其实他也是诺兰的御用演员,也可以说是心头肉。
按理说奥本海默是一个极为复杂矛盾的角色,一个好演员接了这么一个本子,内心肯定是相当激动的,虽然困难但很有挑战性,至少是一个赢得奥斯卡表演奖的机会。
我们当然在影片中也会看到墨菲卖力的表演,但为什么就不会给人一种炸裂的感觉呢?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也想提出自己一点想法。
我觉得实在是诺兰的影像风格太过于鲜明,视听分镜太过于出色,高强度的节奏和高密度的音乐以及高频率的分镜,在蚕食着墨菲的表演,或者说是在将他的表演完整性去打破,让他的表演成为碎片,让其成为视听影像的一部分。
想起一个不确切的例子,希区柯克不需要表演,他只需要剪辑就可以完成一切。
诺兰不是这么极端,但他有点极为自觉的影像创作意识,他不会让任何因素去阻碍自己影像的流畅性。
所以说他根本无视或者说没有给墨菲一个思考的空间——所谓表演的solo。
但是确给了黑白部分唐尼表演的机会,很明显唐尼的表演正是因为有了诺兰的“让步”而更有层次感,更具爆发力,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唐尼至少会有一个奥斯卡最佳男配的提名。
(黑白部分诺兰的掌控欲没有彩色部分强)不过我也不是说墨菲演的不好,恰恰因为他演的太好,才给这部视听语言至上的电影增添光彩,其他的传记片,表演可能凌驾一切,或者说与其他因素都割裂开来,《奥本海默》的表演是视听大厦的一砖一瓦,是底子,是根基。
也就是说墨菲的表演是在给影像献祭,极具牺牲精神的。
除了演员表演,我挺想说说电影声音。
我从小就对影像声音很敏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小时候家里没有有线频道,我总会在外面听邻居们电视的声音,久而久之对声音有了一种非常亲切 间离 独特的感觉。
所以我在看《奥本海默》时没有一秒钟是分神的,因为音乐实在是把我给钉住了,这让我仿佛回到了几年前看《敦刻尔克》的爽劲儿体验。
对于电影声音而言,我觉得最难的是片段之间声音的过渡性,我们之前往往批评一部片子,说它煽情了 太突兀了,其实无非也是在批评声音过渡的不流畅,造成了节奏的卡顿,不完整,让观影体验很割裂。
《奥本海默》无论是影像的过渡还是声音的过渡都是大师级别的,尤其是声音的过渡没有一丝不适和不安,十分流畅和自然,音乐铺满全场,并没有感觉吵,反而心一直被牵着走,它跟影像互为肉体和灵魂,如果说表演是“神”,那就是很经典的肉灵神三位一体,那营造的观影体验是真的沉浸和神奇,乃至歇斯底里的不可思议。
所以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它甚至让我萌发出二刷的冲动,这才是一部电影何为电影的电影,大家至少回归电影这个本体,去好好探讨视听了,毕竟视听语言才是电影的一个最基本的“根儿”。
另外我还是想再简单说说几点:1、其实没必刻意去了解影片中科学家的生平,他们其实是这道大菜的辅料,顶多算是葱花,只需要了解奥本海默 爱因斯坦 和施特劳斯的关系即可;2、比起原子弹爆炸场景,我更喜欢爆炸后,奥本海默在礼堂受众人膜拜那种内心的挣扎,欢呼和惨嚎融为一体,那段蒙太奇拍的太绝了;3、我太喜欢电影的结尾,也确实没想到爱因斯坦我以为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角色,竟然在最后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是点睛的神笔。
这部电影至少可以宣告克里斯托弗·诺兰还是那个“神”,一个走在影像前沿,去不断突破和探索的电影之神。
是的,我甚至有点爱上他了。
4 ) 看不到IMAX 70mm胶片版《奥本海默》?先听我聊聊35mm胶片版和IMAX COLA版的对比(附影厅评价)
《奥本海默》确定香港作为亚洲唯一35mm菲林版(胶片版)放映城市之后,内地上映迟迟没有消息,我和对象蠢蠢欲动,终于在7.8等不及买了香港太古城百老汇的电影票,过了几天英皇激光IMAX开票又买了一场,既然没有IMAX 70mm胶片版不如体验双版本。
小激动了十几天,忽然7.19环球影业宣布《奥》在中国大陆过审,上映日期待定(就在我写文章的时候定档了……8.30);当晚微博上铺天盖地传说香港把本片分为II B所以肯定没有全裸做爱戏,还有博主确认了PG 13版本不是大陆特供且大陆版一刀未剪(仅对某些画面作特殊处理),大家应该还记得当时很多人立马在网上问怎么退票,我则又加买了一场是枝裕和的《怪物》……但第二天上午就有观众证实香港放映版本并未处理。
波米新号四季办在7.21发了《奥本海默》首映分享&版本指南,我一听,他看的版本(以及影城选择)跟我买的一模一样……总之,7.23这天就奉献给了《奥本海默》。
上午在太古城百老汇MOViE MOViE Cityplaza House 3(3号厅)看了35mm胶片版。
明显能感受到拍摄规格远高于放映规格,像是很好的东西做了个旧,打个比方就是想象一首2010年代的电子舞曲被录在磁带上,不是说磁带不好,但你能感受到最终呈现规格在制约表达效果,它就不如80年代歌曲在磁带上那么自然贴切。
全片画幅是2.39:1,对于一部主要为IMAX 70mm胶片和普通70mm胶片设计和拍摄、室内戏多、对话为主、对峙戏也少有安排横向张力的传记片来说,宽幅本身并没有优势,切卷提示小圆圈和胶片划痕也是必然存在的(想最大程度避免划痕、感受理论最高画质的话只能看首映场)。
但值得一提的是35mm胶片版的声音。
对我来说有一种很微妙的高切感(请教了在美国的混音师@变脸 范师,他推测是胶片版做print时可能有单独混录,并且杜比的人编码之后多少影响了音色,从而带来了不太一样的频响感受),很润,这种不过分明亮的听感非常符合人耳听觉习惯,声音绝不老旧但真的没有现在好莱坞大片里经常能感受到的侵略性,就像你在生活里听到的绝大多数声音那样,永远不会有哪里冒出来让你觉得“哇偶这音效做得真牛逼”的地方,给这三小时提供了足够的沉浸感。
百老汇太古城店的影厅音响系统调校也好,听感弹性十足,动态和响度都足够。
前一天晚上在2号厅看《怪物》的声音也非常好听。
顺便提一句,注意这家影城不允许外带饮料(至少不能端着一杯外带饮料进去)。
————————晚上在尖沙咀英皇iSQUARE House 5看的IMAX COLA版(即通称的二代激光IMAX版)则雷点不少。
我坐的位置H20时常能看到一块不知道哪儿反射过来的耀斑(对象坐H19说她看不见),这个耀斑随着画面亮度变化时有时无,但能感受到影响条件不是耀斑所在位置的画面亮度,而是另一个地方的亮度;耀斑出现位置的右边(银幕上中间偏右位置)还有个小暗病,波米说是坑,放映时投上去亮的画面看起来的确像坑,不过映前开灯时看上去更像凸起。
巨幕和1.9:1画幅(非满屏状态是2.2:1)的确让一些空镜和人物特写看起来比35mm版震撼很多,通透度也有提升,但这基于二刷时我已经不太看字幕了所以更能专注于体会影像的质感区别,如果一刷,在字幕附近会看到快节奏对白+纷至沓来的人名+同一场戏不断变化的画幅下边缘位置,这个体验难称完美,对我来说会是一种分心的因素。
声音上,超高频多显得整体更明亮,很多毛病会随之被清晰地展现出来,比如同期对白里的高频噪音非常明显,奥本海默在小礼堂发言的那场戏第一句台词的音质受损严重(滋啦滋啦响了都);音响系统上很IMAX,1kHz左右偏多导致声音整体偏bitey,瞬态也快,总之跟在内地二代激麦看其他大片的感受差不多。
————————看完回来,跟深谙电影放映和版本选择的同事讨论,他说「35mm版声音录制在胶片边缘磁轨道上,理论上声音信息比数字版本多哦」,我问他「理论上声音信息比数字版本多」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同事说「他(诺兰)为胶片版本做专门的音轨,动态范围更大的打印回母版胶片」。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所谓「声音信息多」的提法我个人觉得不准确。
无论动态范围上还是频率上,35mm胶片这个载体都是先天不足的。
民用磁带有效动态范围不到90dB(也就是理论上不如数字16bit动态范围大),35mm胶片上数字光学声迹的动态范围理论上可以大于90dB,但胶片版print做单独混录和杜比编码时可能会减少动态最大的部分防止峰值爆音,也就是说动态范围依然会变小;70mm胶片的声音保真度比35mm胶片更上一层楼,早年间一直宣传比大多数数字格式保真度更高,但要说能匹配如今数字技术的24bit(约144dB)那也不太可能(另,IMAX 70mm胶片版使用特制数字光盘同步播放声音)。
频率更别说了,激麦版能听到的同期对白高频空气噪音在35mm版里都是几乎听不到的(当然可能也有动态小的因素),如果把这个高频噪音也当作声音信息(我知道我违背了祖宗的信息论),那么你能在35mm版里听到的声音无疑是更少的。
综上,我觉得35mm胶片版听感好并不是因为它声音的硬素质更好、提供了「更多的」东西,而恰恰是因为它给我的东西少,反而突出了主次、屏蔽了干扰、避免了疲劳,从而达成了香农信息论意义上的「信息多」的效果。
我们生活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高频和大动态的声音,而且人是活的,感受到刺耳、震耳欲聋的时候我们自然趋利避害地调整听音条件或位置,或者干脆休息一下不听了,这对于强制连续放映、观影位置和还放参数固定的电影来说就不成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频多、大动态范围的声音就不好、不能让人沉浸,诺兰《敦刻尔克》那种吵闹、突然的声音风格使得我在观影过程中随时准备堵耳朵,因为流弹和轰炸的瞬态和音色都太吓人了,这种紧张感、末日感唤醒了极度的煎熬,从而让人体会到战场的恐怖和战争的恶心;再加上《敦》只有107分钟,基本算是在听觉疲劳之前结束了,所以我对它印象非常好。
————————总体来说,非要放在一起对比的话……二代激麦版像个上蹿下跳的孩子,你知道ta有活力,ta学了很多新东西,但ta还没被打磨圆润,你不一定有耐心和体力陪ta疯那么长时间。
35mm胶片版则像个经历丰富、会讲故事的老人,虽然理论上硬件不如年轻人了(视听参数降级),但在抹平、拉平、统一了很多东西之后,反而更适合呈现一个较长的整全作品。
这有点像混音里讲模拟介质所谓glue感的真谛:不仅是把声音粘合在一起,而更是让各具特色的元素能够共同为一个更简单纯粹的目的服务,「少」中见「多」。
我非常理解和欣赏一些影片在新的视听技术上的较劲和拓展(没有它们就没有技术普及与进步),但这次看35mm胶片版《奥本海默》时,作为观众最大的感受就是,看电影,也许用不着先成为一个电影制作和放映技术专家去比较各种版本和影厅的优劣,也许不必为了买不到心仪的影厅和座位而过度焦虑,抱着一桶爆米花轻松地坐在电影院里,为影片鼓掌而不仅仅是为参数所吸引,这样貌似老旧、单调的条件会把我拉回私人电影史中遥远到模糊的记忆。
那段记忆没有画幅变换、没有HDR、没有全景声,只有一个小孩全情投入在电影中的快乐。
5 ) 看《奥本海默》时你需要知道的七件事以及如果你可以影响历史你会吗以及与《哥本哈根》
二次刷完的二更分界线---随着本片在全球的逐步公映,许多好友都去了二刷或者表示想要二刷,这说明我二刷此片并不是个人意趣,确实是信息量太大,太多可回味,太多可深入。
我女刷完之后说此片可排在诺兰作品中前三,应该超越了《星际穿越》。
我与她的看法基本相同。
《盗梦空间》创意太天才,结构太完整,以至让我觉得技术胜过了人性。
看到诺兰的采访,他说《奥本海默》本质上是一部盗抢片(Heist)和法庭辩论片(Courtroom)的结合,看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
这部看起来结构如此复杂的片子无非是两个故事:一个是曼哈顿计划,一个则是曼哈顿计划之后的罗生门。
曼哈顿计划本质上和《盗梦空间》是一致的盗抢片:几个人/天才,具有不同的才能,凑到一起,完成一个天马行空的计划。
这个题材被拍得太多了,《十一罗汉》、《瞒天过海:美人计》都在此列,之所有受欢迎,是因为观众乐此不疲。
当然这一次的计划是制造原子弹,用《盗梦空间》里Tom Ford的话说:做梦就要做大。
有趣的是,诺兰真的为本片在新墨西哥州搭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场景,让演员在其中自由地工作和社交。
艾米丽·勃朗特说:我以前也为很多我拍过的片子自豪过,但这一次和诺兰拍片,我真的觉得是一生一次的与有荣焉。
他就是那种能让演员在片场发挥最大才能的导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拍这部片本身的过程,不也是部津津乐道的盗抢片?
而法庭辩论片更是常拍常新、常看常新的题材。
从东方的《罗生门》,到西方的《控方证人》、《好人寥寥》,全是影史经典,盖因情节中总有双方激烈交锋,容易出彩。
《奥本海默》的听证会部分就是个罗生门,另一部讲海森堡为什么没有为德国造出原子弹的话剧《哥本哈根》也是部罗生门。
多年前在北京的东方先锋话剧小剧场看完《哥本哈根》时的心潮澎湃还历历在目,然而现在已经不记得和谁一起看的了。
附录:下面是多年前在北京看《哥本哈根》时的评论,如今翻回来,发现自己的文字超越了十几年的时光,仍可以与《奥本海默》相互对照。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1941年9月,整个欧洲都被希特勒的铁骑践踏之时,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秋日的夜晚来到了他曾经合作多年、亦师亦友、亦父亦兄的导师,被物理学界称为精神教皇的玻尔家中。
作为丹麦人的玻尔,家中已是监视严密,到处都是窃听器和盖世太保看不见的影子。
这是一次战胜国与被占领国之间的交谈,也是纳粹德国与未来的同盟国之间的交谈。
此时,德国、美国都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原子武器,而武器的核心就掌握在这些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
他们为避开窃听,选择了到户外散步,而10分钟后,两人就怒气冲冲地不欢而散,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就此结束。
事实是,美国制造成功并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而德国未制造成功。
在战后的30年,海森堡都处于竭尽全力的解释,非难与敌视中。
在那短短的十分钟里,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战后,英国情报局和无数的历史学家都想弄清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然而却从未解读出真正的原因。
戏剧就在玻尔、海森堡和玻尔的妻子玛格丽特死后灵魂的对话中产生。
在没有政治利益的对话中,三人一次又一次地想解读出他们当年的对话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是由于什么原因。
海森堡不远万里来到玻尔的家中;两人对对方的深厚感情;那短短十几分钟的户外谈话。
唯一可以解读的是,这次谈话的后果是海森堡告诉纳粹,研制原子弹有技术上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美国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
唯一可以认定的是,海森堡当时向有着“教皇”之称的精神领袖玻尔问出了以下的话: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 对于这次决定世界命运的谈话,剧作者迈克·弗雷恩写了三个可能。
第一个是,海森堡是想向玻尔传递纳粹正在研制原子弹的原因,并告诉玻尔现在全世界的原子秘密都掌握在他们这几个人的手中,希望玻尔向同盟国的科学家传递共同不制造原子弹的默契,但波尔误解了他。
然而,这个原因被民族主义和政治利益打败了,如海森堡所说,“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与我交谈的一颗颗心。
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 德国是我的孩子。
我该知道我为他们选择什么!”于是三个灵魂只能重来。
第二个可能是,海森堡是来炫耀的,然而如果如此,海森堡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根本不可能连扩散率计算的数学都没做就放弃了原子弹,这只能说明海森堡和玻尔一样,都“没想要造原子弹”。
在第三个可能中,弗雷恩放弃了对原因的解读,只把最后实际的结果公布给观众——海森堡的双手没有沾过任何人的鲜血,而奥本海默,作为正义的一方,却屠杀了无数的无辜民众。
观众该相信谁?
该如何解读这短暂的片刻?
剧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说,一切得以幸免,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的事件,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
《哥本哈根》是一次话剧上的罗生门。
比罗生门还要精妙的是,它把物理学上的种种两难性理论,如测不准原理和薛定谔的猫与政治世界的瞬息万变结合在一起。
科学家们,自以为成为神的旨意的化身的科学家们,以上帝视角俯瞰着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他们掌握着人类的终极秘密,然而讽刺的是,这个世界总会沿着其自有的规律发展下去,比如原子弹的制造,比如克隆的成功,都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的命运。
我们与其从原因中勘察,不如以结果为准则。
更因为,这是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人,今天出门坐公共汽车,明天骑自行车,后天打车,是没有原因,或者说原因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的;我们只能讨论结果。
而原因,就在人们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解读中,被演变成了历史。
每个历史学家都是storyteller,每个普通人在回忆自己过往的时候,也是storyteller。
这个Teller无谓对错,也无谓真假,只有结果。
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高考时报了一所其他的大学/志愿?
如果我那天没有去那个餐厅,就不会遇见那个女孩?
如果我没有那次面试,没有去异域工作?
谁也不知道生活是否会改变,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生活。
在东方先锋的小剧场里,不知有多少人为这两小时的话剧激动和沉思过。
《哥本哈根》无疑称得起20世纪最伟大的50个剧目之一的称号,也是极少数让人看了之后想再看一遍、或者去看剧本的话剧。
话剧在这里展示的是真正的语言魅力,而非像现在流行的那样,跳梁取笑,或感官优先。
看了话剧之后再看剧本,感到的是弗雷恩深刻的思想、丰富的信息量;看到剧本之后再看话剧,会发现那些平面的台词被演员演绎得活色生香,其中不乏动人的、或铿锵有力的台词:有描述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短暂宁静的美好生活;有海森堡和玻尔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热爱;有玛格丽特对自己丈夫的爱惜和维护;有掌握命运的科学家在22条规则的责任和义务中生活的沉重。
这是一部可以成为教科书的话剧。
三个人,三把椅子,两个小时,基本没有变换过的场景和布置。
比起某些话剧的上蹿下跳和某些人号称的先锋、实验,这是多么简洁的艺术,这才是话剧的真正魅力。
第一次刷完这部三小时的电影,本质上说的是一个人发现自己可以影响历史时,自我内心的矛盾,以及整个世界对他的矛盾看法。
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那五分钟的床戏没什么必要。
电影对女性的角色刻画太少,以至于两位女配角都没有什么发挥空间。
Emily Blunt饰演的妻子Kitty和本来是有夫之妇,和奥本海默一夜情之后怀孕了,基本可以说是闪婚,然而她就是那种闪婚也不奇怪的女人:干练冷硬,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爱情,但可以和丈夫披荆斩棘;Florence Pugh饰演的前女友和情人Jean也许和奥本海默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她知道他的《薄伽梵经》,甚至在床上也带着它,最后奥本海默给自己的原子弹实验起名Trinity也是她向他介绍的诗歌。
然而,两人无法在一起,最后Jean罹患抑郁症自杀身亡,也是奥本海默角色性格的一个侧和通常高质量的诺兰电影一样,剪辑和音效起码可以给这部电影加成百分之五十。
看电影前有人说原子弹爆炸的场面是个默片,我傻傻地信了,结果出来的视听(注意,是“视”和“听”,这两者是分离的)效果震煞了我。
虽然杜鲁门作为一个政客在影片中是个反面角色,但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挺对的。
杜鲁门接见奥本海默,恭维他的贡献;然而奥本海默不小心说了心里话:“我觉得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杜鲁门顿时变脸,说:“他们才不关心谁造了原子弹。
他们关心的是谁投的原子弹。
而那个人,是我。
”吉利安·墨菲终于多年媳妇熬成婆,在诺兰的电影里演了一回主角。
不知道为什么诺兰这次没有找马修·麦康纳演,可能还是因为后者长得比较土帅(美国南方帅)而前者有一张在大银幕上破碎感十足的脸吧。
总之,墨菲这回扬眉吐气,明年奥斯卡提名不是问题。
本篇配角如过江之鲫,从演员到演的角色个个都是名流,让我想起那张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年会照片。
事实上,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费曼(那时还是个小年轻)等都在电影中有所呈现,这也许是人类物理学和化学的最后黄金年代。
由于第六条,加上一众非科学家的重要角色,本篇信息量巨大,加上诺兰凌厉的剪辑,三个小时想要去上厕所基本是不可能的。
建议大家观看之前做好历史功课,没字幕的背背单词,总之我打算再去刷一遍。
下面我们回到第一条,即这部电影到底说了什么。
奥本海默——现代公认的原子弹之父——是个矛盾的人。
他出身富裕,风度翩翩,才华过人,迷倒众多女性——墨菲在银幕上也相当迷人;但同时又乖戾嚣张,年轻时试图毒死老师。
他爱国,不遗余力制造核武器;但同时又受印度佛教影响,觉得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他爱的《薄伽梵经》中,毗湿奴说向王子阿周那展示了作为时神与死神化身的宇宙相:“焚烧一切是时间,时间又将火熄灭”,毁灭、创造与重生,都是时间的显现,以及历史的必然。
诺兰是大师,我觉得没有人能比他把这个原子弹实验的场景拍得更好:波茨坦前夕,巨大压力的团队(没有想到吧,造原子弹也要赶个deadline),凌晨新墨西哥州的黑暗中,瓢泼大雨后,一团巨大的、人类从未见过的火焰腾空而已,四周是无尽的沉默,只有人类在紫外线墨镜后的沉重的呼吸。
少顷,巨大的轰鸣在现场不同距离的观测者耳畔响起。
一些人笑了,一些人哭了,更多人不知所措。
对这一场面,奥本海默多年后在公开场合曾经引用《薄伽梵经》里的话描述他的内心:
”我将变成死神,世界的毁灭者(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站在历史的悬崖边,他是不可能不知道他制造原子弹所能带来的后果的。
这是划时代的发明,可惜也是划时代的杀人武器。
他用于自洽的逻辑是,他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的,但他知道,他肯定不能让纳粹先做出来。
这个逻辑于情于理,完全说得通。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内心是迷恋这种站在悬崖边的地位的:他知道他的双手推动了人类的堕落,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我觉得他甚至有一丝迷恋因为这种双手沾了鲜血而负罪累累的感觉,那代表着他是被历史选中的人。
另一个影片的高光场面是向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那天,奥本海默走进的庆功会场面。
耳旁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妇女们高兴到癫狂的脸庞;而他的幻境里出现了尖叫声、死弹的白光、被辐射而剥落的皮肤……这两种光影融合在一起,正是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后的景象。
诺兰拍出了他看到的,和他感受到的奥本海默个人的这种矛盾和复杂性,加上他受到妻子和女友的左翼思想影响,使他成为了战后麦卡锡主义追逐的对象。
杜鲁门要的是爱国形象,麦卡锡要的是冷战利益,他是两者的相反。
影片用大量篇幅讲述了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原子弹委员会主席Levis Strauss对他的穷追猛打式的听证,并最终撤销了他的国家安全许可。
这是加诸个人身上的更大的时代的矛盾,也是他选择领导曼哈顿计划时就早已想好的不回头路。
正如他在影片中第二次找到爱因斯坦时候他所问的:“您记得第一次我来找您时,聊到的我们的公式计算告诉我们,我们有极小的可能性,会毁灭这个世界吗?
”爱因斯坦说,记得。
然后奥本海默说:“我们已经毁灭了这个世界。
”
这部电影让我想到多年前在北京工作时看的一部绝佳话剧《哥本哈根》,讲述的是原子弹的另一面故事:作为德国原子弹研究带头人的海森堡和他的老师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一次重要谈话,以及对之后我们的知道的历史的解读。
《哥本哈根》和《奥本海默》的连结点是玻尔。
玻尔在电影中被盟军从丹麦解救出来,而他明确告诉奥本海默,他不是来帮助他制造原子弹的。
海森堡和奥本海默这两个入世的人站在历史的两端共同书写了我们今日看到的历史,而玻尔如薄伽梵经中的印度神一样,俯瞰着这个世界。
下面是二更的分界线。
---随着本片在全球的逐步公映,许多好友都去了二刷或者表示想要二刷,这说明我二刷此片并不是个人意趣,确实是信息量太大,太多可回味,太多可深入。
我女刷完之后说此片可排在诺兰作品中前三,应该超越了《星际穿越》。
我与她的看法基本相同。
《盗梦空间》创意太天才,结构太完整,以至让我觉得技术胜过了人性。
看到诺兰的采访,他说《奥本海默》本质上是一部盗抢片(Heist)和法庭辩论片(Courtroom)的结合,看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
这部看起来结构如此复杂的片子无非是两个故事:一个是曼哈顿计划,一个则是曼哈顿计划之后的罗生门。
曼哈顿计划本质上和《盗梦空间》是一致的盗抢片:几个人/天才,具有不同的才能,凑到一起,完成一个天马行空的计划。
这个题材被拍得太多了,《十一罗汉》、《瞒天过海:美人计》都在此列,之所有受欢迎,是因为观众乐此不疲。
当然这一次的计划是制造原子弹,用《盗梦空间》里Tom Ford的话说:做梦就要做大。
有趣的是,诺兰真的为本片在新墨西哥州搭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场景,让演员在其中自由地工作和社交。
艾米丽·勃朗特说:我以前也为很多我拍过的片子自豪过,但这一次和诺兰拍片,我真的觉得是一生一次的与有荣焉。
他就是那种能让演员在片场发挥最大才能的导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拍这部片本身的过程,不也是部津津乐道的盗抢片?
而法庭辩论片更是常拍常新、常看常新的题材。
从东方的《罗生门》,到西方的《控方证人》、《好人寥寥》,全是影史经典,盖因情节中总有双方激烈交锋,容易出彩。
《奥本海默》的听证会部分就是个罗生门,另一部讲海森堡为什么没有为德国造出原子弹的话剧《哥本哈根》也是部罗生门。
多年前在北京的东方先锋话剧小剧场看完《哥本哈根》时的心潮澎湃还历历在目,然而现在已经不记得和谁一起看的了。
附录:下面是多年前在北京看《哥本哈根》时的评论,如今翻回来,发现自己的文字超越了十几年的时光,仍可以与《奥本海默》相互对照。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1941年9月,整个欧洲都被希特勒的铁骑践踏之时,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秋日的夜晚来到了他曾经合作多年、亦师亦友、亦父亦兄的导师,被物理学界称为精神教皇的玻尔家中。
作为丹麦人的玻尔,家中已是监视严密,到处都是窃听器和盖世太保看不见的影子。
这是一次战胜国与被占领国之间的交谈,也是纳粹德国与未来的同盟国之间的交谈。
此时,德国、美国都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原子武器,而武器的核心就掌握在这些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
他们为避开窃听,选择了到户外散步,而10分钟后,两人就怒气冲冲地不欢而散,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就此结束。
事实是,美国制造成功并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而德国未制造成功。
在战后的30年,海森堡都处于竭尽全力的解释,非难与敌视中。
在那短短的十分钟里,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战后,英国情报局和无数的历史学家都想弄清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然而却从未解读出真正的原因。
戏剧就在玻尔、海森堡和玻尔的妻子玛格丽特死后灵魂的对话中产生。
在没有政治利益的对话中,三人一次又一次地想解读出他们当年的对话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是由于什么原因。
海森堡不远万里来到玻尔的家中;两人对对方的深厚感情;那短短十几分钟的户外谈话。
唯一可以解读的是,这次谈话的后果是海森堡告诉纳粹,研制原子弹有技术上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美国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
唯一可以认定的是,海森堡当时向有着“教皇”之称的精神领袖玻尔问出了以下的话: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 对于这次决定世界命运的谈话,剧作者迈克·弗雷恩写了三个可能。
第一个是,海森堡是想向玻尔传递纳粹正在研制原子弹的原因,并告诉玻尔现在全世界的原子秘密都掌握在他们这几个人的手中,希望玻尔向同盟国的科学家传递共同不制造原子弹的默契,但波尔误解了他。
然而,这个原因被民族主义和政治利益打败了,如海森堡所说,“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与我交谈的一颗颗心。
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 德国是我的孩子。
我该知道我为他们选择什么!”于是三个灵魂只能重来。
第二个可能是,海森堡是来炫耀的,然而如果如此,海森堡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根本不可能连扩散率计算的数学都没做就放弃了原子弹,这只能说明海森堡和玻尔一样,都“没想要造原子弹”。
在第三个可能中,弗雷恩放弃了对原因的解读,只把最后实际的结果公布给观众——海森堡的双手没有沾过任何人的鲜血,而奥本海默,作为正义的一方,却屠杀了无数的无辜民众。
观众该相信谁?
该如何解读这短暂的片刻?
剧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说,一切得以幸免,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的事件,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
《哥本哈根》是一次话剧上的罗生门。
比罗生门还要精妙的是,它把物理学上的种种两难性理论,如测不准原理和薛定谔的猫与政治世界的瞬息万变结合在一起。
科学家们,自以为成为神的旨意的化身的科学家们,以上帝视角俯瞰着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他们掌握着人类的终极秘密,然而讽刺的是,这个世界总会沿着其自有的规律发展下去,比如原子弹的制造,比如克隆的成功,都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的命运。
我们与其从原因中勘察,不如以结果为准则。
更因为,这是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人,今天出门坐公共汽车,明天骑自行车,后天打车,是没有原因,或者说原因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的;我们只能讨论结果。
而原因,就在人们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解读中,被演变成了历史。
每个历史学家都是storyteller,每个普通人在回忆自己过往的时候,也是storyteller。
这个Teller无谓对错,也无谓真假,只有结果。
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高考时报了一所其他的大学/志愿?
如果我那天没有去那个餐厅,就不会遇见那个女孩?
如果我没有那次面试,没有去异域工作?
谁也不知道生活是否会改变,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生活。
在东方先锋的小剧场里,不知有多少人为这两小时的话剧激动和沉思过。
《哥本哈根》无疑称得起20世纪最伟大的50个剧目之一的称号,也是极少数让人看了之后想再看一遍、或者去看剧本的话剧。
话剧在这里展示的是真正的语言魅力,而非像现在流行的那样,跳梁取笑,或感官优先。
看了话剧之后再看剧本,感到的是弗雷恩深刻的思想、丰富的信息量;看到剧本之后再看话剧,会发现那些平面的台词被演员演绎得活色生香,其中不乏动人的、或铿锵有力的台词:有描述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短暂宁静的美好生活;有海森堡和玻尔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热爱;有玛格丽特对自己丈夫的爱惜和维护;有掌握命运的科学家在22条规则的责任和义务中生活的沉重。
这是一部可以成为教科书的话剧。
三个人,三把椅子,两个小时,基本没有变换过的场景和布置。
比起某些话剧的上蹿下跳和某些人号称的先锋、实验,这是多么简洁的艺术,这才是话剧的真正魅力。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的公众号王小心
6 ) “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千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
(首发“深焦”公众号)看完《奥本海默》,我有个奇怪的联想——我理解程心为何不向宇宙发送三体的坐标了。
这不是夸张。
三小时片长的《奥本海默》最珍贵也最有力的是原子弹实验(“三位一体”)的短暂影像。
人眼即使戴上保护镜也不能“看”的炫目白光冲破屏幕而来,血红的蘑菇云在死亡的寂静中慢条斯理地绽开。
“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千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
光,唯有光。
这千只太阳的光提供了一次摄影。
而《奥本海默》和影院中的我们,只是组成宇宙的影像中的一些影像。
匍匐在地的科学家们,其血肉之躯霎时如凝固在火山灰中的尸体般惨无颜色。
洛斯阿斯莫斯成了庞贝,尽管人们尚不自知……银幕前的观众,是否能察觉他们在底片上的形象,也正如尸体?
直到……(在客观现实和主观体验中同样)很久、很久之后来到的巨响。
死在核爆中的人,其身体经过一个非生非死的阶段。
正如快走出而又消失于冥府的欧律狄刻。
其形也不存,其魄也犹在。
《奥本海默》中核试验的影像竟在视觉和听觉中捕捉了这一不可名状的形象——人类本身在恒星、核弹和宇宙面前的形象。
但这是不可“看”的,随后奥本海默将不断由眼前的构陷、倾轧和置之死地出发,试图复现那个形象,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尝试。
他看到的甚至不是恐怖但饶有诗意的白骨如山,而是剥落的屑状“皮肤”和烧焦的骨头,纯然的物质。
点缀奥本海默青年时代的宇宙之璀璨形象和连通生者死者的形销骨立构成对照,指向人类的物质实质。
《奥本海默》几乎是冷漠地给出这些形象,其实是给影院中的人也来了一次核爆。
简洁的光,定义我们栖身时空的绝对尺度,死亡的直接指示,目睹者焉能不恐惧,战栗,以及失落?
声迟滞于光,影像则终湮灭于光——因此《奥本海默》细致入微地复现了核试验——骤雨,闪烁的按钮,抖动的手指……却回避想象或提供任何广岛和长崎的影像——真实发生过的核杀戮的影像。
这不只是传记片对奥本海默本人视角的严格遵循(奥本海默自不可能亲睹)。
从根本上说,原子弹在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使用”是unrepresentable、不可言说、不可想象的。
大西洋另一侧发生的大屠杀亦如是。
所以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只在广播中出现。
哪怕它们将在梦中再重复千百遍。
这是《奥本海默》的高明之处。
属于人类知觉范畴的是战争胜利,洛斯阿斯莫斯的人们在星条旗下欢呼雀跃。
奥本海默走入礼堂,说着俏皮话,被掌声和欢呼淹没。
但这热闹在遭遇过声爆的耳朵听来不啻于地震。
于是,在电影开启两小时后,观众才会知道那萦绕全片的、愈渐疯狂的跺脚声来自何处。
在奥本海默眼中,这些人的皮肤如灰尘般剥落,讲台化为焦土。
他罹患核爆PTSD。
随后是背叛、嫉妒、举报和调查。
生命中每个被摧折的时刻都将奥本海默带回那个实验的夜晚。
广岛和长崎的死者或许来不及逃走,自然也不会有踩踏,但那不存在的踩踏声已化为跺脚声,如影随形。
至此,《奥本海默》提供了关于核爆的摄人心魄的影像和体验,用时约半小时,。
我会想为这半小时再次、再次前往电影院。
可惜,剩下的约两个半小时是乏味的。
《奥本海默》以大量闪回紧密连接起两条主线:奥本海默主持“曼哈顿计划”制造原子弹,奥本海默接受安全审查,期间穿插他的求学和情感史。
巨细靡遗。
几乎每个在奥本海默冤案中留下个名字的人都在影片中露脸。
这两条主线当然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奥本海默领导了“曼哈顿计划”,但那真正制造出原子弹的政治计算、社会控制和意识形态,在吞噬了广岛和长崎的生命后,最终也吞噬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本人。
只是,双线在意旨上的融洽因奥本海默形象塑造的缺失而不令人信服。
这一缺失来自诺兰于再现时代风貌之雄心和塑造奥本海默形象多义性间的踌躇。
就前者而言,《奥本海默》以巨大的信息密度和精巧的叙事结构描摹了战前战后都不曾散去的对communism的恐慌,《奇爱博士》式自我毁灭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活动,以及席卷了所有人的恐惧和狂热交替的气氛。
狂热和恐怖以彩色和黑白两种画面标记出来。
第三视角施特劳斯的插入和两条主线并存,这个孤立的、属于政治家的视角正是恐怖时代无时无处不在的逼视,它令人如芒在背,又最大限度地减轻大量对话戏和大量人物所可能造成的观影疲惫。
如果说奥本海默的视角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其意义尚不可确定,那么不断闯入的施特劳斯的视角则将生成中的一切变成叙事,这既是政治叙事的独断,只追问是和否;也是传记片这种形式的独断,它将真实存在过的人的经验组织为一个“故事”。
《奥本海默》以黑白画面直率地标记出施特劳斯的视角,似乎主动避免落入传记片的窠臼,提示奥本海默和原子弹诞生这段历史的多义性。
但是,领起全片的“普罗米修斯”的比喻,结尾部分类似盖棺论定的收束,以及塑造奥本海默形象时的力有不及,损伤了可能的多义性——诺兰似乎延续了《敦刻尔克》中那种对于特定时空本身的爱好和绝对关注。
在《敦刻尔克》中,遥远的、黯淡的海岸线,天际的战斗机,炸弹震起的尘土和海水,似乎都比士兵更像“主角”。
它们指向“敦刻尔克”——撤退和存活,而非光荣和胜利。
在这个时空中,个体的动机、目的乃至结局都是可知的。
在《奥本海默》中,他让奥本海默和友人一次次骑马漫游于荒凉的洛斯阿斯莫斯,又着意拍摄1945年时洛斯阿斯莫斯的兴旺人丁;让镜头久久徜徉于装载实验弹的高架,又让拿走数万人命的“小男孩”和“胖子”仓促地坐上车就走;让奥本海默事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坐到听证会长桌的那一头,让奥本海默本人坐在他们旁边的角落。
这些精心的选择诚然高效地为那个时代作传。
它们确实让我身临其境。
如果哪天有人想拍“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而非生机勃勃的核基地,诺兰也一定胜任。
不过诺兰对时空和氛围的敏感把控恰恰反衬出人物的单薄。
毫无意外地,两位女性角色,躁狂的Jean和疲惫的Kitty,也按照诺兰电影惯例担任工具人。
历史上的Jean确有躁狂障碍,但片中仿佛是要强调时人对共产党人刻板印象似的,一再无必要地让皮尤以裸体出镜,艾米莉·勃朗特饰演的Kitty也满脸厌世,靠烟酒稳定精神状态。
对两个女性角色的草率处理甚至剥削仿佛只是为了让Kitty向奥本海默道出一句话——世道惘乱艰险,但只有你,而非他人,能改变这个世界。
时代的悲剧性正悲剧性地凝结在奥本海默的生命经验。
但“救世主”的形象实在单一且庸俗了。
何况奥本海默本人的形象早淹没在如斯政治群像之中。
奥本海默其人如何?
他在学生杨振宁的笔下锋芒毕露,会走上讲台打断别人发言。
他在朋友的回忆中常亲密地提起“乔治”(时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仿佛乐于有些政界关系。
但在《奥本海默》中,他似乎只是“天真”的科学家,不知人情练达,还在亲密关系方面有些麻烦;后期则是核爆和政治双重PTSD的单纯受害者形象。
基里安·墨菲尽力了。
他的个人形象甚至为片中的奥本海默增加了剧本未太着墨的敏感自矜。
但《奥本海默》缺失了它欲讲述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的滔天力道。
如果奥本海默如本片反复申述那样,正是20世纪的普罗米修斯,那么普罗米修斯和火是怎样的亲昵?
在影片的开头,《奥本海默》试图以一些主观想象画面阐明奥本海默的志趣——他思索着物质,他和宇宙相连。
然而,果断拒绝加入共产党的奥本海默如何果断地从科学转向制造毁灭性武器,影片并未深究。
当他欲招揽的科学家忧愁地指出曼哈顿计划的毁灭性力量,奥本海默像传声筒般重复美国比纳粹德国更快造出原子弹的紧迫意义。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反派施特劳斯那句“污蔑”——奥本海默热衷“原子弹之父”的名和势。
但《奥本海默》显然避免在这一方向有更多着墨。
或许,更为复杂的奥本海默形象会损伤观众的同情。
又,盗火后的普罗米修斯日日被啄食肝脏又是怎样的痛楚?
由狂热地强调后来者唯有在实践中才能理解当下行动的意义,到在广播中听到原子弹被扔在广岛,如梦方醒,手中已鲜血淋漓,再回首是百年身。
追求真理的科学家成为死神,这不只是奥本海默本人的PTSD时刻——人类制造出可以毁灭自身之物,并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叩问至科学和理性尽头的时刻。
尽管《奥本海默》并未让奥本海默就此多言,但核试验的影像,及其此后的两次“复现“”,是一种超越甚至否定任何叙事的力量。
它们溢出了《奥本海默》的另一条主线。
千只太阳逼迫着哪怕不懂核物理的观众战栗,或许质问。
但《奥本海默》竟在给出了这样的影像之后,又轻轻将重心拨回政治惊悚的剧情,仿佛压根儿不理解其力量似的。
电影中的杜鲁门也宛如小丑,当他安慰奥本海默,广岛和长崎的决策者是作为政治家的他,而非后者时,电影仿佛在暗示一种科学和政治分离的话语。
正如电影贴心地帮观众将政治世界藉由施特劳斯的视角呈现为黑白。
这是否是《奥本海默》为奥本海默所着急作出的友善开脱?
在核爆之后的一小时里,本就节奏紧凑的《奥本海默》加速、加速至下一次“核爆”——那最终宣布奥本海默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听证会。
只是这次核爆之后,我们不可能咀嚼回响了。
《奥本海默》急不可耐地跳到传记片最爱使用的和解结尾——奥本海默坦然接受了审查结果,妻子和朋友犹在身旁,以及最终的平反。
仿佛那具因核爆而PTSD的残躯,也是可以修复的。
以至于结尾处奥本海默向爱因斯坦的坦言“我们确实毁灭了世界”,反像是某种须阐明立场而为之的策略。
7 ) 【转】方在庆:重审“奥本海默事件”
【作者简介】方在庆,1963年生,湖北天门人。
1979年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学系,1991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自200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尤其关注爱因斯坦、德国的科学与现代化。
曾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杰出访问学者”,德国慕尼黑大学埃里克•弗格林教席(Eric-Voegelin-Professur,C3)以及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客座教授等。
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论著和译作多本。
《美国的普罗米修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伟绩与悲剧》
奥本海默传8.8[美] 凯·伯德 [美] 马丁·J.舍温 / 2023 / 中信出版集团中译本
【延伸阅读】
真知灼见8.2(美)奥本海默 / 1998 / 东方出版中心
现在可以说了8.4[美] 莱斯利·R.格罗夫斯 莱斯利·格罗夫斯 / 1991 / 原子能出版社
原子物理学家的戏剧目前无人评价[西德]约斯特·赫尔比希 / 1983 / 原子能出版社
原子弹秘史(上下册)8.6(美国)理查德·罗兹 / 2008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囚徒的困境7.1[美] 威廉·庞德斯通 / 2015 / 中信出版社
柏拉圖的天空评价人数不足Ed Regis / 天下文化
第一核纪元评价人数不足[美]艾尔文.温伯格 / 1996 / 原子能出版社
8 ) 我对《奥本海默》的不满
01在《奥本海默》里,我看到了诺兰故作镇静下的无所适从。
在面对历史上或许最敏感、最暧昧、最犹疑的灵魂时,他想要无损地呈现出这颗灵魂真实的质地,呈现出它全部的挣扎、内在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中隐含的自洽,但很可惜,诺兰似乎还没有找到方法。
他的理性过于强大了。
这是诺兰的绝技,也是他的命门。
理性总能够引导他去构建繁复的确定性,这之中,繁复只是外在的奇观,确定性才是内在本质。
换言之,诺兰的电影更像是一篇篇辞藻华丽、逻辑严密的论文,它们有着极强的可读性,有着丝丝入扣的结构,也有着对这世界斩钉截铁的某种论断。
但很显然,这套方法论可以用来叙事,却很难拿来写人。
特别是面对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被种种不确定性笼罩的人物,所有以追求确定性为终极目的的方法论将通通在其面前失效。
也正于此处,诺兰看见了理性的局限。
《信条》里有句话,“不要试图去理解它,感受它。
”当初听到这话时,暗自觉得,这是诺兰讲给自己听的。
因为某种程度上,《信条》的“失败”恰恰在于它把逻辑置于感受之前,使逻辑成为了感受的前提,而影片建构的游戏规则又实在过于复杂,使得感受根本没有机会登场。
于是,诺兰让片中人说出那句话,与其说是对观众的善意提醒,不如说,是对于影片缺陷的一种内省的自嘲。
我甚至会认为,正是有了《信条》的失败,有了对理性发挥到极致后的无力的清晰认知,诺兰才有了挑战《奥本海默》的冲动。
这一次,他终于要去抵达暧昧了,但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水土不服。
02《奥本海默》里 ,诺兰明显在给影片降噪。
他基本放弃了从前那种对于显性的极致奇观的追求,转而采用一种内敛的、散漫的方式,去重新组织影片的文本和视听系统。
这种自我更新,一部分奏效了。
当精巧的叙事游戏被弃置,故事不再因复杂的时间线索而重组,换言之,当外在情节变得简单易懂后,我们似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去潜入人物内心,去感受那些喧嚣的孤独和无尽的仓皇。
这是诺兰从前的电影,从未有过的时刻。
在那些电影里,我们会在情节的迷宫里赶路,会在绮丽的景观前赞叹,却从不会为人物停下。
而在《奥本海默》里,我们第一次在诺兰的影像中,为人物驻足。
我们看见了有关这个人物的片段式的一生,看见了他对于宇宙隐秘本质的幻想,看见他在情感面前的愚钝和稚拙;看见他见证原子弹爆炸的一刻,那如泡沫般美妙又易碎的画面,以及随之而来的轰鸣,有如一柄钝斧,劈开了所有人的梦;我们看见他在鼓掌和跺脚声中,同时体认着英雄与恶棍那微妙难分的界限;更看见他不安地坐在听证席上,孱弱得像是个随时会蜷缩起身体的孩子。
但遗憾的是,我们看见了关于这个人物的一切,却似乎仍然对他所知甚少。
我们始终回答不出那个问题:奥本海默究竟是谁?
03对一部传记片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失败。
倒不是说,一部传记片非要给一个人物盖棺定论,让我们能简洁地定义他,并非如此,而是说,一部传记片的首要任务,是让观众对人物产生鲜明的印象。
这种印象未必准确、未必全面,但必须鲜明。
它可以是像《莫扎特传》《巴里·林登》《乔布斯》那样,围绕人物的某个突出的精神特质,做反复的试探与重现;也可以像《社交网络》《公民凯恩》那样,把看似冲突又七零八落的碎片拼装起来,最终呈现出人性的多变与脆弱的一致性。
然而,观看《奥本海默》,却形不成任何鲜明印象,他的面孔,自始至终都是模糊一片。
当然,这种模糊也不一定是坏事,它也可能意味着复杂,意味着暧昧,意味着影片真正抵达了那片人性的神秘水域,带回了鲜活的样本。
可是,这里面所讲的复杂和暧昧,却是一种清晰的复杂和清澈的暧昧。
也就是说,它势必还是要提供一些明确又自相矛盾的线索,令观众自一种罗生门式的彼此拒斥又紧紧缠绕的结构里,去体味一颗暧昧灵魂的左支右绌。
很显然,《奥本海默》并没有提供这样的玩味空间。
它以一种过于自我压抑的方式,淡化了任何一个方向上的情感流露和态度表达,但最终,它却并没有酿出有层次的酒,而是滑向了苍白、空无,成了一种无意义的白噪音。
04当然,我这么说,或许有些言重了。
从积极的层面看,诺兰确实在试图走出舒适区,进入到一种更去公式化的创作领域,向众多影迷所期待的“大师”进发。
但与此同时,积习的创作惯性却仍然在悄悄起作用。
这也导致了,诺兰一方面想要激发直感力,去触碰那些不可捉摸的人性暗涌,但另一方面,他过于发达的理智又在不断跳出来,提出质疑,继续去审视和控制创作的过程。
正因如此,《奥本海默》呈现出了某种割裂。
它既散漫,又精密,既像是信手拈来,却又高度自控,它一边不动声色,一边又横眉冷目,它既想要营造一种无数可能性共存的量子态,却又忍不住要去观测,得出那唯一的结果。
体现在影片中,诺兰一方面极为克制地去展现人物的一生,去不加评判地摊开所有重要的节点。
他对于奥本海默早年参与左翼运动的经历,不予置评;对他投入曼哈顿计划前后的欲望与道德的缠斗,缺乏描绘;对他战前战后巨大转变的内心动因,也语焉不详;以及,当他成为名人,不得已卷入到权力的漩涡之中,他一边想要捍卫良知,一边又难以抑制对于舞台中心的眷恋,这种矛盾深深摧毁了这个野心勃勃的人道主义者。
对这些,影片通通在意义层面将其悬置。
这似乎是一种自觉的后撤,为的是预留出巨大的解读空间。
但另一方面,影片又事先张扬地将这种解读空间压缩到了最小。
它不仅体现在片头就提出的普罗米修斯的寓言,基本就概括了全片的主旨——一个圣人的成圣与受难。
更在于影片看似碎片化,实则又精心布置的结构。
片中所谓的三条线,实际是以两场听证会为目录,来检索奥本海默的一生。
换言之,这种对于人生的回顾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在两个视角的对峙中完成的。
它最终彰显的是受害者的无辜与施害者的狡诈,是奥本海默的隐忍与施特劳斯的狂纵,更是哪怕已经“爱国敬业”至原子弹之父的地步,却仍然难逃权力的绞杀与清算。
这是被这一叙事结构所清晰框定的表达。
但也正是在这种强势的结构下,奥本海默其人被挤压至近乎扁平。
05他只能是一个圣人。
尽管影片还是给到了一些暧昧的线索。
其中最明显的两处,来自政敌施特劳斯和妻子凯蒂。
两人分别点出了奥本海默可能存在的另一张面孔。
凯蒂指责奥本海默的怯懦,指出他之所以放弃反抗,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他实际是在用一种自毁的方式,来赎内心的罪,博世人的同情。
而施特劳斯的指控要更为严厉,在他眼中,奥本海默就是个伪善的野心家,其战后的种种行为,无论是对核爆的忏悔,还是对氢弹计划的阻挠,通通只是一场表演。
他不过是想最大限度地攫取声誉,让世人永远记得他是“原子弹发明者”,而不是那个“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恶魔”。
这两种看法都是在影片结尾处释放出来的,企图去搅乱此前平静的叙述。
但实际上,它们看似多义,实则同义,看似矛盾,其实统一。
它们无非都在把奥本海默推向神坛。
其中凯蒂的叙述,与其说让奥本海默更复杂,不如说让他更纯粹了。
她把他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塑造成了自愿的受难者,这无疑进一步夯实了其圣人人设。
而施特劳斯的指控,看似铿锵有力。
可问题在于,在他说出这番话时,他已经被证实是个无耻之徒,所以他的话哪怕再有理,在观者心中也再难有说服力,而更像是在歇斯底里地泼脏水。
也正因如此,在妻子的确证和政敌的反证之下,奥本海默的圣人形象越发高大。
他的其他可能的面孔都渐渐暗淡,唯有圣光,依然闪耀。
06其实还是挺可惜的。
在《奥本海默》中,我看到了诺兰与过去决裂的决心,但迈出的这一步,终究有些迟疑。
从另一个层面看,这部电影也陷入了两种类型片的冲突之中,它既是一部人物传记片,也是一部政治惊悚片。
相比之下,其政治惊悚的属性还要远远盖过人物传记。
那么既然要拍系统对个体的用完即弃,拍科学精神在权力逻辑下的全面陷落,拍私欲如何打着正义的幌子,借政治迫害来实施报复,那么作为受害者的奥本海默,就势必会在这种单向叙事下被无辜化、圣人化。
这是这一类型预先规定的情境,另一类型很难从其内部完成突破。
至于政治惊悚的部分完成得如何,也只能说,它呈现了一种隐藏在公事公办和温文尔雅之下的冰刀霜剑,其惨烈程度,比我们所见要温和得多。
行文至此,基本写完了我对《奥本海默》的不满。
但与此同时,我还有另一番话要说。
在这些基于冷静思考的批评形成以前,我必须承认,坐在影院里的那三个小时,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我看到了电影正在以它的某种本来面目,素面朝天地朝我袭来。
那种直接源自于视听的巨大震撼,那种经由一幕幕影像连缀而成的有如长诗一般的隽永感,那一张张纤毫毕现的人类的面孔,那被恢弘的弦乐推向极致的命运被写定的瞬间,它们似乎都成为我不忍苛责的理由。
但我之所以仍然坚持写下这些严肃的意见,只因为,在当下能够值得被这样审视和书写的电影,已经过于稀缺。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就是我们目前能在此地院线里看到的最好的那类电影。
而这一点,也同时成为我此刻感到欣慰和难过的理由。
9 ) 看《奥本海默》
非常值得观赏的科学家传记片!
谢谢这部电影让我了解了近70年前的这位科学家的有关历史,看了网上网友们推出的许多关于这位原子弹之父的资料,感触良多。
诺兰导演的出色电影表现是亮点,但他用电影对历史做深刻反思的态度,更是值得夸赞。
电影中没有,但资料里提到的奥本在60年代去世前的电视采访中的话,更使我记忆深刻:
“我们知道世界将会大不相同,有人欢笑,有人哭泣,更多人沉默不语。
我仍记得印度教经文《薄迦梵歌》里写道,守护之神试图说服王子,承担起他应尽之责,为了让王子铭记心中,他展开了千臂然后说:现在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
10 ) 5个关键词、17场戏、6000字看懂《奥本海默》,无科普,纯解读。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3号厅检票员工」这篇文一共6000字我们今天会用五个关键词,来把《奥本海默》做一个拆分,让大家更清晰于诺兰这次到底想说什么。
以下正文部分会有严重剧透,建议还未观影的朋友,可以观影后对照着阅读。
一.黑白画面理解《奥本海默》讲故事的方式,是理解这部电影的第一步。
同时这个片子也是《奥本海默》最保有诺兰色彩的地方,他依旧在维持自己所擅长的陌生化叙事。
也就是让观众对此刻电影所呈现的画面的空间、时间感到陌生,让我们依旧会在这个历史书、新闻特稿书写过无数遍的故事里晕头转向。
诺兰这次以黑白的区别法,把电影里横跨20年的时间线和不同角色的视角,进行了碎片化的剪接,我们会先看到历史客观视角的某个结果(黑白),再看到他主观视角发生的过程(彩色),整个电影都在不断跳转和返回,然后再反复,比较准确的比喻是“时间和视角的套娃”。
那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只是炫技以对观众的戏弄吗?
当然不是,这些混乱,构成了这部片的表达基底,他有三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人物的宿命性剧情的悬疑化对利维坦的批判性1.宿命性这一点其实最好理解,奥本海默这个历史人物的矛盾性就在于他是二战后和平的缔造者,也是全人类的死神。
这一结果,在他整个人生过程中,或者说在他发明原子弹之前,总是有痕迹和先兆的,这构成了传记回溯时会产生的,最微妙的人物宿命感。
于是,电影里在不断的时间跳转里,呈现大量奥本海默成为“奥本海默”的先兆,比如一开始的毒苹果,年轻时的奥本海默,曾经有一次因为和老师的争吵,在实验室导师的苹果里注射了氰化物,也由他自己救下了将要吃下这个苹果的玻恩。
毒苹果在人类历史里的隐喻是很泛滥的,是诱惑了夏娃的禁果,也是开智于牛顿的力量,人们习惯将其用在童话里,同时代表着危险和文明的共同体,这很显然指向的是奥本海默本身。
还有那一句梵文“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诺兰让奥本在和情人琼亲热的时候念出了这句《薄伽梵歌》里的句子,彼时他还没有加入曼哈顿计划,但这句话所直白讲出的神之语言,和他那一刻赤身裸体偷情的人之肉体,同样也是他的一体两面。
更明显的还有电影一开始,普罗米修斯的那一段描述,这就更直白了,盗火者对应原子弹的发明(不过普罗米修斯这点的作用,绝对不止于此。
我们后面还会再详细解读)。
2.批判性电影中间有一段奥本海默和拉比的对话,后者说,“政府需要的,只是我们(科学家)作为一个预言家”(大意),奥本海默回答“是必须预言准确的预言家”(大意)。
预言这个词,就是这部片里形成批判性的关键要件。
因为时间线的打乱,观众拥有了一个先知视角,知晓那些预言已经发生,于是当我们再一次回头,看到过去奥本海默对于未来的预言的时候,那些对预言的轻视,阻挠,都自然成为了一种讽刺和批判。
当科学的预言和警告成为了现实,狂热成为了现实,民族主义成为了现实,片子里所有政治和科学的博弈,最终服务于的都是对政治利维坦的讽刺。
3.悬疑化这一点相对隐蔽,但挖出来是最有意思的,片子一共有三个悬疑点,由浅入深:第一个是针对奥本海默的政治阴谋,幕后黑手是谁?
第二个是曼哈顿计划中,通苏联的间谍是谁?
第三个是奥本海默到底对爱因斯坦说了什么?
(这点严格不能算悬疑,但同样是通过时间线先埋下答案,后揭晓答案,所以先列在这里,我们后面专门会聊爱因斯坦的写法)
第一二两点的成立,基本都是通过这种黑白画面打碎时间线的做法,来实现的悬疑效果。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幕是军方在曼哈顿计划实现之后,和奥本海默讨论当时谁是苏联间谍的问题,提出问题之后,突然画面切回了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第一次小型试爆的现场,第一句台词是有另一个科学家喊“福克斯,低头”。
这个福克斯就是那个间谍,两个画面突然构成了跨越时间的提问和回答,第二个画面里这句话,其实也是暗示福克斯对爆炸试爆的积极性过于异常。
即使你已经知晓历史,知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在观看时已经可以因为这种时间线错乱下的细节暗示,得到观影趣味。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不一一举例,大家二刷的时候,可以多注意一下。
二.奥本海默诺兰最惯用的手法,其实并不是大众认知的对结构的玩法,而是对人物的同一种写法——天使与魔鬼于一身。
从第一部《追随》中的Bill开始至今,诺兰电影中人物的道德立场往往是不分明的,他自己的道德立场一直都是认为“天使能堕落成魔鬼,魔鬼也可以变成天使。
”这点依旧被它贯彻到了《奥本海默》,或者更准确来说,是奥本海默这个人,完美符合着诺兰的道德立场。
诺兰几乎是全方位展现了奥本海默让人讨厌的地方。
一方面是奥本海默在工作中的傲慢。
这里用的是他与大卫·希尔的关系。
二人在片中的交集仅有两处,一处是奥本夺走了希尔记录的笔,一处是希尔递上不要对日本投放原子弹的请愿书时,他打掉了希尔手中的本子。
在奥本的眼里,希尔只是一个小人物,他对待他的态度带着一种无意识的傲慢,但正是这个小人物,却成为听证会上为奥本海默名誉力挽狂澜的人。
他最终的反水揭穿了施特劳斯的真面目,指出对奥本所有莫须有的叛国指控都是施特劳斯在背后一手操控,这本身就形成了对奥本前期傲慢最大的讽刺。
另一方面,是他对待家庭和女性的方式。
他和同事的妻子偷情,结婚后出轨,只顾自己事业上的成就,对妻子产后抑郁的忽视。
有一场戏是当他回家后开心的分享完自己的成果时,听着楼上孩子持续的哭声,他只对疲惫的妻子问了一句:为什么你不去哄一哄孩子?
最后一方面,就是他这个人身上的政治敏感度以及他主动利用政治去达成自己的目的的行为,这都让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显得尤为复杂。
比如在讨论如何追赶上德国的研究进度时,他主动提出了利用“反犹太主义”,在纳粹对犹太人的驱逐和追杀从普通人发展到物理学家,这意味着在期待一批德国犹太物理学家的逃亡,但这些人明明都是他的同胞。
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科学的天使,同时兼有魔鬼的一面。
三.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这个历史人物最具有写作魅力的地方,必然是他在制造原子弹这件事情上的矛盾感,他是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但亲手制造出了最可怖的灭绝武器。
而诺兰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呈现这种矛盾感,他只用了一个角色——爱因斯坦。
奥本海默一共和爱因斯坦发生了三次对话,三次都服务于了加强奥本的矛盾感。
第一次对话,发生在有人算出原子弹的链式反应,最终造成的危害可能是会燃烧大气层毁灭全世界之后。
奥本去找了爱因斯坦验证,爱因斯坦告诉他如果这个计算结果是正确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停下来,同时分享给纳粹。
最后的结果是算错了,这种可能性趋近于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哪怕身边的人对奥本强调这是个好消息,但他依旧毫无表情,甚至有一些不易察觉的低落。
不管是去询问爱因斯坦的行为,还是得知错误后的失落,这都是为了告知观众,奥本的立场,并不是建造武器,而是维护被迫的和平。
但他依旧为了和平“被迫”踏上原子弹研发的轨道,于是他的挣扎就成了宿命式的必然,这放大了个人的悲剧性。
第二次则更加突然。
那一场对话的背景是曼哈顿计划实现多年后,当时奥本海默正面临着美国政府审查的打压,有一个镜头是奥本深夜送走帮助自己的朋友后,爱因斯坦突然从草丛尽头走来。
他对奥本说:一个国家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的英雄,如果你觉得不公平,或许就到了你应该离开的时候。
但后来我们都知道,奥本没有选择离开,他选择留下。
这里爱因斯坦的突然出现,突兀得尤其不像是现实,我们也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这一次私密的对话,但这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爱因斯坦就是从祖国逃亡到美国而来,两人都是不受祖国政府欢迎之人。
他构成了奥本此刻的另一种选择,在对人物内心的处理上,这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二人的最后一次对话,发生在电影的结尾,也出现在电影的开头。
那时原子弹已经试验成功并成为终结二战的重要一环,施特劳斯邀请奥本海默来委员会任职,他在湖边捡起了爱因斯坦的帽子,问他“你记不记得当初我拿着那张纸来找你,我们计算出的链式反应有可能会毁灭整个世界,我想,我们确实毁灭了世界。
”这与其说是一段对话,不如说是奥本海默的一次自言自语,他是在说给自己挣扎的内心听,他一直被困囿于如何取得和平的矛盾,最终不得不在历史的轨道中被迫做出选择,而毁灭世界就是自己曾经做下选择之后留下的结果。
这份挣扎贯穿着电影的始终,同样也贯穿了奥本海默的一生,爱因斯坦在这段对话里对他说:有一天,当他们惩罚你到一定程度,就会给你端上鲑鱼和沙拉。
拍拍你的背,告诉你一切都被原谅了。
但他始终不会原谅他自己。
四.普罗米修斯本身普罗米修斯,在奥本海默这样的角色身上,是一个孩童就能识别出来的低级的隐喻。
但诺兰在片中放入了一句非常关键的台词,让这个隐喻瞬间复杂了起来。
在奥本海默被政府和麦克锡主义压迫的时候,妻子质问奥本:你觉得任由他们羞辱你折磨你,世界就会原谅你吗?
这句话无疑切中了电影一开始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口白。
但与我们理解的隐喻相反,他不是在说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和奥本海默发明原子弹相似,而是在说普罗米修斯后续被束缚在石头上的刑罚,是否并非被迫,而是当看到人类以火开始战争杀戮之时的愧疚。
这成了一种新的解读,他最终依旧服务于奥本海默的矛盾。
这种道德困境被以更具象的方式表露,普罗米休斯被铁链绑缚上悬崖,每日被鹫鹰啄食肝脏,奥本海默内心每天在经历一样的痛苦。
惩罚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人不得已之下自我的救赎,这是关于电影,关于命运的悲剧所在。
五.链式反应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了,链式反应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曼哈顿计划前期,有人的计算结果显示,试爆原子弹有可能会产生链式反应,链式反应指核物理中,核反应产物之一又引起同类核反应继续发生、并逐代延续进行下去无休无止的过程,最终整个地球毁灭。
通俗来说就是爆炸会一直发生,导致整个地球的大气层被点燃,世界末日来临。
最终验算的结果是算错了,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无限趋近于零”。
这件事在历史上已经很少有人提了,毕竟历史永远只会记住成功的结果,不会施舍太多篇幅去回顾当中的歧途。
但诺兰重新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不止是把它还原了,还用它来作了一个刻画奥本海默的“妙用”——“链式反应”是奥本海默整个人生的注解词。
我们都知道,爆炸在那一刻发生,然后瞬间结束,核实验成功了,链式反应没有发生,地球也没有被毁灭。
这是历史的事实,但在诺兰眼里,这显然不是奥本海默人生的事实,在奥本海默的人生里,爆炸没有在那一瞬间结束,链式反应发生了。
有两场戏特别明确了这一点,第一场是广岛被投放原子弹之后的,奥本海默对着洛斯阿拉莫斯的人演讲时,全场欢呼时,突然镜头剧烈抖动,后景和奥本海默的主观视角瞬间被白色的光吞噬。
核爆的场景在那一场狂热演讲中突然重现,现场出现了超现实的核灾难场景,奥本海默踩着焦炭化的尸体往外走,一路看到呕吐的男人,痛哭的女人。
这是他痛苦的外化,当他看到现场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时,他无法让自己自洽,出现了属于他自己内心的“核爆”,他突然意识到,真正的链式反应,不是物理上的世界末日,而是人类与人类的关系,由此开始了剧烈的转向。
而他是那片人类的大气层,正在被链式反应逐渐燃烧。
这场燃烧延续到了1942年,曼哈顿计划的12年后,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场戏,奥本海默被审查时的一场问话。
那段问话的内容是政府审查机构的律师,在不断套问奥本海默对于广岛原子弹投放的立场,奥本海默强调自己只是在那个时代下,去避免纳粹率先拿到原子弹的风险,但都被对方律师所打断,逼迫他说出明确的支持,或者反对。
在那场审查中,不论是反对还是支持都有各自的风险,况且那对于奥本海默来说都不是事实。
在那一刻,同样的超现实核爆场景再一次发生。
这里还有一个和当年对应的细节,奥本海默在面对真正的原子弹试爆成功那一刻,整个视听画面是静默的,他在静默中等待着爆炸的结果;而在这场审查的段落里,面对着所有的攻击或帮助,他也是静默的,他在静默中等待着另一个结果。
这依旧是奥本海默内心从1942年链式反应了12年的那场爆炸。
那一场戏之后没多久,审查结果公布,奥本海默没有通过,他起身接过了给妻子的电话,只说了一句话“不要把床单收进去”,这是当时他们在核爆试验前的约定,因为不能泄露结果,奥本对妻子说,如果成功了就会让你把床单收进去。
当年真正的试验当然在物理层面成功了,但12年后,属于这个世界,属于奥本海默的那场爆炸,失败了,那无限趋近于零的链式反应发生了,它永远不会再被停下来。
太阳依旧在每时每刻里朝夕轮替,大气层还在,但人类握紧的拳头,已经永远不会再松开了。
写在最后电影最后,奥本海默得到了爱因斯坦提醒过的未来,当他沉静着走下神坛,人们希望这位已经白发苍苍的死神,可以在勋章、鲑鱼和土豆沙拉面前原谅曾经的一切。
但此刻的政客们永远不会意识到,这早已不关乎什么谅解,那一声巨响也早已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普罗米修斯不会后悔盗火,更不会憎恨,他只会把自己永远绑在那块石头上注视着。
注视着人类在炽热明亮的火焰中,敲打着那支冰凉的即将刺入下一个人心脏中的利刃。
配图/《奥本海默》预告、网络音乐/作者/小哥,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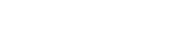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豆瓣打分是疯了吗……为什么我会觉得很……肤浅🥲🥲🥲
或许他们在谈论更重要的事呢?
这么多年了,诺兰还是只会用信息轰炸和反转来掩盖自己糟糕的character building和叙事节奏……这种手法的缺陷在悬疑片和科幻大片里常常由于过于眼花缭乱而被人忽略,但放在传记片里简直无处遁形…… 奥本海默不算难看,但诺兰哥的封神之路道阻且长(当然他永远是filmbros的神
一如《信条》,诺兰再次展现他对当下世界的复杂样态无能为力的软弱,这部电影的三个维度,冷战思维及麦卡锡、新型武器的战争伦理、左翼思潮的流行与覆灭,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无论哪一点深挖都会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然而每一点都蜻蜓点水、形同儿戏。作为全球顶级商业导演,诺兰可以拥有一部毫无必要呈现为三个小时的冗长制作的最终剪辑话语权和院线排片率,以及一亿美金的宣发费用,用最为商业的形式诠释何为“不商业”。
这不是在讲述英雄的故事,只是真实地谈论虚伪、真实、矛盾的人性。
终于看了70mm Imax版,三小时的片长可以砍三分之一,喜欢《教父》的人一定很喜欢这部电影,非常个人英雄主义,非常mansplaining🤣🤣🤣1,一个4000人的项目,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成败全是奥本海默,他就是个project manager,为什么把他拍成了神?2,他毁灭世界的纠结也是ego很大,他又不是杜鲁门,能够决定是否发射核弹?说他是普罗米修斯也太过了,他充其量就是那个火种;3,大场面镜头很少,大部分都是人物特写,不理解诺兰为什么要用IMax,纯属浪费。总结就是:炫技大于内容,并未见多少深刻洞见,吹诺兰也有个限度,这部就及格而已。
交叉叙事本可以用于解构围绕在名人身边的光环,并彰显出传记叙事中的表演性。但诺兰不是拉莱因,他的[奥本海默]就像是一幅耶稣受难的拼图,明明显而易见,却要剪碎成一块块时间碎片,拼成与公众认知一模一样的圣人形象供人瞻仰。奥本海默这个人物本身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他的科学研究本来就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指挥枪,因而他人物道德上的复杂性最终注定要被扫进政治立场的地毯下。电影叙事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塑造出一种大卫迎击歌利亚之相,仿佛他是个在政坛中身不由己的悲剧英雄,最终是一种精英主义式的天真,仿佛置若罔闻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美德。
从没看过一部电影,在倒数、成功、欢呼结束后,让人感到席卷而来的无力与绝望。
又是全片轟炸配樂,諾蘭現在沒配樂是處理不了戲了嗎這麼沒自信?也就發射原子彈之後(最後一小時戲)才有兩三場戲配樂和sound effect有其成效,之前的倆小時大部分時間皆是在虛張聲勢,抽掉配樂光看戲本身甚至毫無神采,只是平庸異常的流水帳,看到睏。
上班一天继续看你们开他妈三个小时会是吧?
脆弱的大男子主义
我到最后只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思考了宇宙之后,被这个世界拉扯的样子。
3.5;炫技奇观+铺天盖地的配乐一如既往,且因对话过密导致镜头切得偏碎,接受海量信息时会导致感受过载,与追求内化处理倾向相悖;科学家的理想主义天真仍属表层化,政治“站队”、如何面对核武的诞生和运用,都可抵达更深层。剧本结构密实,以听证会为切入,套层回溯往事,纷繁闪回+视点流动+色彩区隔,缝原复杂背景下的多维人物,观众接收到的是局部信息,正因为受限视野才让多义成为可能。“这不是一场审判”,是所有碎片朝向决定性时刻汇聚的历程——无论是日常事件积淀的人格/政治态度形成,还是众生在历史思潮中的顺流转向,甚而想象核爆内部的过程,都在逐渐朝向静默中爆发的一刻,在这之前你要忍受无数暗淡时刻;这种爆发,略去直击场面,而代之以失语、失声、过曝以及延宕的沉默,此刻死神所及之处的灰烬与空无才是最好的表述。
没看,但是这种全男宇宙本来就是对女人的挑衅🙂
本来是想打三星的,看你们吹的这么离谱改两星了。
诺兰这几年的电影一路看下来,感觉他的风格辨识度越来越高,作者电影的属性越来越强,不管他拍摄什么题材,最后都是与众不同的诺兰电影。以前大家说他的电影,配乐声音太大,这部还是一样,配乐在电影中不仅是外化了主角的情绪,同时还控制着戏的情绪和节奏,时刻操作着观众最本能的生理反应,明示观众该有怎样的感受。诺兰对于配乐的理解有他的那一套,像是在艺术和商业中寻找平衡点。其实他的导演风格也是如此,他是当今好莱坞导演里视听语言功底深厚的极少数,可以用商业电影的思维去运作任何题材,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中间寻找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包括《奥本海默》这种台词量巨大,骨子里很文艺的类型。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加,这种比重的权衡与拿捏所带来的电影的观影感受,也变成了他的作者风格,而《奥本海默》属于能凸显导演视听技巧的那一类。
这是一部适合装腔人士的电影伟大的殉道者+宏大的叙述战争、政治、权力……味道很正
诺兰的奥本海默和起点男频爽文的区别是有一大堆好演员给他撑场子,以及他没有给大招写运作原理的能力。另外,几年没拍电影就跟不上时代了么?朋友你哪怕百度一下都能看到即使在那样的年代,曼哈顿计划中女性科学家作出的成就也是名头响亮的,但在2023年的今天却可以在一个长达3小时的电影里被抹杀得只剩下标签,而留了点空间去刻画的凯蒂和琼也没好到哪里去,除了晒床单酗酒偷情外加给男主进行一些必要的pep talk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有意义的事可干啦!还声称“电影的扁平化处理可以理解”?wow现在的粉丝扯起来真是一个比一个能唬人。
对不起,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眼中的好电影。准确地说我对诺兰比较失望,在五十多岁依然保持一种浅薄的自恋。奥本海默是一场简单的炫技,为了让一切看起来复杂晦涩,本质上却是不堪一击的肤浅。而这不妨碍观众的狂欢,他们变成了一个个新的诺兰。就这样吧!
1、先不说女性角色多扁平多花瓶(一个红玫瑰蚊子血一个贤妻良母默默奉献最后还杀出来护夫扬眉吐气……)2、诺兰真的老直男,最后讽刺李维斯人家根本没说你,秒穿越韩寒邓超电影里的抖音水平爽文剧情,小直男们看得一起高潮。3、从炸前的坚定甚至说服这么多人到突然一炸后困惑太急转弯了,我跟不上。4、这不是3D炫技片啊,为什么穿插这么多PPT讲课般的碎片画面,我还期待导演试图在爆炸的时候教会我科学原理,但它们只是碎片……5、最后半小时把战争、科技、政治多维矛盾讨论全落在小鸡肚肠科学家宫斗上,我为奥本海默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