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剧情介绍
阿桃(张静初 饰)幼时目睹父亲被炸死受到刺激,之后人就变的傻乎乎的。长大后姑姑阿水(李丽珍 饰)把她带到自己在中国经营的按摩房帮工,阿桃的纯真引起了光顾按摩房的黑帮老大沙巴(李修贤 饰)的好感。在一次警察的追捕中,阿桃误闯进瑶族男人阿夏(张家辉 饰)的家中。阿夏靠街边的卡拉OK生意为生,阿桃的好嗓子让他看到了新的商机,而阿桃则因为阿夏额头有一颗和父亲一样的痣而认定他就爸爸。阿夏的生意因阿桃的加入明显好转,小摊前要求和阿桃合唱的人排起了长队。在阿夏与阿桃相处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阿夏因有好色之徒占阿桃便宜而大大出手,阿桃也因为阿夏和情人阿花亲热而发怒。沙巴一直牵挂着纯真的阿桃,他决心要收阿桃做干女儿。沙巴的手下绑架阿桃之后,阿桃意外看到沙巴开枪而对他充满恐惧并逃回阿夏身边。沙巴并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故事因为沙巴的坚持而复杂起来。 本片由...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王牌校草彩虹的重力赤警威龙神曲奏界Polyphonica你教会了我什么最重要遥远的家凤梧洞战斗我的抗战之铁血轻奇兵碟仙玩偶国家宝藏十品官吴山羊惹火甜心别想跑摇曳露营夺命高楼基因危机:天才科学家的五日女兵切尔西将死之人女同志吸血鬼杀手苍之彼方的四重奏灰姑娘职场记疯狂72小时七个秘书我的女神第二季缤纷之翼追凶:黑夜狩猎者第二季第五大道第一季爱你入胃地面师怪侠一枝梅屋内下雨狐闹干探
《红河》长篇影评
1 ) 《红河》:让河清澈的是鱼
章导是一个聪明的导演,故事的背景总是人们不太了解的陌生之地。
有着强烈的人类学情怀。
那些不被人关注的孤山远水,那些尚未商业化的山民寨子,还有,那些没有被这个欲望肆虐的世界吞没的纯朴人们。
红河,是清澈的。
让它清澈的不是青翠山幔,不是隐隐修竹。
而是其中的鱼。
这部影片也是一样。
瑶家传统的婚俗固然美得让整个影院静默无声,男主人的家乡固然美得让人忘记世俗。
但是,最美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与他们的情感。
阿桃与阿夏的爱情,是故事的核心线索,他们的故事非常的脱俗,从天而降的傻女,没有欲望的相处,他们甚至没有谈恋爱的过程,既没有80年代的你追我赶,90年代的四目相望,十指相扣,也没有21世纪的爱情动作大片中应有的惊心动魄。
他们有的只是,所有最自然的相依相伴,危难相济。
张静初在云南首映式上说道:看完这个片子,许多男同胞说——娶一个越南弱智MM也很不错。
我在观看时,身边的MM一个劲地说:太贤惠了,又刷地板,又洗衣服,还帮忙赚钱。
我想,能同时征服两性观众,这个智障MM着实不简单。
要是我是男生,我也会娶她:不提要求——甭管房子多少平米,人直接可以躲柜子里,不事儿,听话,偶尔任性,但属于爱人的表现,——如因气恼阿夏和别的女人鬼混,扔掉了阿夏的鞋子,对于一个智障的女孩子而言,没有比这个佯狂发疯的举动更好地表达她爱上他了。
在逃亡过程中,在清澈的小溪里冲凉,她把他的鞋子当小船,漂走了,她后来给他买了一双。
还记得那个镜头么?
火车将他俩隔在铁轨两侧,因寻不到阿桃的阿夏心急如焚,火车开走了,阿桃捧着鞋盒笑吟吟地出现在他面前。
对于两个极具个性的主角而言,编剧和导演将他们的爱情细节设计得匠心独具。
阿夏(张家辉)在首映后来到现场,观众的呼声代表了对他的喜爱,阿夏确实如抓他的民警所说一样,只会玩女人,花女人的钱,可是,他有许多有钱人都做不到的可爱之处:他仗义,在从阿水那里借走阿夏为其路边卡拉OK配唱的时候,遇见有歹意的混混,敢于上前,虽然,最后还是阿桃自己一麦克过去把人撂倒;他重情,前女友路过他的歌摊,他情不自禁,被前女友大款丈夫侮辱后,痛哭流涕,这其实,是一个男人最感人的时刻,女人固然也嫉妒,但嫉妒是源于这个男人值得爱,重情,就是值得爱的见证,阿桃连这层嫉妒都可以免去,直接就妾心似君心了,哭得比阿夏还让人心疼。
从此,这两人要是不好上,就不符合情感逻辑了。
阿水,由风情万种的李丽珍扮演,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角色,她是属于真实得可爱的那种人,属于池莉所描述的那一类人——有一种市井的风尘感,但更多是属于万家灯火般的世俗温暖。
她对阿桃,其实是保护有加,后来,我们也看到,她并不是卖阿桃,而是为了给沙巴做干女儿。
其实,对于阿桃来说,最需要的可不就是一个父亲么?
一个人在某个情感空间受了伤,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弥补这个感情的洞,阿桃喜欢阿夏的,可不就是阿夏眉头的那一颗痣?
这颗痣也长在她爸爸——那为了给她找风筝而不幸被地雷炸死的父亲——的眉上。
很多人很疑惑,为什么阿水为什么事先不告诉阿夏说,沙巴不是买阿桃为妻。
其实,道理很简单,她想知道阿夏对阿桃的真实感情,她对此好奇,因为她也爱阿夏。
而当她想说的时候,阿夏误会了,瑶寨公用电话亭的交流,是阿夏先挂的电话。
当然,所有的理由,抵不过编剧想这么写。
剧情的张力就在于此。
沙巴其实也是一个很理想化的黑老大,他并没有将武力滥施于阿桃,他对阿桃的方式区别于他对待其他人和事的方式,不了解他的手下把阿桃抓来,绑在椅子上时,他一枪崩了狗腿子的腿。
他对阿夏也不是情敌般的较量,实际上更像一个父亲与不成器的女婿间的对话:阿桃对我很重要,你想带她走,你能给她什么?
……正如阿水说的,阿夏,你太冲动了。
可是,如果不冲动,什么都条分缕析,那还是爱情么?
这是埋伏的命运安排给他们的悖论。
别拿杜拉斯的情人来做比,这不是一个欲望的故事。
乡愁是有的,亚细亚的孤独是有的。
但这更是一个有着中国水墨精神的影片,记住:让河清澈的,是鱼。
让我们再安静地聆听脑海里反复回想的这首民歌——红河里有两条会唱歌的鱼一条叫阿香 一条叫阿山阿香是阿山的新娘阿山是阿香的新郎……………………补遗:我在现场最想问的四个问题——章导演——为什么您的电影,都有少数民族情怀,这和您的生活经历或读书偏好有怎样的关联?
张静初——所饰演的这些所谓的问题女性,会给自己的性格带来怎样的转变,入戏,是专业素养,那么,出戏时,怎么调整?
张家辉——走上大银幕后,还会演电视剧么?
作为少数转战成功的电视红人,有什么心得?
李丽珍——您的《千言万语》是我最喜欢的港片之一,为什么后来没有加固这种转型的力度?
期待你更多更好的表演。
2 ) 哑默的回响
不要管海报上的恶俗煽情,也不要管IMDB5.6的评分,甚至也不用管不咸淡的剧情,这其实是一部挺有意思的电影,主要故事设定在97年云南的一个凌乱、嘈杂的边陲小镇。
电影里的声音是越南话、云南话、张家辉蹩脚的普通话、低档音响里的路人歌声、张静初美妙的越南童谣、老Beijing牌电视机里97年中国对伊朗的解说、暴雨和溪水……电影里的人物是一个智力障碍的越南小姑娘、一个潦倒的靠在路边赚一首歌一块钱的卡拉OK摊老板、一个经营越南小妹按摩的迷人老板娘、一个跟美军打过越战的独腿黑帮老大……电影里的画面是喧闹熙攘的小镇夜市、破旧的招牌、农用三轮车、杂乱的建筑、不洁的街道、整面墙的风中着响的玻璃窗、铺着芦苇凉席的钢丝架床、素色麻布衣服……电影里没有通常中国电影里的脸谱化反面人物、刻意逢迎的笑脸、阴谋诡谲、绕不开的血缘纠葛、愤世嫉俗的恬噪、可疑的正义力量、诉说与渴望……甚至没有掩饰、没有欺骗——只有说出的和未说出的,电影里的朴拙、多余都以纯粹真实停在那里——勿需流露,只是平和而自然存在。
这是一部真诚的电影,一个真诚的故事,这种真诚令人忧伤,因为这样的毫无修饰的真诚在今天几乎已经消失殆尽——这或许也是导演将故事放在十几年前的原因,尽管在场景上,在今天中国的有些地方依然可以找到,但人已经改变了……所谓物是人非,就是《南京南京》海报上那些手挽手的中国士兵,已经难以毫无保留地去信任。
这是一个执着于表达而遗忘了观察与发现的世界,留在我们眼中的梁木。
3 ) 谁都伤心过,那个没有
平安夜的凌晨,不睡觉。
看旧片,和旧友聊着天。
探讨起所谓喜欢。
排除了所有的外在,是不是才是真正的喜欢。
看外在,他不是完美的男人,只知道玩女人,穷困潦倒。
看外在,她更不是完美的女人。
她连话都说不完整。
但是,就是爱你,有什么理由呢。
那么平凡,却那么真挚的爱。
那么多真挚,我们只是看不到。
那么多不完美,我们只是没有勇气去坚持。
我想,这样的不完美,是要让你相信,自己的不完美,也是美的。
于是,我们都陶醉在自己的不完美里。
相信那并非没有意义。
就像安娜,要选择死在车轮下,相遇那一刻的车轮。
4 ) 如果这股感动来得蓄谋已久
如果电影没有被盖上诸如“中国《情人》的生死悲歌”之类的帽子,我想最后那幕现实中的“咬手指”戏会让我哭出声来。
(DVD封皮的广告总是会不自觉地感染到人不是吗?
)并且张家辉张静初李丽珍无疑都贡献出了相当优秀的表演——张家辉已不用赘述,我无数次的为这个男人感到心软和母爱泛滥(很囧但是事实);张静初虽然还是太过用力,但在这里反而恰到合适,纯真的眼神让阅片无数的干爹以为她刚演完《孔雀》不久。
当然,所有不圆满的爱情都会让我感到难过。
无一例外。
5 ) 红河:以父之名
我不谈电影本身,只谈电影背后的话语。
序幕,父親的離奇死亡,正如阿桃的離奇智障。
電影似乎沒有告訴我們,阿桃是原本智障還是受刺激生病。
父親為了撿風箏誤入雷區,最后有意無意被雷倒,也讓觀眾雷倒。
無心硬傷也好,有意安排也好,電影的序幕即是離奇。
阿夏為了逃避情傷,混跡與中越邊境,不愿回寨子。
這段感情,我們只能從阿夏口中得知:原本他們情投意合,美國大片來了,沒人看滇劇,小悅就嫁給一個昆明老板。
小悅的出場,是一種曖昧的誤會,唱歌,歌詞的影射,丈夫-老板在幕后,出場,撒錢。
一切都在暗示,阿夏只是自欺欺人。
也許從來沒有什么愛情,沒有美國大片的沖擊。
就像那個阿花,昨天還說愛他,今天就要拿錢。
中越邊境,也是我們觀眾和電影之間的邊境,真實與虛擬的邊境。
沙巴老板同樣是個離奇的人。
他喋喋不休地重復自己打過越戰,殺過美軍,諷刺的是,他靠走私美國煙發財。
有一句很重要的對白:我從來不殺沒有反抗能力的人。
于是,他用美式手槍打了敵人的腿,這一槍也嚇壞了阿桃。
后來,他對阿夏也堅守原則,沒有拿他的命。
可是,阿桃不能承受生活的重復——重復地看到父親之死,重復地看到手槍在行兇。
令人驚訝的一幕出現了:注意,電影給了我們充分的暗示,智障的阿桃將用手槍擊斃沙巴(她未來的“父親”)。
所以,我們需要驚訝的,不是情節,而是另外的東西。
沙巴在所有人物口中都是壞人,與之交易的阿水,身為公安的老鄉,普通人的阿夏都一致認可。
對了,還有那一群被嚇壞的妓女們。
這個雷人的安排,從反面看出沙巴的孤獨,以及阿桃的異常。
只有阿桃沒有害怕、恐懼沙巴。
這大概可以解釋沙巴的離奇決定:無兒無女又富裕的他決定收養智障的阿桃。
這是一種當父親的愛欲,不是阿夏以為的庸俗男人的性欲。
沙巴沒有戒心的將手槍放在顯眼的地方,正是源于父親對女兒的先天信任。
我們已經逐漸靠近值得驚訝的某物。
智障的阿桃猶如動物,不懂計算,容易滿足。
唯獨一點,她的欲求比任何人都強烈和瘋狂:父親。
這種愛欲只有人才有。
她的生命,一直停留在父親死去的時刻。
她始終是個女孩,需要父愛的保護。
愛的反面是恨。
阿桃憎恨暴力,恐懼閃電打雷。
本來,沙巴與其他人一樣,在阿桃眼中是無區別的。
她一視同仁。
她的世界遵循兩條簡單的區分標準:父親與非父親,暴力與非暴力。
沙巴想當她的父親,從一開始便是不可能的。
沙巴與父親毫無關聯(我們將會看到,事實上是有關聯的),阿夏卻與父親外貌相似。
糟糕的是,沙巴那一次無害的槍聲,徹底中止自己渴望的父女關系。
阿桃不再當沙巴是普通人,他成了暴力的化身,惡的力量。
老鄉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瑤族人忌諱年老結婚,沒有結婚的死后不能進入祠堂。
阿夏在結局的迷幻中不顧一切地超越邊境(我們一直強調這個詞),他同時也在穿越愛與死的邊境。
阿桃的歌聲在召喚他,對于靠經營卡拉OK為生的阿夏來說,歌聲是生命的隱喻。
我們也大抵感受到電影的暗示,那是阿桃的離奇結局。
在分離的最后一刻,阿桃狠狠地咬了阿夏的手指,這是一種儀式的契約。
阿桃從儀式的外部觀看者進入儀式的內部,成了儀式的實踐者。
這種從外部進入內部的強力,也把阿夏從中越邊境帶回古老的家鄉。
瑤族寨子的傳說。
從過阿桃,阿夏得以回歸家鄉的祠堂,這是獨一無二的重生。
從自欺欺人的自我放逐,回歸到囚禁中朝向他人的自由之路。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值得驚訝的東西?
當我們都做好心理準備,接受阿桃槍殺沙巴的時候,我們遺失了什么?
當我們順理成章地見證阿桃與阿夏的感情發展,我們有錯過了什么?
還是父親這個名字。
銘記在阿桃心中的父親,除了血緣,還有愛,模樣,父親的經歷。
父親無可挽救地死去,父親不可尋回。
然而,可以有父親的替代。
沙巴愿意充當這個替代,他有真實父親相同的愛,相同的越戰經歷,相同的孤獨(甚至,相同的結局)。
父親總是處于誤會的陷阱。
阿桃卻把模樣相似的阿夏誤認為父親。
換言之,阿桃記得父親的表象,卻遺忘了父親的實質。
這種記憶是可疑的,因為它的來源是項鏈中的照片(至此,我們應該好好思慮攝影本身)。
如果說,沙巴是真正的父親的替代,他本可以是、將會是、甚至已經是她的父親。
就在這個瞬間,阿桃使用戰爭武器的暴力,將“父親”處死了。
這種類似俄底浦斯的遭遇現在重新降臨在中越邊境的女性身上。
更加離奇的是,阿桃事實上也處死了“父親”這個名字。
與此同時,她將阿夏誤認為父親也經歷了一種離奇的跳躍。
不再有父親,只有夫妻愛情間的約定。
從父親的親情之愛到丈夫的愛情之愛,是血緣的擺渡和逆轉。
一種瘋狂,注定是沒有起源的。
瘋狂只因瘋狂自身而在。
沙巴自愿充當父親的替代,從一開始便是雙重危險的替代。
父親注定要被殺死。
阿桃瘋狂地離棄父親,徹底破壞了原來簡單的世界秩序。
父親-非父親,暴力-非暴力的兩分崩潰了。
為了阿夏,阿桃殺死所愛的父親,成了所恨的施暴者。
真正遭到破壞的,是阿桃之前的生命。
一種世界秩序的坍塌,意味著一次生命的死亡。
阿桃的過去成了虛無,父親之名也成了空洞的符號。
這是一次無中生有的創造與重生。
暴力與血在跳躍的瞬間無盡地彌漫。
在瞬間中,發生著怎樣的事件與變異?
當以父之名成為過去,阿桃與阿夏以什么名義繼續余存在這個世界?
這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一個充滿反諷,美國幽靈無處不在的國度與時代?
越戰沒有結束,美國大片在侵略,什么才是真正的邊境?
國與國之間的差異何在?
如何避免暴力?
在逾越了電影邊境的此刻,我們只好停止書寫。
是時候回到電影的標題。
紅河:邊境之河,血之河,等待逾越的線,生與死的一紙契約,自我的鏡像……
6 ) 住在心底的鱼。
这是我熟悉的场景,连绵的山峦,窄轨火车道的小火车,放着土气卡拉OK的夜集,大裤衩劣质吊带裙塑料拖鞋,说着半吊子中文的越南人,长满热带植物的小路,突突的三轮摩托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行驶,这些是我小时候看过的,听过的,生活过的种种。
但故事却不是我熟悉的故事。
红河里有两条会唱歌的鱼 一条叫阿香 一条叫阿山 阿香是阿山的新娘 阿山是阿香的新郎 这首歌被成年的阿桃唱出,抹上了一丝悲凉的味道。
阿桃眼神清澈,表情天真,可是她的智商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地雷响爆的五岁,对父亲的记忆,也顽固的被定位在了额头那颗红痣。
落魄的阿夏和阿桃彼此遇见,那颗红痣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日久的相处也让他们的心越拉越近,但阿夏一开始并没有发觉。
他靠相熟的妓女满足生理需求,也和阿水保持着暧昧的感情关系。
直到沙巴要把阿桃带走,他的感情才呈现出了勇敢的一面。
看到最后我们可能会遗憾,如果阿夏一开始就知道沙巴的真正目的是收阿桃为女儿,那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但说不定沙巴的看不起会不会又酿下另一个悲剧呢?
他用枪指着阿夏的头说:你有什么?
你能给阿桃带来什么?
沙巴是不一定会接受阿桃和阿夏在一起的。
这段感情让我很感动的原因是,阿夏和阿桃其实都是内心很清澈的人,心底像住着一条鱼。
沙巴凶恶,阿水狡邪,在他们的世界里,不可能养鱼。
阿水去探监那场戏,当阿夏声嘶力竭地抓着栏杆吼叫的时候,阿水留下了眼泪。
正是因为她对阿夏感情的试探,造成了这个误会不可避免的产生。
阿桃的项链被阿水塞在了阿夏手里,不知道他攥着它在多少个白天黑夜思念着阿桃,因此在听到和阿桃一样的歌声时,不顾一切地越狱了。
但,那不是阿桃。
一个有着和阿桃相似声音的越南女子,晒着的床单在风中不断翻飞,也不知道,阿夏奔到跟前时,是怎样的失望。
导演对小人物的处理非常到位,细节尤其值得称赞。
张家辉饰演的阿夏虽然操着一口并不熟练的普通话,但那种流动卡拉OK小贩的小角色却被演得入木三分。
唱了几句机器就出现故障的客人要退钱,阿夏希望还能找回一两毛;给阿桃办暂住证,对民警说一分钱都没少我白找你了;抽烟时用两个指头前端夹住送入嘴里,这是底层的人经常用的姿势。
另外就是影片拍得很美,特别是开头那几幕,风景如画的越南乡村,河水缓缓流动,村民们撑着船驶过平静的河面。
————与评论无关的分割线—————1.片名叫红河,但片中出现的方言却都是昆明话,这一点上,要批评导演了解不够深入。
作为红河人的我认为这是本片最大bug。
2.导演的三部曲,讲的分别是元阳、石屏、河口,这三个县都是云南红河州,干嘛不干脆叫红河三部曲呢?
3.越南女子的传统服装真的很好看。
7 ) 适合在舒适安静环境中慢慢品味的电影
这个电影和《南京!
南京!
》前后脚上映的。
在电影院犹豫了两秒决定看南京。
事实证明,在电影院看《红河》,对我而言确实有点小浪费。
不是说这片子不好,只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更适合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安静的环境下,慢慢品味。
一个只有五岁孩子智商的越南少女阿桃偷渡来云南的姑姑开的按摩店做清洁工,无意遇到没有正经工作的四十多岁老男人阿夏,因为阿夏的痦子和帽子阿桃觉得他像去世了的爸爸,而阿夏发现阿桃的好嗓子可以帮他赚钱。
黑道老大看中阿桃要带走她,阿夏在救阿桃的路上被老大追上打断了一条腿。
老大带走了阿桃,阿桃用老大随手放在车上的手枪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警察赶到后,阿夏说老大是自己杀的,被判刑入狱。
阿桃被遣送回越南。。。
这个电影看完不会哭的死去活来,但是会有淡淡的感动长久的回荡在心中。
我记住的几个镜头:阿桃的好嗓子给阿夏的卡拉OK机带来不少生意,阿夏兴高采烈的点着钞票,抽出一张递给阿桃让她买槟榔,阿桃又顺手把钱塞进内衣里。。。。
躲避黑帮老大的路上阿夏的鞋子顺着溪水漂走了,阿夏光着一只脚到路边的二楼电话亭打电话给警局的同乡求助,电话打到一半发现阿桃不见了。
阿夏慌忙挂断电话跑下楼,最后发现阿桃抱着一些东西站在路对面,阿夏冲过去不由分说打了阿桃一下。
阿桃手上的东西被打掉——那是一双男皮鞋和一堆零钱。
我猜这堆零钱应该就是按摩店的客人和阿夏零零碎碎的塞到阿桃内衣或手里的吧。
事发后在警察局外面,阿夏被带上警车,阿桃追上警车并狠狠的咬了阿夏的手指一口。
这个镜头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这个礼节是云南少数民族婚礼上新娘对新郎“实施”的。
头脑单纯的阿桃,对阿夏的感情已经从觉得他像爸爸,到爱上他。
可是偏偏命运就是这么无情,“让我爱上你,却又让你与我分离”。
警车远去,一直温柔的阿桃那野兽般悲痛欲绝的哀吼久久回响。
看电影之前,红河是一种香烟的名字,看过电影之后我还记住了一首越南儿歌的旋律:红河里有两条鱼一条叫阿香,一条叫阿山阿香是阿山的新娘阿山是阿香的新郎红河里有两条鱼。。。。。
8 ) 感情受挫折,来根小红河
下班前心里有点乱,不想回家,又已经戒了酒,于是这个习惯用单双数和红绿灯乱下注又忠于结果的人终于跑出去看电影。
从来没有试过一个人去电影院里看,穿过空荡荡的地下停车场的时候,鞋子很滑,反正左右无人,有人我也近视我看不见,于是索性脱下来,地面很凉,但是竟然很干净。
到了之后直接排队去买最近的一场。
管它下一场是什么,赶上什么就是什么吧,人生不也是这样的吗。
安排好了就没意思了……很幸运,我遇到一个我喜欢的故事,这让我差点以为,它暗示着我也可以遇到我喜欢的人。
这故事有我喜欢的名字红河犹如记忆里燃不尽的烟,这故事有我喜欢的年代一九九七那时候我在哪里遇见谁,这故事有我喜欢的国家越南和大眼睛水瓶女,仿佛量身定做,很完美。
眼泪从爸爸两个字一出口就开始流下来。
人少,灯暗,那么不用擦。
爸爸。
爸爸,爸爸……这声音很微弱,但是一声一声招惹我,像对着悬崖,留下无数的回音,我很想他。
说远了。
说回电影本身……我一直在想,一个人是怎么样才能爱上另一个人呢?
阿桃和阿夏的感情里,一个更多的是依赖,一个更多的是保护。
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以前我一直想错了,以前我觉得爱很纯粹,可以凌驾于一切情感之上,所有的暧昧迷恋啊,相逢失去啊,大伤痛小温暖啊,都在它面前自惭形秽,避之不及。
可现在。
我觉得爱不是那么单薄清透的,它很厚重,包含了世间所有的情感,包括恨和不甘,包括酸涩和疼痛,包括依赖和保护,包括说不出口和下不了手,包括纵容和折磨包括所有所有。
但是它又并不复杂。
正因为它是多种情感的混合,所以任何一种情感都能变成它。
又说远了。
再次说回电影本身……后来我想,其实也许是电影剧本需要矛盾冲突来产生高潮才会有那样的结局吧。
如果平淡一点的推动,他们应该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又简单又快乐,就像阿桃的眼睛那一汪洒着星辉的湖泊,而她的歌声划破夜空,落在他的笑容里。
那该多温暖啊。
当我不再迷悲剧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老了。
9 ) 小人物 真爱情
这是一部悲情电影,一部描写小人物的悲情电影。
爱情不分国界,不分尊卑。
生活在南国边城社会底层的阿夏和阿桃相爱了。
他们一个是被爱人抛弃无牵无挂的浪子,一个是失去双亲无依无靠的孤儿。
阿桃用她的歌声,用她的纯真善良打动了阿夏本已对生活、对爱情失去希望的心。
虽然阿夏对阿水否认了他对阿桃的感情,但当他在道口发现阿桃不见的时候那份心急火燎;当他为了阿桃与沙巴一众拼死搏斗的时候,都已证明了他不能再没有阿桃。
他们爱的沉重,爱的真挚。
阿夏和阿桃语言不通,大部分时间只能用手势交流,虽然没有恋人间的卿卿我我,但当影片的高潮阿桃踉跄着追着阿夏,咬着他的手指的时候,已经胜过世间一切山盟海誓。
在真挚的爱情面前,有多少人有勇气与命运抗争。
阿夏和阿桃做到了,虽然命运如此残酷。
他们原本可以幸福的。
影片请来了张家辉、李丽珍、李修贤一班香港演技派明星的加盟,为影片增加了不少看点,也给影片增加了更多怀旧气氛。
张家辉一直是我比较欣赏的演员,他外形不差、演技不差,但正是这份中规中矩让他十多年来一直不温不火,扮演的不是小人物就是配角,还曾一度淡出演艺圈。
好在他执着的一路走来,今年更是凭借《证人》中绑匪的角色一举获得香港金像、台湾金马双影帝,也是对他从影生涯的最大肯定。
“能够演好小人物的演员才是真正的好演员”,他做到了。
10 ) 纯与真
在警察带走阿夏,阿桃发疯似的追上去咬阿夏手指的时候,我被感动了。
“掀盖头,咬手指”,是瑶族男女成亲时的礼仪程式——阿桃被阿夏带回乡时,曾经见过…… 无论是沙巴还是阿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都喜欢上了阿桃。
而阿桃,只不过是一个智力水平永远停留在儿童阶段的傻女孩而已。
或者,单纯、真诚,正是她的“致命武器”,忙碌、征战的人们,偶尔需要“丢盔卸甲”。
后来通过阿水的话,我们才知道,原来沙巴只是想收她作女儿;原来所有的逃亡与厮杀是场误会。
不知阿夏心底有没有懊悔过?
如果当初打电话的时候,他把阿水的话听完……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阿桃本是一面名叫“单纯、真诚” 的镜子,她映照着复杂化了的人们的向往与无奈。
既然她是这个复杂人世的“稀有品种”,也便终究难以久留。
篇末,阿桃唱过的歌重又响起了,阿夏追随着歌声越狱了…… 可是他永远找不到了——真人,真山,真水,美人,美山,美水,都成幻影消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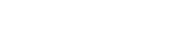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這裡的影片中是記錄下一個二千年前後時期的歌手怎麽以一首歌紅遍全球在講她的生平因為歌首首歌聲動人,感人心弦,像是在講大家的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