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剧情介绍
刚从瑟堡来的斯蒂芬,加入了巴黎93省圣德尼的“反犯罪特种部队”。在这里,他遇到了新队友克里斯和瓦达,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街区不同帮派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在一次出警的行动中,局面变得不可控制,而这个事件意外地被一架无人机记录下来,进而引发了更为剧烈的冲突。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青出于蓝乙女游戏世界对路人角色很不友好同居牢友王媛媛情事缉私档案为你抛却残忍的心皮囊第四季“大”人物国际空间站恶魔法官烽火硝烟里的青春暴劫青春我们无法阻挡2加齐号的攻击十二生肖城市英雄五个女儿暴力特快钢铁飞龙之再见奥特曼破坏神夜孔雀谢谢你医生天下同心控制午夜先生:小心怪物卧探屠龙女巫不存在高个夜魔后来的我们丹尼·罗维拉:还是值得交友网战
《悲惨世界》长篇影评
1 ) 通往主体间承认之路
总结一下的话要套后殖民话术,边缘群体的获得国家层面的承认不够而催生了动乱和不满,因为未能从正当合法的传统路径中获得承认,边缘群体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方式,如运动、暴力、反抗等重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迫使国家机器承认自己的存在。
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的权利是与所有人的权利所协调一致的,每个人对于他人都具有社会团结义务,对彼此负有最低限度的义务的承诺。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公民权利义务的意识首先从个人和其他主体的相遇生发出来。
孤独的自我意识遭遇了其他主体,此前知识纯粹认知性的问题转变成了由“为生存和死亡而斗争”构成的社会性故事。
主体意识到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就必定进入斗争状态。
自我意识需要得到其他自我的承认,主体间的承认构成了获得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
而承认在hegel的话语中是为了他者的利益而相应地限制某人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由此完成了从欲望到被承认的跳跃。
与主流的自由主义叙事不同,hegel的社群主义认为,自由王国作为一个公民自我实现的积极领域,让一个公民能够自由地对于自己的个性进行表达。
如果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权利,能在社会世界中主张自己的(实际上是由由国家保证的)存在,这反过来又成为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
他者形成了外在的客观建制,个体之间的承认被推广到涵盖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的实在的领域。
然而,当一个社会将自己的组成部分限定在不充分的自由中,会出现相应的社会病态。
个体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推移到个人与国家之间或者族群(利益团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时,就是国家层面上的承认。
根据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个人与国家对话、族群与国家对话的交往行为在合理程式内进行通常会减少摩擦,但是这种合理程式是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承认未能达到,程序理性会崩塌,摩擦性矛盾随即爆发,即个体对于承认的需求性抗争、运动、暴力等非常规的手段展现出来。
这一冲突爆发的合法性深植在法国民权运动的进程之中,早在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与公民权宣言》中就有所体现,该宣言从反抗压迫出发明确承认人民有“起义权”。
影片中主要体现的是互惠性的缺失——尽管少数族裔在巴黎的公共生活中承担了相当大的劳动和并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理应得到承认,然而少数族裔并未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和认可,并未真正被接纳到法兰西民族之中,没有得到来自国家权力层面的承认,拥有的只是和基层官僚之间的互动和群体内部的自认。
骚乱和动荡在长期不被承认的不平衡之下爆发,恰好是互惠性没有得到践行的体现——国家没有对于个人的权利进行承认,个人因此拥有起义权。
身份的承认和认同:在影片的开头,非裔少年伊萨在全法居民观看世界杯夺冠的氛围中感受到法兰西公民这一身份的询唤,感受到与姆巴佩作为有色族裔和片中的足球少年之间的联系,甚至感受到与马赛曲之间的情感联系。
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是否包含来自旧殖民地的移民?
开头群情激昂的狂欢场面与之后的动乱与暴力产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对位。
移民从未得到承认,即使在国家可以利用移民个人的能力谋利之时也有深深的沟壑如文化、观念、偏见阻拦。
移民被视为闯入者、错位者和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否与白人一致?
想象的共同体,即原住民对于外来移民群体的承认可能仅仅在影片的开始也就是非裔足球运动员为法国的国家荣誉添彩时存在,或者从根本上来说,不同族裔之间的相互承认的“共同体”从未存在过。
不同层面的承认与自认和否认:maire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是经由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白人警察之口、以讽刺的态度说出的,“巴黎的市长也是黑人”。
然而很快镜头切换到市集中的画面,白人警察尽管并不尊重作为黑人社区老大的maire,也不得不称呼其名称,并对maire对于黑人社群的有效管辖和公共空间中所处的地位进行承认。
Maire在黑人社群中的广泛影响力和自我族群的称谓构成对于市长地位的自认。
然而在抢夺储存卡的冲突中,黑人社群与穆斯林社群和警方的决裂恰好又将此前表面上的脆弱承认撕裂开,白人警察“c'est moi, la loi”的宣告和穆斯林群体的对抗直接构成对于黑人社群掌权者地位的否认。
狮子作为意象代表什么:幼年的狮子可以被人随意控制、抚摸而毫无反抗之力,但是一旦狮子成年就会成为无法控制的暴力源泉。
小狮子是非裔少年伊萨以及群体的具象,也是暴力的具象化表达。
平民在国家权力机器之下往往成为“经常沉默的、权力机器的目标”,然而当非暴力手段在失权者手中失灵,神圣暴力就会通过突然降临来填补历史的断裂。
主体间的承认广泛存在于家庭、社群和国家层面。
影片没有仅仅聚焦于街头暴力本身,而是对于参与街头暴力的个体所植根的土壤也有展现。
手持国家机器之暴力的警察在家中也是父亲、儿子,非裔少年在家中也会受到父母的冷遇。
在市民社会层面,暴力的运用和政府的缺位也恰好是国家层面的失衡。
“在一个个人有责任尊重比起的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民主的法律共同体之外,个人也被卷入了多种形式的家庭和工作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在这些关系中,我们显然获得了我们自尊的其他面向。
”对于一个新加入的群体,如果国家想要通过干预去改善承认的条件,可能存在侵犯其他领域自主存在的条件的危险,这也是国家权力在巴黎郊区的运行处处掣肘的原因。
非正式权力的行使和主体性的重新发现:阿尔都塞的主体性论强调,个体只有服从于一种实践规则和为他们提供一种社会身份的角色归属的体系,才成为主体,也即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和权利的人。
然而,这种对于顺从于已经确立的行为预期体系的自我观念的要求构成了对于社会支配的巩固,影片国家权力对于少数族裔守法的要求恐怕也是对于公民顺从与国家支配这一消除主体性的消极实践之体现。
相反,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正是通过对于合法的、正方的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突破或者说通过非正式权力的运作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
巴黎郊区处于国家权力这一正式权力的边缘,也是国家权力在具体行政单位上运行的细微触角。
然而在巴黎的93省,这一权力的运行并非想象中的畅通无阻,起码在运行时是通过迂回的方式。
非正式权力的运行是巴黎市郊的常态,国家权力通常以既强势又妥协、既侵犯又回退的态度介入巴黎郊区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未在巴黎市郊这样得到强烈的挑战和不承认,但是又在迎面挑战的过程中得到被动的强化和确认。
说明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确实是互动形成的,承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探对方底线和不断妥协的过程。
影片本身的站位和象征意义影片并不是从中产上层学者的视角来审视法国的族裔和文化的断裂,而是 以伪记录片的形式,将视角在巴黎郊区的底层人民的不同群体上不断切换,尽力客观地反映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历史的、殖民的、权力的、边缘的区隔和撕扯。
本片是左翼电影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后殖民电影的代表作,本质上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于自身所处的族裔中的记忆进行的传递。
导演和参与其中的演员并没有迎合精英阶层和白左叙事对于一个受压迫的族裔在幻想,而是以具备完全充足的主体性的态度探入到事件的发展、冲突和升级之中,尽力以个人的能力和能量来斡旋、调解以促进事情的解决,无论是否使用了合法还是非法的手段,是否使事情得到解决还是让事态愈发脱离控制,都可以看到充分调动主体性而不是被动接受事情发生的努力。
作为少数族裔,巴黎街区的黑人团体、穆斯林群体和吉普赛人群体在主流叙事中往往是被边缘化和想象化的,需要西方父亲般的维护其利益并加以管理。
尽管从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移民的劳动极大支撑了整个社会运转体系的底层,但是移民并未模糊明显的种族界限。
西方的权力仍然被谨慎地控制着,上到国家主政者,下到细微的社区层面的社会控制,异族人仍然被小心对待和隔离。
影片给我们呈现的恰好是权利与义务在个人与国家的承认层面的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古老的“权利-责任”范式是失效的,这可能说明了在政治哲学和行动哲学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现实的断裂。
这或许是对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制的过度迷恋所造成的承认制度的单一化,并不是承认理论本身的问题。
如果想要进一步理解甚至消弭影片中乃至现实社会中的断裂和冲突,或许需要从非正式关系的相互承认,从族群、社区等碎片团体和交叉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承认理论。
从2005年巴黎暴恐事件乃至发生在多个地区、多个民族文化圈层的冲突事件来看,政治权力通过广泛的、零散的、去中心化或者多中心化的政府或民间的组织网络来运作,这些前国家性的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道德原则并在国家权力下降之前就已经磨合运转。
社会正义的概念不仅应当遵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的定义方式,而是根据相互承认的要求来界定的,而我们必须以历史发展和已经制度化了的承认关系为出发点 ,识别业已存在的社会伦理。
2 ) 暴力对抗中的上帝视角
这是个除了异乡人之外没有闪烁着善良光芒的人的地方,这是法兰西种族矛盾的放大与缩影。
拉吉·利的这部处女作让人一下子想到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
同样是黑人社区中的种族矛盾问题,同样是由弱渐强直至不可收拾的暴力行动的螺旋式叙事,同样是审视所有人的客观眼光,只不过确实多了些“悲惨世界”的意境。
18年法国世界杯夺冠,大家纷纷涌上街头,无论肤色年龄出身,都在高唱马赛曲,披带挥舞着三色旗,在凯旋门前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欢呼雀跃。
此刻,他们都是团结法国人,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导演为这个问题打上了大大的问号,“Les misérables”跃然于欢庆的法国人头上。
小狮子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原本危机四伏的火药桶社区。
导演在整个无厘头失控事件中设置的角色很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将我们带入到某一个人的视角观察世界、考虑问题,而是让观众以完全旁观者的角色审视整个事件,而手持摄影带来的视听盛宴却又让我们身临其境。
Issa偷鸡摸狗的行为似乎让人无法在他遭受黑帮欺侮和警察的伤害与威胁时让人们对他产生同情,就算在他啜泣的时候有一丝怜悯,那么也会被最后的暴力报复抹杀得无影无踪。
泪水在这时不是孩子们面对不公的无力,而是浇灌仇恨的温床。
在警察角色上我们能确切地感觉到,导演难能可贵地有意将电影的主角们当做有着独立形象与人格的人,而不是符号。
作为白人警察的Chris歧视黑人,暴力执法,在出事后将重点放在无人机带给自己的名声损益上而不是救治小孩。
他俨然已成为悲惨世界酿造者中的一环。
同样,黑人警察Gwada有着与Chris相似的暴力的、没有同情心等特性。
但当Chris回到家中,他变成了受妻子宠爱的丈夫,两位宝贝女儿的守护神;Gwada回到家中,他变成了母亲面前脆弱的孩子,或许是内心的自责,对于同为移民后代的孩子的伤害,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黑人警察事后的一句“Putain!
”是懊悔,恐惧还是单纯的愤怒?
以及他怎样处理有着自己罪行的磁卡?
影片都没有给出回答,却在他归家时给出了模糊的指向。
最后警察由施暴者变为受害者,让人唏嘘。
而Ruiz作为异乡人,是良知的代表(虽然他也做出了包庇Gwada失职的行为)。
他不开下流的玩笑,制止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为受伤的小孩买药,威胁马戏团大佬射杀狮子等等。
但或许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抑或是缺少的魄力,他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被整个大环境推到了悬崖边上。
当他掏出枪来对准Issa时,电影的讽刺力度达到了巅峰,有良知的人首先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被迫与自己曾救下来的Issa对峙。
最后,良知是否会在Issa的内心中闪现,导演以省略作了答复。
电影中最独特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它的视角。
客观/上帝视角有了可以具象化的东西——无人机。
当然,戴眼镜的小男孩同样也被塑造成偷窥狂和受警察侵害的中立形象。
巧合的是,在没有无人机的情况下,他依然在最后的大混战中通过猫眼成为暴力事件的观察者。
从无人机到猫眼,男孩的视线发生了变化,视角却没有中断,依然与观众同在。
多次俯视镜头,让我们重新审视着人们,审视着城市,而中间无人机视角下的夕阳,却代表了每个人心中柔弱的一面与尚存的善念。
楼道内的战斗却摧毁了这一切美好的希望。
此外,另一个很独特的情节设置是暴乱前一群玩水的小孩向车内呲水。
从呲水枪到燃烧瓶,从笑脸到怒容,两种“暴力”的相似性有多少?
暴力对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是肮脏社会环境的恶果?
导演以《悲惨世界》中的话语作为回答,也作为影片的结束。
“从来没有坏的杂草或坏的人,只有不好的种植者。
”现如今已不是雨果先生时代的法国了,但他的话依然振聋发聩。
05年的暴乱有什么用呢?
无疑是种植者的又一次失手罢了,但流血的却是人民自己。
3 ) 悲惨世界
在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语境里,片中警察混乱中开枪打伤小孩,基本算是正当的。
这帮小孩的野性和不可控,是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不能接受的。
西方法律或公民意识里对执法行为的合理性与边界线的争议,在我们这通常被简化为“你有没有配合执法者”的问题,没有,就是你的错。
片中宗教和种族对立的移民社区,人性自由伸展,维持基本生存法则,在剑拔弩张中保持和平。
这种管理方式,有点类似于西方初期对待疫情的态度——既然接受了不能(短期内)绝对控制的现实,那就采取措施防止它彻底崩坏。
对待人性亦是如此,他们接受了人性复杂的现实,不去试图完全控制它,而是防止它沦落到法律不能容忍的程度,因此西方能够允许片中那样的移民社区存在。
这种文化差异,正是我们的主流社会,不能接受难民或是那样的移民社区明目张胆存在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一切都可控被控。
4 ) 殖民主义种下的恶果
导演通过风格写实的镜头一改人们对法国的浪漫印象,故事简单到用“偷窃事件引发警民冲突”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充斥冷峻暴力的镜头语言下带观众目睹了整个法国社会矛盾的缩影,说白了都是殖民主义种下的恶果,移民、宗教、种族等遗留问题汇聚在一起时,才真正构成了现实中的悲催世界。
滥用职权的秃头警长会假借搜身之名偷吃路边姑娘豆腐,嘴里说着姆巴佩太飘,自己的行事作风却更飘,不仅作威作福还明目张胆的暴力执法,在他眼里那些非裔移民都是来自底层的病毒。
而黑人警察瓦达虽不似秃头那般嚣张却也十分高傲,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他信奉的原则是以暴制暴,即便是手无寸铁的小孩他依然会狠心的按下手里的枪,而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情理之中。
男主斯蒂芬是这群疯子里的一股清流,然而随着事件发酵他也被周遭的暴力所同化,从一开始的商量也逐渐变成了威胁,直到故事的最后举起了手里的枪。
电影里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值得可怜的,被暴民围堵的警察是暴力执法的自食其果,而黑人小孩也是这种暴力环境下滋生出的刁民,导演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许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恶心循环吧,穷山恶水出刁民并非全无道理。
5 ) 《悲惨世界》告诉我们,法国会被移民玩完
影片《悲惨世界》(2019)告诉我们,法国好不了,会被移民玩完。
要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只需关注影片中的几个细节足矣。
影片情节的起因是吉普赛人的马戏团有一只幼狮被窃,目击证人说是一位非裔少年所为。
于是,吉普赛人兴师动众地来到非裔社区,向“市长”(当地的黑帮领袖)讨说法。
幼狮被窃,只是一般性的治安案件,按照天朝人民的想法,有困难,找警察。
但是,吉普赛人闯荡过江湖,世事洞明,知道报警有一套流程,人家愿不愿立案难以预料,立了案什么愿不愿投入警力也不明确,投入警力能不能破案更是不可指望。
于是,吉普赛人选择了最民间,也最高效的方式:开车在非裔社区巡游,通过高音喇叭,对偷走“强尼”的人进行恐吓和诅咒。
当然,吉普赛人在广播时犯了一个错误,对于信息的披露不够完整,且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
高音喇叭里不断强调“强尼”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偷走“强尼”的可怕后果,却一直未说明“强尼”是一只幼狮,而是默认全世界都知道“强尼”的真实身份。
进行了宣传造势之后,等于广而告之,“我”丢了“强尼”,“我”很愤怒,后果很严重,这就占领了道义的高地,可以文攻武卫。
于是,吉普赛人拿着棍棒,光着膀子,露出凶猛的纹身,逼迫“市长”交出“强尼”。
“市长”作为民间推选,且得到了警察认可的话事人,有一定的江湖地位,面对对方的嚣张气焰虽然内心有点慌,但考虑自己的身份,尤其楼上有老人在观看,认怂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肯定不会有民主融洽的交流氛围。
甚至,“市长”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强尼”是一只幼狮。
可见,吉普赛人虽然才艺出众,武力值爆表,但毕竟没有受过礼仪方面的培训,与人交涉时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
一场群殴事件一触即发,三位警察及时赶到才平息双方怒火。
“市长”虽然看在警察的面子上答应找“强尼”,心里是不以为然的。
他一直牵挂的,是他的父母在楼上可能目睹了这场争吵,也不知他的形象会不会受损。
三位警察也看出来了,“市长”对于找幼狮这样的小事不太上心,于是派鲁兹向萨拉赫打探消息。
萨拉赫是前圣战分子,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恐怖分子”。
当然,萨拉赫现在已经从良了,开了一家餐馆,平时以精神导师和良心厨师的形象出现。
他店里常驻几位大汉,乃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这个兄弟会是民间的“反犯罪大队”,专门负责调解纠纷,处理违法事件,当然也包括对少年进行宗教洗脑,以及开展春风化雨般的说服教育。
鲁兹说明来意之后,萨拉赫态度轻慢,神情漠然,这倒让鲁兹局促不安,这就是气场上的差异。
萨拉赫是见过世面的人,也做过大事,不可能像猎狗一样去关心一只幼狮的下落。
而且,萨拉赫认为,狮子乃草原之王,自由高贵,充满智慧和力量,居然成了吉普赛人的宠物,这是对狮子的侮辱,也是对他们教义的亵渎。
总之一句话,萨拉赫不愿帮忙。
影片在情节设置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揭开一个社区的堕落与混乱,根本不需要引入重大的恶性事件,而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用一个平常的治安案件,带领观众去探询这里的社会生态以及社会治理。
围绕这只幼狮,当地社区的几派力量悉数出场:非裔社区的民间管理者“市长”及其手下,前圣战分子萨拉赫及其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三位警察为代表的巴黎反犯罪机动警察部队。
由于语言、文化、宗教、肤色的标识极其明显,这个非裔社区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外人只能敬而远之。
因远离世俗生活和现代文明、法制,这个社区注定会深陷贫困。
这样的环境,就特别适合孕育犯罪的种子。
更重要的是,这个社区强大的凝聚力使警察的执法行动举步维艰。
这就不难理解,这个非裔社区虽然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风平浪静,但实则暗潮涌动,各种力量撕扯角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
这种平衡与平静,甚至容不下一只幼狮的搅动。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区里,通过社区民警,这种“赃物”独特的失窃案很快就可以调查清楚,并物归原主。
但是,在非裔社区,这种平和的处理方式却不可得。
因为,这个社区的真正管理者是“市长”,吉普赛人要“市长”平心静气地听他们说话,必须展示出足够的战斗力。
但吉普赛人在“市长”面前炫耀武力,又会冒犯“市长”在众人面前的权威。
另一方面,吉普赛人率领这么多大汉高调出场,却未能讨得一个说法,对于江湖形象也伤害极大。
于是,小小的矛盾因交织着尊严、江湖形象、种族荣誉、宗教教义而变得不可调和。
三位警察去足球场带走偷幼狮的伊萨时,被一群孩子围攻。
在这群孩子眼里,伊萨什么也没干就被抓走了,这肯定是种族歧视,冤枉好人。
这群孩子顽强的斗志令警察招架不住,伊萨伺机想逃脱,格瓦达开枪打伤了伊萨。
这一幕又被无人机拍下来了。
围绕这段视频,三名警察又要寻求当地一个贩毒团伙的帮助,真的是身心疲惫,如履薄冰。
最后,幼狮事件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伊萨心中的憋屈感难以平息,于是组织了一场对三名警察的围猎行动,三名警察在伊萨的汽油瓶面前,命悬一线。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当地非裔社区的实际管理者因为无利可图,加上自尊心受到触犯,不愿处理;当地的宗教团体,教义坚挺,本就不赞成圈养幼狮,不想施以援手;警察在非裔社区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前,加上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压力,难有作为,甚至自身难保。
进一步说,在这个非裔社区,社区首领只在乎利益,不在乎公理;宗教团体只关心推广教义,吸收教徒,行事理念中没有“法律”的框架;警察受制于各方势力的牵制,只能充当和事佬。
因此,这个非裔社区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但又时刻处于爆炸的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都会燃起熊熊大火。
大火过处,秩序不存,法律退位,鸿沟拓宽,生活日益困苦,唯有犯罪才能勉强度日,暴力机关一旦惩治犯罪,又会激发同一种族和同一宗教的同仇敌忾,一场骚乱又将引发大火……《悲惨世界》的开头,伊萨像一位良家少年,身披法国国旗,脸上涂着红、蓝、白(法国国旗颜色)的油彩,
与众多小伙伴逃票去巴黎市区,聚集在凯旋门前,庆祝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
在这片欢乐的海洋里,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差异被消弭,众生平等,团结在同一个法国的荣光之下。
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仍然存在,伊萨等人谈论的是非裔球员,欢呼的人群中,有人披的是阿尔及利亚(法国的前殖民地)的国旗。
影片结尾,伊萨变身为暴徒,手持燃烧的汽油瓶,准备置三名警察于死地,鲁兹握枪紧张地与伊萨对峙。
从片头的大融合,到片尾的生死对决,时间不过两天,起因不过一只幼狮被窃。
将此放大到法国,联想到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种族骚乱,我们可以猜想,这些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在法国是无解的存在。
(来自我的公众号:影像之魅)
6 ) 《悲惨世界》导演访谈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
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
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
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
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
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
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
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
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
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
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
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
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
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
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
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
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
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
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
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
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
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
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
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
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
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
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
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
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
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
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
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
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
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
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
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
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
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
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
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
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
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
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
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
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
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
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
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
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
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
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
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
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
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
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
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
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
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
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
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
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
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
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
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
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
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
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
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
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
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
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
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
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
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
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
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
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
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
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
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
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
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
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
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
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
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
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
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
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
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
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
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
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
“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
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
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
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
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
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
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
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
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
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
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
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
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
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
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
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
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
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
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
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
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
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
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
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
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
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
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
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
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
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
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
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
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7 ) 悲惨世界
看到有人讨论说,难道一切不都是因为那个黑人小男孩闯出来的祸吗?
是。
小男孩闲着没事去偷别人的小狮子,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熊孩子惹了大祸。
不过别的角色难道就没问题了?
警察不仅添了柴,还倒了一整桶的汽油助力。
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有人偷了你的钱包,你作为警察就能拿出枪来威胁恐吓他,打他一拳,抽他一巴掌,再把枪口塞到别人的嘴里?
电影中那个警察队长(反犯罪大队,听起来好像是纠察大队的意思,警力是否也太不够了!
),与其说他是警察队长,不如说他是城市里另一个帮派的老大——政府这个帮派。
他的执法准则不是按照警察手册里执行的,而俨然像帮派那样,利用手里的牌——其他帮派的把柄——或利诱,或威胁,或合作,来掌控及平衡整座城市。
而对于那个新来的警察,他并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的原则,同时也审度过利弊,不仅仅出于对黑人警察同事的袒护:他认为如果把存储卡上交或公开,并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反而却会因此导致整座城市的骚乱,甚至整个国家的无秩序对抗状态。
把政府的公信力降至低点,将警察的信任扭曲成仇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且似乎这个代价非常巨大,巨大到需要几十年甚至百余年来抚平康复。
就像我们的文革一样。
对于他来说,似乎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举报队长滥用职权;第二种,继续默许队长的行径;第三种,辞职或申请调离。
他选择了第二种,于是就有了矛盾的升级。
有句话叫做:仗剑而生者,必殁于剑下。
对于警察队长的那一套,他必然最后很难能够安然活到晚年,他用过的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最后终会被反噬一口。
滥用暴力,只会被暴力吞噬,让局面变得更加恶劣。
罗曼罗兰有句话,反过来说就是:“ 要散布仇恨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仇恨。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获得信任难,失掉信任容易,重新获取失掉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我忽然记起以前香港警察整片整片的腐败,到后来香港警方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高效廉洁典范,到如今又失掉信任。
我印象里记得以前获取信任,一是建立ICAC廉政公署,二是全警既往不咎,但再犯事从重处罚。
电影里面,警察队长是主要冲突的起因,因为即便没有小男孩偷狮子,仍会发生其他事件。
但是社会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到底是制度,还是经济?
还是都要解决?
或者,历史遗留问题?
PS:1,在片头,当所有人,不论黑人白人,不论大胡子还是卷头发,当他们身披法国国旗,为法国足球队摇旗呐喊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不分种族和肤色。
2,关于角色,其实还可以作更多考虑。
比如那个开枪的警察,他不是黑人,而是白人或一个亚洲人呢?
是否会因之间微妙的关系而导致完全不同的走向?
很难说。
3,其实导演可以在把男孩送回家,无人机存储卡被收走,警察各回各家,然后就结束掉电影。
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结尾,也能给观众留下许多思考。
不过显然导演另有打算,他把冲突升级了。
我觉得这个结尾更好。
8 ) 《悲惨世界》里的足球元素
谈两句《悲惨世界》里的足球元素(剧透慎看)电影是以描绘去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时法国民众的反应开场的,印象里最开始那些黑人小孩还在聊奥斯曼登贝莱和姆巴佩上不上场的话题。
了解这只世界冠军的朋友都知道,以姆巴佩、博格巴(坎特)、乌姆蒂蒂(瓦拉内)为首的三条线都是黑人,还没有算上登贝莱、勒马尔、马图伊迪等等主力球员。
法国队决赛的首发11人阵容里更是有超过半数的6位黑人,毫不夸张地说是黑人少数族裔给法国拿到的大力神杯。
这就不难理解导演设置这个片头的用意,不只是通过所有人走上香榭丽舍大道欢庆胜利的宏大场面营造气氛和引出“悲惨世界”的酷炫片名,更是暗示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打响了,即这到底是谁的法国。
这里还必须提一个小细节(也是一个逗的我笑出声的细节)。
粉红猪小队刚开始在市集里有一段闲聊:粉红猪说金球奖就是他了吧,团队的黑人小哥说是姆巴佩吧,粉红猪否认说他觉得是莫德里奇。
很不经意的一段对话,但信息量很大。
首先解释下金球奖是足球个人的最高奖项,过去十年都被梅西和c罗垄断。
再看两个人选:姆巴佩是法国人,世界杯夺冠最大功臣之一和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新星,以及黑人少数族裔;莫德里奇是法国队决赛对手克罗地亚的核心球员,世界杯最有价值金球奖(不过这个奖项近几届被视为对亚军的安慰奖),以及白人。
然后回看那段对话,作为法国人的粉红猪宁愿把金球奖颁给对手也不给自己国家的黑人球员,那种不可调和的种族矛盾通过两句话传达出来。
事实上电影最后交代给我们的正是无法调和的结局。
(有趣的是,当年金球奖最终得主正是莫德里奇,姆巴佩排在第四,第三是他的国家对队友格列兹曼。
)最后想说的是,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悲惨世界》的原因的一个缩影。
它太工整了,连足球元素都用得没有一点点废戏。
每场戏都像是精心算计的组成部分,最后更是用某种看似升华的方式作结。
而我对这种高考作文似的表达没有感觉,甚至有点抵触,这还是在没讨论人物弧光的前提下(事实上最后的大战因为人物坍塌在我这也是减分项)。
到底是谁的法国写于2019年6月24日将要发于公众号 深邃的电影
9 ) 這是場戰爭但勝利是不可能
(其實沒想寫長評的,無奈超字數了。
我當然也關注移民問題,但畢竟了解太少,沒什麼可說的)法國於我而言不止是浪漫,更有革命情懷,最經典的莫過於原版《悲慘世界》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幾百年過去,這世界還是這麼悲哀,壓迫、暴力、強權、傷害、反抗,舊有的因由沒有消失,新生的問題卻源源不斷,一切都在繼續。
本以為電影講到男主把芯片交給瓦達,故事便在這不公和壓制中結束了,沒想到緊跟著會有那麼激烈的樓道戰,最後停格在高舉的燃燒瓶和中彈孩子的臉上。
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人性在此刻博弈,顫抖的手槍,靜止的燃燒瓶,悄然撥開的門梢,「這是場戰爭但勝利是不可能」。
反抗的圖景總是動人,在街頭就拋出磚頭,去商場就推出購物車,在樓道就拋下所有能拋的廢棄物。
然而當一切都走向失控,還能對這一圖景說出「動人」二字嗎,未免太過冷血。
但也無法譴責奮起反抗的人民,無法對肆虐的強權和仇恨無動於衷。
我們最終會被裹挾著走向哪裡?
10 ) 玷污了雨果的《悲惨世界》
这片子在豆瓣评分这么高就离谱,事实上在巴黎住过的华人都知道93区是什么情况。
这帮人从生下来就吃着法国政府的各种补助:住房、医疗、教育、生育,包括各种现金补助,成长的日常就是偷偷游客的钱包、抢抢亚裔的手机、骚扰路过的中国女生,然后在社会骚乱中时不时快乐0元购一番,居然还要“控诉”法国政府是mauvais culvateurs...和HK废青一样,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说什么种族文化宗教受歧视的,照这个逻辑,最有理由控诉的应该是在法国生活的华裔移民啊,可是也没见人家打砸抢烧成天破坏社会治安啊?
你自己在电影开头都说了非洲老家多么野蛮可怕,抓到小偷就绑上活活烧死,那你在文明的法国还不好好珍惜眼前的生活环境,偌大个市镇只有三个警察巡逻,治安的脆弱已经可想而知了,还要进一步破坏平静生活的最后一丝底线,彻底回归荒蛮就开心了吗?
看了这片子导演的背景采访终于明白了,这么一个有着殴打女性、绑架和非法监禁前科的人能拍出这样的片子一点都不奇怪。
这片子获得戛纳的奖项和各种赞誉,只能说明法国电影界已经全面好莱坞政治正确化,吃枣药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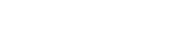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观众的政治觉悟感觉都太高了些,我就想问问,谁来约束偸狮子的熊孩子?
2020年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5部提名电影终于全部看完,整体观感稍胜过2019年第91届五部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成为近几年个人最心仪的一届。今年五部电影我个人的喜欢度大致排名:《寄生虫》韩国、《痛苦与荣耀》西班牙、《蜂蜜之地》北马其顿、《悲惨世界》法国、《基督圣体》波兰。—— 联想到1995年的《怒火青春》,然后第N次深深地感受到自己那个理想的和谐美好世界是多么天真且难以实现。且不论不同人对是非观念的差异,有些人即使明辨善恶也不代表会行善弃恶,而复杂的现实情况还可能也会让好人做了坏事。看到 Issa 被抓进狮笼那段我流泪了,Ruiz 那种想把事情处理好有时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也曾体会过。—— 朋友们,请记住:世上本来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片尾引用的雨果“庄稼人”原话,充分暴露了编导自己无耻至极的三观:我们偷窃、我们无视法律以及一切公序良俗、我们野蛮、我们暴力、我们为所欲为、我们不学无术,但全都是你们的错!你们TM给我老老实实反省! 谢天谢地,幸好这里不是法国。 不是片尾的这种自爆可以给3.5星。
这种没有答案的问题看着真令人头疼,导演的节奏挺吸引人的。“我们没想伤害谁,不是故意开枪的。”“你们没错,总是没错,你们配了武器但不懂使用,还是运气不好?”“无论是不是意外,视频泄露出去,只会火上浇油。”“如果只有发泄怒火才能换来倾听呢?”“之前的愤怒换来什么?最糟糕的是你们的愤怒也没人在乎。”
攻击
“如果愤怒是唯一表达的途径呢?最糟是没人会在意” 事态走向的万劫不复感拍出来了,但缺乏情绪和核心情感,本以为是另一部《狩猎》。狮子笼戏份最有力度…“会叫的狗不咬人” 愤怒无用。
论恶是如何产生的。
视角单一化、人物脸谱化,以牙还牙的简单逻辑,站边挺明显,孩子做什么都无罪论,男孩的转变非常突兀,粗暴、蛮横的对待确实存在,但整起事件并非全都是恶意加害,而之后的复仇却是恐怖分子级别的了,警察里姑且还有个温和派,但孩子群里却没有,这也是提醒众人边缘且低龄的孩子别随便惹,他们更能团结一心,破坏力惊人,因涉世未深、敏感躁动而更难沟通~那个叫萨拉的黑人有点像当地的牧师,但他没有担当起和平使者增进双方的理解,反而觉得愤怒只有以暴制暴一种出路,也是诧异~毕竟那个所谓的巡逻警头头是外强中干型,不是残暴到必须杀之后快,权钱交易、黑白勾结,只是蜻蜓点水,没有素材来解释警察的行为逻辑~新人警察这么有说服力也是少见,如是极端环境他早就被干掉了,悲剧点在于警察的态度刚软化就被暴击了,预示着没完没了的冤冤相报吧~
开场庆贺的大场面和结尾处的反击骚乱场面都极其刺激眼球,也算是相呼应,这部分情绪上似乎有点共通娄公子刚上的风雨云。即便作为一部阶级革命片有点简单粗暴,但这种深入血液的暴动基因还是让自己艳羡不已啊!
带有明显批判色彩的电影,从开头就高压拉满一直到最后,这群人都不安且不信任另一群人,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却又无解。
了解法国的另外一面
8.2 默片,人们张口,却没说任何话。难得的缓冲时刻,在那一段结束也并无不可,比开放式结局更合我胃口,不过至少是好看的,只是和《悲惨世界》到底有什么关系?
什么玩意。
世界上没有坏种也没有恶人,只有坏的播种人庄稼地。这早已不是雨果的巴黎,海报上的人群也不是抗议,而是在庆祝拥有多半数有色人种的法国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当年轻的姆巴佩驰骋在绿茵场成为英雄,比他还要小的黑孩子跑在街头白警察仍然追不上他们。应该在非洲大草原自然生长的小狮子不堪呆在鸡窝,被关在马戏团笼子里的大狮子也仅是像会叫的狗一样不咬人。离得那么近为什么会开枪,仇恨的累积无限的报复只会植入到每一个亲历见证者年幼的心里以改变未来不可收拾,高级的暴力那就是革命。生猛成熟的处女作,与同样非常喜欢同获戛纳评审团奖的《巴克劳》都出现了无人机,用俯瞰的视角展现记录着那些不可告人足以抹去的杀戮。#金马56#年度十佳。
【4.5分】
后排法国人从头笑到尾……烦。前半部分节奏不行,基本在靠最后二十分钟让人入戏,同情。
用最后一个定格刻写了“仇恨”的当代形态。在处女作的意义上可以给到四星。
雨果可以描绘革命年代里人的沉浮,但是他无法预料在未来的巴黎,人们会以另一种方式站上街头。出色的记录风格,很难得一位马里移民能用完全不偏袒的口吻讲述这样的矛盾。
形似社会批判却不见作者思考,止于皮肤,意思松散,比较取巧的水时长+装深沉,不及导演后作《雅典娜》(亦强得有限——什么风格这么接近查了下居然不是一个导演,行吧)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