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剧情介绍
音乐人阿鲁斯(伊德尔 饰)因不满哥哥对患有阿茨海默症的母亲(巴德玛 饰)的照顾方式,决心带她返回草原,去寻找母亲记忆中的家。为了防止母亲走失,阿鲁斯用一根绳子系在两人腰间。似脐带一般的连接,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逆位”母子情,牵引着两人向草原深处漫游。当爱由彼此羁绊化为理解和自由, 母亲终于回到心中的故乡,阿鲁斯也得到平静和爱的力量。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十全大补男叛逆性百万亚瑟王第二季紧急链接地狱奶奶民间怪谈录之走阴人摩登家庭第十季乱世芳华世界奇妙物语2007秋之特别篇霍顿与无名氏9号秘事第六季白日焰火近距离我最亲爱的柳予安墙壁之间孤魂记假面骑士55520th天堂・重获铁血钢拳迷你刀使复仇者联盟神盾局特工第二季古宅老友记第五季最遗憾是错过你不幸之家红灯绿灯不屈服的女人芒针十角馆事件飓风营救第一季船只灵瞳
《脐带》长篇影评
1 ) 今天下午看了《脐带》的阿那亚首映,很唯美,很温暖,很感人。
今天下午看了《脐带》的阿那亚首映,很唯美,很温暖,很感人。
在看电影的时候 中间有好几幕眼泪都要出来了,影片中语言不多,仿佛什么都没说,但仿佛什么都说了,很喜欢这样的电影。
看完之后内心一下被带进去,整个下午到现在很久都没出来。
也大概明白了脐带的意义,影片最后那棵树我理解是根,是我们回不去的过去的故乡,是我们对家人的情结 是我们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
片中处处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对家人父母的爱,对社会中普通人的爱。
拍的特别好,很喜欢这部电影。
2 ) 有一天月亮落下的时候,我来接你回家
这两年开始面对父母的断崖式衰老。
不是那种白发、皱纹的老,是要每天盯着他们吃药,经常去医院、偶尔做手术、住院、陪床,和不遵医嘱的他们斗智斗勇,以及陪伴他们度过漫长治疗的老。
很奇怪,在这之前,他们在我潜意识里一直是三四岁的模样,整天忙忙碌碌,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偶尔吵架,就会拿出长辈身份讲些颐指气使的话,我自然不听,只想着怎么快点长大,能真正独立到逃离他们。
也许正因为真正逃离过吧,40岁以后的父母在我记忆里几乎是空白的,直到这些年再次走进他们的生活,才发现他们居然已经老成了这个样子。
昨天送倔老头儿去医院做常规治疗,他非让我先走,说陪在那儿一下午没意义,他不想麻烦任何人包括我。
我拗不过,只好把带的水塞到他手里说:医生说多喝水,你要听话啊,别一下午都渴着。
看他拿着小水瓶过马路的样子,忽然觉得自己很像是送他去上幼儿园的妈妈。
电影里第一次让我没忍住哭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段。
阿尔兹海默的妈妈发现自己尿床了,害怕被看到就想要用被子盖住,儿子赶快跑过来抱住她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尿床,太阳一晒就什么都没有了,没事啊。
”妈妈听完愣了一下,紧接着把头靠在他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说:“爸,你终于回来了”是的,曾经妈妈也是女儿,是她父母的宝贝。
后来她长大了,成了妻子,成了母亲,用自己的一部分换取了家庭的稳定、孩子的成长。
多年后她老了,这时身份对换,某种程度上妈妈变成孩子,孩子变成家长,他们又回归到需要手牵手才能走下去的关系,一直这样到路的尽头,那时连在他们身上的脐带由孩子亲手剪断。
他放她回到她的父母身边,从此再没人把他跟死亡隔开,他的人生来处已逝,只剩归途。
电影跟《我的阿勒泰》一样好看,拍得像诗歌,像散文,像民谣,也像一个传说。
音乐、摄影、巴德玛的演技都在不停的疯狂输出,想着不哭不哭干啥啊只是看个电影啊…最后还是哭得一塌糊涂[哭惹R]一下就懂郭采洁为什么要跟伊德尔结婚了,管他呢,就是这一秒,爱了再说吧~(全平台同名:杨素瑶。
原创不易转载小窗~感谢关注)
3 ) 乔思雪导演访谈:漫游在蓝色草原
策划、访谈:许金晶(影评人,《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一个家族的电影史》编著者)2023年12月31日上午腾讯会议连线访谈于各自家中访谈整理:冯雷铮(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在读)《脐带》是2023年我看过的最喜欢的院线艺术电影之一,也通过这部电影,对于其作者乔思雪导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思雪的过人之处,不只在于娴熟而老道的影像表达语言,也在于记录草原社会文化生活生态,自觉传播草原上优质民族音乐、世界音乐与灿烂文化的学术自觉。
而后者是深受文化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浸淫的我、所特别钦佩与感动之处。
2023年的最后一天上午,得益于老友郑大圣导演的引荐,我终于得以通过腾讯会议,跟乔思雪导演展开了一场为期两个小时的访谈交流。
希望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访谈,能够让广大读者和观众,了解《脐带》这部优质艺术电影背后、其电影作者的成长之路与影像创作历程,也由衷期待乔思雪导演在艺术电影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
许:我们先从您的成长背景聊起。
您的家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旗,而您本人又是达斡尔族。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家乡是一片怎样的地域,您童年和少年的成长背景如何,以及大概是什么时候、最早接触到电影和艺术的?
乔:我长大的这个地方跟传统意义上的内蒙草原不太一样。
我们这刚好处于中俄蒙交界的地区,再加上靠近东北,本身地貌比较丰富。
文化上也是如此,非常多元。
俄罗斯和外蒙古的文化对这里产生了不小影响,甚至一些当地部落本身就是从俄罗斯迁移过来的。
所以大家在思想上都很开阔,我高中毕业之后,家里面就送我出去留学,大家都很渴望与外面的世界接触。
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排斥集体的小孩,不愿意上学,几乎是跟周围邻居一起在院子里面长大的。
我的童年和大自然有很多接触,每年夏天爸爸都会就骑着摩托带我去山上采蘑菇,学校里面也会组织春游。
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整个内蒙古,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变化其实蛮大的。
我小时候住的院子离草原非常近近,出门十分钟就是一望无际的草海,同学的父母可能还要用马车拉他们到小镇里面来上学。
现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车了,牧区进入了一种现代化的状态,城市的版图虽然在不断扩大,却离自然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至于电影,我从小就喜欢妈妈给我讲故事,有很多北欧的故事、童话,我听到讲故事的声音,脑海里慢慢浮现出画面,就像电影一样。
我的想象力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
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也很喜欢电影,每周都会租录像带回来,全家人聚在一块看电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家庭活动。
后来他们不在一起了,但是看电影的这个生活方式倒留在我这儿了。
我从初中开始就会租DVD光盘来看,那些盗版的DVD简直拯救了我们那群小镇青年们贫瘠的精神生活。
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有其它窗口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电影就像一个任意门一样,把我们带到不同的文化、地域,甚至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体验的人生里面,所以它后来也变成了我想要去表达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的一种方式。
许:也就是说您最早就是接触到电影的方式,是一种家庭内部的私人化观影,我前段时间采访过李睿珺导演,他在西北农村看的那种公共电影跟您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不同年龄段或者说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导演,观影经历还是有区别的。
你可以再讲讲当时看的电影里面让你至今印象很深刻的吗?
乔:当时有很多欧洲的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个时候我对他们的文化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的观影会让我产生一种寂寞、孤独和不安全的感觉,冲击很大。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有可能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一部电影,名字我都完全记不住了,但是有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一个非常高的石头建筑的街道上,有一个穿着黑色风衣戴着礼帽的男人,然后街上全部都是被风卷起来的报纸和垃圾,就是那一幕,让我对外面世界甚至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我开始想,也许离开家后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等到我稍微再长大一点,再看到法国电影,就发现电影里面的生活是那么精致那么丰富,我又有了另外一种感觉,我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一种好奇,想去探索。
许:您的大学是在法国巴黎3IS国际电影学院学习电影。
能否介绍一下这是一所怎样的艺术院校,以及您大学期间在其中接受电影和艺术训练的情况?
大学毕业后,您还曾在法国一家VR电影公司做后期,当时的具体工作能否再简单介绍一下?
乔:选择去法国留学主要还是因为对法国电影非常感兴趣。
但是到了法国之后,实际上很多内容是听不懂的,因为它完全脱离了我熟悉的语境,学了十几年的英语也用不上了。
我现在觉得,学校教给我最多是怎么样看电影。
我留学的学校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很好的学校,他们很注重对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所以,虽然很多东西我刚开始不懂,但是实践的过程帮助我理解了一些理论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法国学习电影,还能够通过做志愿者的形式来直接接触到戛纳电影节这样的活动。
到了戛纳的现场,会发现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戛纳其实是一个挺小的城市,远不如报道里的辉煌。
但很神奇的是,那个地方就是聚集了很多跟电影无关却热爱着电影的人,他们从世界各地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排一下午或者一天的长队,准备看一部电影。
这种神圣的观影状态,对我感染特别大。
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一家VR公司,那个时候刚开始流行一些VR眼镜。
然后我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做了很多实验性的短片,也有一些相对长一点的剧集。
许:您对巴黎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体验和印象?
它跟您之前在草原的生活状态有哪些异同?
在巴黎期间的电影学习和工作经历,是如何影响到您之后的编剧和电影创作的?
乔:我先说相似的地方吧,我觉得无论是法国还是我的故乡,大家对人之间的干涉是比较少的,大家都愿意理解你想要做的事情,很少会非议别人的生活。
不同的地方在于,巴黎显然是一个更丰富更复杂的地方,有很多的美术馆、展览、古董市集、跳蚤市场等等,很多年轻的父母并不需要老人帮他们照顾孩子,会在周六周日用婴儿车推着孩子去看各种展览,包括电影院。
我们这儿的文化生活就没有那么丰富,这一点差别还挺大的。
在巴黎的生活和学习完全打破了我以前的生活习惯,我相当于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要面对新的文化,适应新的规则,像一个海绵一样不停不停地吸收新东西。
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在很多社交和拍摄的场合里,我更像是一个站在旁边的观察者。
我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都已经无法从原本的生活经验中获得解决办法,这就导致了我需要再一次进行独立思考才能找到解决的路径。
事实上,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的。
我认为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一点,对所有学电影、搞电影的人来说都挺重要的。
许:在法国期间,您曾经创作过两部电影剧本,能否介绍一下这两部剧本主要的主题、内容以及创作灵感来源?
这两部剧本最终未能由您本人创作成电影作品呈现,各自是什么原因?
这两部剧本的创作,对您后来创作拍摄电影《脐带》有哪些帮助?
乔:《和月亮的距离》是我在法国写的第一个剧本,是跟另外一个朋友完成的,讲述了一个女学生爱上女老师的故事,属于同性恋题材。
当时是打算回国来拍,但是当我们真正回到国内,了解了整个行业内的环境后,就发现其实这个剧本无论是找钱还是拍摄,都面临很大的难度,所以那个剧本就一直放着。
或许会将来会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吧,我们会去再改这个剧本。
然后另外一个剧本是《梦幻骑手》,它也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合作完成的,讲述了一个内蒙古骑马女孩的故事,我们这边骑手虽然很多,但是女骑手非常非常少。
《脐带》里面塔娜的洒脱女孩形象和这个有一些相似,我很欣赏这样的女孩,因此我的每一个剧本里面的女性角色,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的角色,都比较接近这种情况。
我还蛮感谢这个剧本的,这个剧本后来被国内的一家公司看中,但是这家公司的制作更偏向于有文艺内核的商业电影,体量都比较大。
考虑到我们并没有执导长片的经验,我们最终选择了把版权卖给这家公司,他们也给了我们一笔钱,这成为了我的启动资金。
也正是因为交易这个剧本的契机,我回到了国内,要不然可能会一直留在法国。
许:我发现您现在的常住地还是鄂温克旗家乡的小镇,所以为什么您从巴黎回国之后会选择回到草原上,而不是定居在像北京、上海这样有很多方便电影创作资源的城市呢?
您回到草原之后的心境和体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它们最终是如何促成您就是创作期待的这部作品的?
这个剧本有哪些是源自你的家庭,和生命体验?
乔:我其实是在拍完《脐带》之后搬过来的。
因为刚开始进行创作的时候,我在国内电影行业里面所认识的人以及其中能帮助我的人是有限的。
但是当我拍完了《脐带》,我觉得这个关系已经建立了,就没有必要留在北京了,尤其是对于一个非商业电影导演来说,离开北京后的生活跟社会关系网反而对创作更有益。
我在北京也生活过三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周围的朋友不是搞电影的就是搞艺术的,我很少能接触到行业之外的人和聊行业之外的事情。
但我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创作的过程,是创作中接触到的人和事,它们能给我真正的启示。
所以我就搬了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这儿的生活其实很丰富。
朋友们都是我从小见到大的,他们的生活关系网其实就非常有意思,也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聊他们生活与工作中的人和事。
其实只要肯花时间挖掘,跟当地居民敞开心扉地聊天,我们就能够发现这里有很多值得创作的空间,也就自然不会觉得这里的生活很贫瘠。
《脐带》的故事可能没有一件事情是我的真实生活,但是这些人物都变形自我周围的人。
比如说哥哥和弟弟这两个角色,哥哥更像我爸爸,弟弟更像我叔叔,他们的兄弟姐妹里面没有女性,所以他们家确实是以男性照顾父母为主。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物原型最深层的潜意识是来自于他们俩的。
但是在塑造弟弟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又参考了伊德尔这个演员本身的经历,我们之前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很了解他整个生命体验的变化,他本身是一名音乐人,后来离开家乡去北京闯荡,做一种新形式的音乐。
他的经历对我塑造角色有很大的启示。
母亲这个角色跟我母亲其实完全不像,但是她身上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我对母亲的一种寄托。
其他的角色也都来自于我周围的人物,塔娜角色本身就跟演员的性格很像,她就是一个在生活里面很有主见的人,她曾经也在北京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读过书,在那里工作过几年,是她后来自己选择的回草原开一家民宿。
我觉得这些生活都非常有趣、丰富,又具有现代性,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类似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草原上的传统牧民生活,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但是还没有人去讲,所以我就有了讲述他们故事的欲望。
许:《脐带》从剧本完成到成功公映,历经了五年时间。
能否介绍一下这五年时间里这部作品经过了怎样的传播、改编与打磨历程?
在长达五年的打磨历程中,有哪些相遇的人和事让您印象深刻或特别感动?
我在完成剧本之初,有公司表示有兴趣投资,但最终还是流产了,所以我们才决定参加电影节。
事实上,我们对国内的电影节并不了解,那是我们第一次参加First电影节,在没有制片人,也没有公司支持的情况下拿到那样一个成绩,我自己都挺意外的。
后来坏兔子公司的员工将这个剧本拿回了公司,并向我的制片人展示。
因为制片人自己就是内蒙人,所以对故事有一种很天然的情感在里面,他就把这个剧本推荐给了我们的监制曹郁和姚晨老师。
我后来对他们的反应也很意外,因为他们本身对内蒙古的文化并不熟悉,但是却能对故事产生强烈的共情,这很难得。
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我很担心它是否能够与外界产生联系。
他们在这个阶段对我的肯定让我感到非常有信心。
我们当时决定在2020年开始拍摄,但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的疫情,一直到2021年才开始正式开机。
拍摄结束后,又进行了一整年的后期制作,电影直到2023年才上映。
这里我特别感谢我们的制片人辉哥(刘辉),虽然碰到了疫情以及各种各样的挑战,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和退缩,帮助我们把问题都解决了,他坚定的态度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片子做下去。
其实在开拍前这两年的筹备时间里,我们的剧本一直在打磨,前后改了十稿,有的时候人会很疲惫,在犹豫到底还要不要拍,所以制片人坚定的态度对我们很重要。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影片的监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几乎动用了所有可能的资源,找到了一流的主创团队。
另一位制片人胡婧也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她也是蒙古人,我们三个内蒙人之前互不相识,却因为这样一个剧本一块来做这个片子,并且邀请到如此有分量的主创完成这部影片的拍摄,我觉得很有缘分,也很幸运。
许:阿尔茨海默症是近年来国内外图书、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呈现的热门题材。
在创作《脐带》之前,您之于这种疾病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生活体验还是文艺作品的“阅读”经验?
能否介绍一下之前接触的这些生活体验和“阅读”经验?
您在《脐带》中之于阿尔茨海默症的主题立意与故事呈现,跟之前接触的这些一手、二手经历之间,有哪些异同?
乔:我在此之前对这个病完全不了解,而且我觉得在2018年之前有关阿尔茨海默症的作品还比较少。
我写作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有这个病的阿姨,她的年纪跟我母亲差不多,我当时就想到这种生命体验如果置换到我母亲身上,会对我影响会很大。
所以当时就关注了很多跟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内容,包括小说、纪录片之类的。
后来过了差不多一两年,我爷爷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我对这个病就有了不一样的新的认识。
这些东西影响了《脐带》最早的构思,但其实我写《脐带》也不完全是为了阿尔兹海默症,我在碰到那个女士之后,最早是想拍一个跟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小短片的,但是写着写着,我觉得它发展成一个长篇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不断地想到我的母亲,我的故乡。
它最后其实就已经脱离了这种病,变成了一种别的情感在里面。
中国老话讲人会返老还童,我其实很强烈地感受到了父母的这个变化,原来会觉得他们戴着一个父母的面具,我们对他们只能通过“父母”这个角色去了解这个人,但是,他们在慢慢退化成小孩后,就好像变成了独立的人。
而通过单纯的日常生活是很难展现人返老还童这个状态的,尤其是还要让观众理解,所以我是觉得阿尔兹海默症让人变成小孩的这种状态,其实是比较能具象地展现他们返老还童的过程。
所以当时就把这个病加入了这个故事里面。
许:对蒙古族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的呈现与传播,成为电影《脐带》的重要亮点之一。
能否一一介绍一下电影中使用的每一首歌曲的大致内容、选择用意,以及其之于电影叙事的作用?
电影中的配乐,以乌仁娜、伊德尔、欧尼尔这三位蒙古族音乐人的作品为主,能否介绍一下您对这三位音乐人及其作品的接触历程、对于她(他)们音乐作品的评价,以及在这部电影里的合作情况?
乔:对蒙古地区来说,音乐其实很像一个隐形的脐带。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当有朋友来访的时候,语言的表达有时候总是很匮乏,甚至是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能让大家进入到这个情境,但是当我们喝掉一两杯酒,然后有人起来唱歌的时候,大家就会很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共同情境里面。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能感觉到音乐就是这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所以在《脐带》里面,音乐对于他们是很重要的,是一件在生命里面不断重复的一件事情。
《脐带》里面的歌曲在叙事上面真正产生作用的,实际上是伊德尔给母亲弹的那几首曲子,那都是草原上以前很老的歌,也都是他小的时候母亲唱给他的摇篮曲,也是我们以前经常听到的一些很很熟悉的音乐。
伊德尔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反哺的方式再一次弹给了母亲——他 孩子一样的母亲。
乌仁娜老师那一部分的配乐,实际上最早影响了我对《脐带》的写作,尤其影响了我在这个剧本里面注入的情感。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法国,我在想家的时候经常会听乌仁娜老师的音乐,听那些歌曲,就好像突然一下回到了草原,甚至能闻到那个草的味道。
她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在外面漂泊的人,她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因此她的音乐与《脐带》的内核有着深刻联系,所以这里面用了很多乌仁娜老师音乐。
我最早甚至有想过找她来演母亲的角色,但是因为她的年龄感跟真正的牧民女性还是有一些差异,再加上疫情影响,最终没能邀请她来。
如果邀请她来演这个角色,可能这些配乐的曲子会让这个角色真正演唱出来。
我曾经想过放弃用她音乐的想法,但是监制曹郁老师听到她那张《ser》的专辑后大受震撼,最终我们决定以配乐的方式将乌仁娜的音乐融合进脐带。
伊德尔老师本身就是音乐人,他的音乐的极力追求着音乐的现代性,包括怎么样把传统的音乐带到现代音乐的语境里面,所以电影里的开场音乐以及后面的有一些配乐,像跳舞的那几场戏的很多编曲,其实都是他制作的。
我之前并不认识欧尼尔老师,他主要在新疆工作,他改编的内蒙老民乐里面又有一种带有新疆地域风格的节奏感和乐队感,跟民谣又很像,甚至有一种俄罗斯的风格在里面。
所以这三个音乐人的合作让《脐带》的音乐表现在整体上显得非常丰富。
它也表现出了音乐传承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音乐人发展出来的对传统民乐的不同理解。
许:您刚才提到曾经考虑过让乌仁娜老师来做女主,但是后来呢您还是选择了巴德玛老师。
在跟巴德玛老师合作之前,您是否看过她之前主演的影视作品?
这次是如何与巴德玛结缘的?
您作为年轻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如何跟巴德玛这样的资深表演艺术家合作?
围绕巴德玛和伊德尔这两位主演的拍摄沟通交流,有没有一些难忘的故事?
能否一一分享?
乔:因为我非常喜欢巴德玛老师曾经在内蒙古拍过的一个片子,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的《套马杆》。
我知道她其实她以前不是演员,她从小在牧区长大,所以对牧区的生活非常了解,而且她整个人透露出来的感觉其实是离演员的身份很远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是一个我熟悉的中年阿姨的那个样子,非常热情,会开着车来火车站接我们。
她看过剧本后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在我们聊天过程中,她聊到自己的家人时还落泪了。
我觉得她流露出来的神情,以及她的动作、音容、样貌,其实都没有中年人的中年感,反而很纯净,很像一个小孩,有那种童真的感觉在他身上,就正好符合这种返老还童的设定。
因为这个角色难度很大,如果你身上的东西太过沉重,没有那种很轻盈的东西,是演不好一个慢慢变成小孩的角色的,所以我见到她之后就决定要找她来演这个角色。
但是当我们离开呼和浩特之后,她其实把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也很让我感动,她说她从来没有接触过阿茨海默症的患者,更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而她又很喜欢这个剧本,如果她在表演上没能完成这个角色应该有的东西,她害怕对我这个青年导演以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大影响。
后来其实我和制片人又去找了她两三次,包括作为演员的监制姚晨老师也和她通过几次话,大家从不同维度给她建立了很多信心。
她身上的一些特质,实际上是能跟这个角色天然结合到一起,甚至给这个角色增资增色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导演跟演员之间建立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怎么让她相信她饰演这个角色是不二人选,怎样让她建立跟角色之间的信任。
所以最后她还是决定来出演这个角色。
在拍摄过程中,有困难的是伊德尔老师,因为伊德尔老师没有过任何演员表演经验,虽然他在舞台上是一个很有自信的音乐人,但是到了拍摄现场,每天九十几个人看着他表演,全场安静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紧张,连生活里面最基本的走路、喝水等动作都没办法自然地进行。
后来我们让他和巴老师每天一起坐车,一起吃饭,除了睡觉之外所有时间都在一起,就是让他们建立起那种亲密关系。
巴老师又是一个很有母性的老师,所以他就每天带着伊德尔老师,慢慢就建立出了角色之间的这个情感。
因为我们是按照时间线的顺序顺拍嘛,两个人通过时间慢慢建立起情感的过程跟故事里人物慢慢走进的过程是很像的,所以最后他们能很完美地配合演出。
到拍最后一场“告别”戏的时候。
他都不需要太用力地去表演,只要真正进入到告别情境,相信真的要跟母亲,跟他自己的角色,跟所有剧组的人要告别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一种真情流露的状态。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有这么深的感触,我看到他流泪的时候也跟着热泪盈眶了。
许:电影中以蒙古族的人物为主,也出现了说鄂温克语的牧场主,但似乎没有出现达斡尔族人。
您作为达斡尔族人,为什么会拍一部以蒙古族人为主体的电影?
您今后是否会再拍以达斡尔族人为主体的电影?
乔: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拍达斡尔族,因为对我来说,这不只是拍一部电影这么简单。
我自己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实际上在我成长过程中,像我爸爸爷爷一家,包括我姥姥一家,都是说达斡尔语的,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将语言传承下去了,我对此感到很悲哀,又很难受,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化解方式。
所以我轻易不敢拍达斡尔族的故事,我对我自己的民族还要更深入地挖掘和了解,才能知道到底应该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脐带》就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当然我周围有很多蒙古朋友,他们说母语的时候,我在旁边也是一个观察的状态,所以这个语言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相对熟悉的语言,这个文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熟悉的文化,然后这个文化又相对更丰富,无论是从舞蹈、音乐,甚至历史,都有很多可以挖掘和研究的东西。
所以就是先从先从他们入手。
许:如今草原上这种这种生活状态跟您童年、少年时相比,有了怎样的变化?
这种记忆与变化,是如何体现在电影《脐带》的影像呈现之中的?
对于李睿珺导演之前创作的以裕固族人(人口同样为十多万,跟达斡尔族类似)为主体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您是否看过,有着怎样的评价?
乔:在我小的时候,像我姥爷他们其实会非常流利地讲当地四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包括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还有布里亚特语。
所以他周围的朋友全部都是少数民族,他们也都是以真正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生活在一起的。
但是现在我周围一块长大的少数民族朋友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去交流了。
这是语言上的变化,还有一种是生活状态的变化,我们不用再过一种很贫瘠的生活。
像我爷爷、姥爷那个年代,他们在一块就是喝酒聊天,他们生活非常非常单调,我现在已经写了一个关于这些老酒鬼的故事,我其实挺想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他们跟朋友之间的亲密度可能比我们现在要亲密得多。
我也很好奇他们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所以我就不断在问这些还在世的老人,去尽量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故事。
我觉得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和关系是没有以前那么紧密的,有很多东西都在快速发展中被遗憾地丢掉了,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语言,甚至除了身份证能证明自己是这个族群的,我们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是跟它联系的?
这么看,这个东西其实是其实越来越少。
发展太快了,20年前,大多数家庭都用马拉着孩子到小镇里面上学,今天所有人家里几乎都有了汽车,极速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老人们和我们都没想清楚,就被无意识地丢掉了。
许:《脐带》的制作团队非常强大,监制是曹郁和姚晨,美术、声音、造型指导都来自电影《八佰》的团队,剪辑指导是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剪辑师张一凡。
能否谈谈跟这些优秀的团队成员的结缘经过、跟他们的具体合作情况、以及他们自己在这部电影创作中的贡献?
乔:曹老师在《脐带》里面的角色相对更复杂一点,因为他既是监制,又是摄影执导,我跟他接触的时间要比其他主创多很多,他在这里面付出的心血也非常多。
这是他拍完《可可西里》之后第二次再回到大自然里面拍戏,经过这么多年,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和热情又更进了一层。
他本身对蒙古族的文化音乐也很感兴趣,再加上也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他也很能带入到故事情境里面。
在改剧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已经非常深入地解析了《脐带》这个故事,包括最终以“脐带”这个中文名作为片子的名字也是我们一块决定的。
所以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没有分镜头脚本的,因为大家对这种故事都已经太熟悉了,其实更多的是在现场去解决其他的问题。
再加上这个片子里面,大部分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我也很难用具体的分镜和脚本去规定每一个人的表演,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每天到现场排练,然后再来讨论合适的拍摄方式来表达我们想传递的东西。
除了摄影,在很多方面,曹郁老师都给了我很多灵感和启示,因为他是一个有高度艺术自觉性的人,都不只是摄影师了,对我们团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富康老师是我们的声音执导,在拍摄《脐带》之前,我就已经看过所有他和娄烨导演合作的作品,我很喜欢他的声音设计,有种处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细腻。
他其实很了解草原,也正是他在后期制作阶段对声音的正确理解和处理,观众们才能在《脐带》中对草原有进一步的认知。
电影里有许多很细微的声音都是需要声音指导进行二度创作的,包括一些用来突出角色心理状态的声音,这些在富康老师的帮助下完成得很好,所以他是投入了很大的情感在里面的。
张一凡老师是我们的剪辑指导,我虽然熟悉他剪辑的《太阳照常升起》,但曾经也探讨过他的剪辑风格和《脐带》这样的电影适不适合,中间我和监制们也都各自剪辑了一版,不过,我们也想跳出一直以来对艺术电影的惯性认知。
张一凡老师的剪辑版本最终融合了大家的意见,反而让《脐带》的整个观感更能被观众接受了。
许:电影《脐带》的片名和核心意象“脐带”,我印象中灵感来源应该是出自某位国外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作品。
能否谈谈为何会把“脐带”作为本片片名和核心意象?
这样的意象,在您看来,包含了哪些层面的寓意?
这些寓意在影片中,是如何以影像语言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的?
乔:我当时写这个故事时候,借鉴了台湾的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作品。
但是他使用绳子是将两个陌生艺术家系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传递脐带的意象。
那我如果把绳子系在母子之间,那绳子就跳脱出了它本身的意象,除了束缚和牵制又有爱与保护的意象,正像我们和父母的关系,会真的像曾经在母体里面的脐带一样,把两个人重新连在一起。
我刚开始想把这部片子叫做“漫游在蓝色草原”,当然也没有完全确定。
后来我在和乌仁娜老师他们读剧本的时候,就突然问他们,“脐带”在蒙语里面有没有合适的翻译?
然后他就说了蒙语里的huis。
脐带在蒙语里面有很多种叫法,但是他们就觉得huis特别好,因为在蒙语里面的huis,除了脐带之外,还有连接和传承的意思。
这三个意思在不同的语境里面都会使用,跟脐带在中文里的象征用法就不太一样。
所以当时就定下它的蒙语名字就叫huis,汉语名字一直都是“漫游在蓝色草原”。
但是去了坏兔子之后,我有一次很无意地提到说,蒙语里面它还有不同的意象,大家都觉得“脐带”这个名字更能让人联想到母子之间的关系,其实也让本来被隐藏起来的“绳子”显性化了,所以后来就用了这个片名。
其实“脐带”的寓意除了想要保护母亲,实际上还表达了一种束缚的关系,一种摆脱不掉的母子关系。
人们想要通过长大离开家,建立自己的家庭,但是这条线不是物理的,是一条隐形的脐带,表面上我们可以把跟母亲连在一起的绳子剪断,实际上那条隐形的脐带一直都不会断掉,即使母亲已经不在了。
然后这个“脐带”又像这个片子里面的音乐的一样,是一条看不见的,实际上却把整个民族的情感,包括他和他母亲之间的情感,系在一起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
许:在影片的叙事中,小儿子阿鲁斯小时候以擅拉马头琴著称,成年之后成为了一位电子乐音乐人。
阿鲁斯之于马头琴和电子乐的各自演奏,始终在影片中间或出现,最终通过塔娜的话语“这里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也不该一直活在过去”予以点题。
通过阿鲁斯之于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演绎叙事,您试图表达怎样的意蕴与思考?
乔:我觉得这种变化和遗失是不可改变的,已经是发生过的事实了。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是要我们需要去探索的。
难道只是像老人一样,仅仅只是喝酒去缅怀吗?
那我们可能什么都留不住。
所以我觉得塔娜说的这个话才是年轻人的心态,也是我从伊德尔以及欧尼尔他们身上看到的。
他们以一个很正向、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文化传承问题,既没有完全抛弃传统音乐,也没有仅仅拥抱传统,而是用这个时代的方式去传承老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传承方式,能够让我们真的在时间的长河里面保留下来我们想保留的东西。
许:影片中呈现的草原自然景象唯美而诗意——河流、湖泊、牛羊、明月、骏马、篝火……在影片故事发生的背景选景及其影像语言呈现上,您有着怎样的考量与设计?
乔: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我以前没去过,在剧组中的美术和大组到来之前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事就开车出去找景,最远我自己都开过五六百公里之外的地方,因为呼伦贝尔非常大,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在这个片子里面呈现不一样的草原风貌,因为真实情况就是,它确实不只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而是很丰富的,有很多地方需要跟牧民打交道,要跟他们交朋友,他可能才愿意带你去,比如说私人草场这种地方,不是你随便想去就能去的。
而这里的河流湖泊等景色其实也跟母子之间的意象息息相关。
电影里的老房子选址在一个湖泊旁边,它其实很像母亲的羊水,这些东西可以重新孕育一个生命。
电影里面的牛羊,月亮、骏马就是草原上本身在景象和意象,也是怎样把草原生活和电影故事巧妙结合的关键点,我已经不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的意象进入了。
实际上电影里的很多意象在剧本阶段没有的,是在拍摄现场二度创作的。
就是当我真正进入到电影故事里,感受那个环境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捕捉到一些东西,而这可能也是影片生命力的一个体现吧。
比如说,告别时的超级月亮,我们在拍摄现场根本没有想到会同时碰到月全食和超级月亮。
那时候,我们在拍告别那场戏,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月牙,到送别的时候,它又变成了一个满月,这种偶然的天象巧妙地和故事的内核产生了联系。
而它本身并不是我剧本里面的规划,也不是说想拍就能拍到的。
片尾的那个阴阳树,那个树是我在开拍之前才从朋友那看到的,他开始还不想告诉我树的位置,因为他自己也有短片想拍,后来他还是把这个树也让给我,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故事。
我看到那棵树的时候就被深深地震撼了,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相较于城市它就是有你永远意想不到的一面。
两棵紧紧挨着的树,一棵死了一棵活着。
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在草原上突然看到一棵树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其实这棵树长的地方是一个很贫瘠的草原,那里都是石头和沙地,而这样的两棵树长在这一块,就像是那棵旺盛生长的树吸收了另外一棵树的营养,会让人联想到很多东西。
所以这棵树其实并不在我最初的设计之中,而只是一个很偶然的相遇,以及随之而来的很朴素的感叹。
树本身像连接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就是长生天、人间和地下。
它本身的意象又跟故事很契合,所以最后就用了这棵树,许:传统与现代、草原与都市、远行与回归,是贯穿《脐带》叙事的一条主要情感与思想线索。
这样的情感线索设定,跟您个人的成长经历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您之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随着个人成长阶段和环境的变化,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历程?
乔:我觉得在我长大的过程里,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有一段时间,我也会像一些老人一样很愤恨这种变化,很愤恨我们丢掉的东西。
比如说,我已经不会讲母语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老人在讲达斡尔语的时候,我插不上话,进入不到那个情境,是会产生一种哀愁的。
但是随着我的成长,我会去理解这种现代性到底给在这生活的人带来了什么?
我之前也到过外蒙古去调研,发现他们其实还保存着非常原始和传统的游牧生活,非常辛苦。
零下三十几度的冬天,他们仍然处于一种没有电,打水要到十几公里之外的生活状态中,一户牧民家里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一个蒙古包和一个摩托车。
其实他们对现代化的生活,对没有那么辛苦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渴望的,但是他们是实现不了的,而我们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生活。
所以,可能有些外界的人会觉得这种传统生活应该保留,但我会觉得那是一种非常自私和狭隘的想法,对于真正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来说,这是很残酷的。
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们都要到城里面读书,有一部分人之后就会留在城里,牧区就会面临劳动力缺失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怎么让这个传统游牧生活可持续发展?
一些年轻人就会把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带回去,使牧区真正可持续地生存下去,这才能保留原有的文化。
所以一味地回避,一味地排斥现代化是没有意义的,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个过程对于那些留在城市里面的少数民族也是一个挑战,因为那些曾经在草原上要遵循的规则、生活方式都不再适用,大家要去适应新的规则了,原有的成长经历中又有哪些是能被带到城市里,保留下来的?
这其实就是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的问题。
像伊德尔、欧尼尔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东西结合在一起,也不是全部丢掉。
许:达斡尔语里将民间舞蹈称为“鲁日格勒”,而“鲁日格勒”的词源含义就是“燃烧火焰”。
刚好影片结尾处最为精彩和诗意的场景,就是众人围着篝火弹奏、歌唱、舞蹈,在欢乐祥和中,阿鲁斯含泪送母亲“远行”。
将篝火舞蹈设定为影片结尾,源自您怎样的成长与生活记忆?
为什么会用篝火舞蹈作为母子二人“生命送别”的背景设定?
乔:因为我们在大自然里面长大,就经常会玩火,篝火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罕见,每逢节日都会点篝火。
电影里面也有篝火,它发着光、闪着火星、一直往天空上窜,而且能把所有人都凝聚在一起。
我认为篝火很能唤起我对草原上的火的印象,它还连接了我跟天的这种关系,所以它是我生命体验里面一种很温暖和安全的状态。
电影里面的火其实也是我对于死亡的认识,我们最后用火去送别家人。
现代社会里也流行火化嘛,人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往另外一个世界,那在大自然里面,它是另外一种形态,我们以前会认为死亡背后是冰冷的黑暗,是寂寞的。
但实际上,火的背后可能是一群你熟悉的人,一群你最爱的人在那等着,充满欢声笑语。
所以我就在送别的过程里面,用了篝火这个意象。
篝火本身将所有的家人聚在一起,是非常欢乐的,像一个盛大的party一样,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送别,就打破了我们此前对死亡的认知局限。
电影就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个场景产生了更丰富的含义在里面。
许:影片问世之后,您收到过哪些有意思的观众反馈?
在影片持续的放映与传播过程中,您获知的哪些反馈和反响让您个人印象深刻?
在收获了这些反馈之后,您个人之于《脐带》这部电影的创作与作品意义,又有哪些新的认识?
乔:我在上映之前去过很多南方城市进行路演,因为我最开始觉得南方观众产生的情感共鸣或许不如北方,但很意外的是,在一个南方城市里面,有一个观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观众可能就二十出头,跟我说他爷爷也有阿尔兹海默症,他说在看《脐带》之前完全不理解他爷爷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回到自己的家。
他爷爷老家是东北的,每次犯病就一直说要回老家。
他虽然趁着暑假一路坐火车陪着爷爷回到了老家。
但他其实是特别不屑的,他依然不理解为什么他爷爷的儿子、孙子,所爱的家人都在这儿,却还要找一个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地方。
看完《脐带》之后他终于理解了他爷爷到底是在故乡里找什么,他爷爷找的是儿时的记忆,是跟那片土地之间的联系,以及与父母之间的记忆。
这些不是他们这些子女以及南方的新生活能带来的体验。
人最后还是要落叶归根的,他爷爷回去了,才会释怀。
那个时候他也理解了陪伴他爷爷旅行的意义。
这个是我确实是没想到的,能够跟那么年轻的观众有这样情感上的链接。
另外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是在东京电影节上,当时都是国外的观众,我很惊讶两场放映里面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
因为东京电影节是一个很年轻的影展,这群长辈居然能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与这种情感,尤其是跟母亲之间的记忆产生链接,这对我触动还是挺深的。
许:在您迄今为止的电影创作中,哪些导演、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作品对您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能否为我们一一介绍?
我觉得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法国拍电影的外国导演,比如像贝托鲁奇。
他们在法国拍的电影和法国本土导演拍的电影实际上不太一样。
他们的身份跟我的境遇比较类似,都采用了一种外来者的视角。
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观感和本就身处其中的人是有差别的,不会像法国本土导演那么生活化。
但是外来的导演在呈现日常生活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抽离感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诗意化的表达。
我再回到内蒙拍《脐带》的时候就比较接近这种感觉。
虽然我在这土生土长,但实际上我对这里生活的描绘方式已经不再是一个身处其中的状态了。
我原来看到的可能全部都是细节,是很主观的认知,但是当我拉远了距离之后,从一个外来的视角再去看的时候,就又有了一种游离感。
这其实也体现在了《脐带》的视觉语言和影像风格上,它不完完全全是一个写实主义。
最近这一两年我非常喜欢意大利的埃莱娜·费兰特,她在中国出版的所有小说,我全部都读过了。
尤其是,我在拍完《脐带》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性别,也思考了我的创作应该往什么地方走,她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其实是不断隐藏着她个人的真实生活经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抉择,而她能保持这么多年。
她的小说里面反复地让我意识到大多数女性的创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受到了男性创作者的影响,包括看的小说也好,电影也好,我们很难从中剥离出来哪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看到的并想要描绘的世界。
而我通过她的作品重新认识了我自己,也再重新认识我自己的错误。
其实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去找到那些不能理解的,再通过创作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事物。
还有一部跟草原民族相关的作品叫《流水似的走马》,是鲍尔吉·原野写的,对我影响也很大,是我在写《脐带》剧本的时候经常会看的。
这里面有很多散文,书中的文字非常具有现代性的美感,跟我以往读到的有关草原的小说、散文非常不一样。
里面的文字风格甚至影响了整个《脐带》的电影剧本写作。
许:您能否介绍一下如今您的生活状态?
《脐带》问世之后,对于您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觉得我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无业游民,然后只有小部分时间是电影创作者。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养活我自己的生活,并且需要真正地深入到生活里面去观察,去学习,并找到那些创作素材,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才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
我几乎不会以一个电影导演或者编剧的角色与周围的陌生人打交道,他们问我做什么。
我更多会说我是拍视频的,就是会让他们对我的兴趣少一点,把关注留在他们身上。
许: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后续创作计划?
未来是继续在民族电影与艺术电影领域深耕,还是会考虑涉足商业电影、类型电影甚至主旋律电影?
我接下来也要跟《脐带》告个别,踏入新的成长了。
目前还没有拍摄商业电影的打算,我现在最感兴趣的还是回到故乡,去描绘这个地方年轻人的生活,后面几部作品应该都要写这里的故事。
包括刚才有跟你提到的酒鬼的故事,还有一个女性私奔的故事,其实都挺有现代性的,也是我们这一代或者这个时代会面临的问题。
但是可能这个地方它的解决方式会跟城市里面有一些差别,包括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就是蛮有意思的。
(本文于2024年7月4日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刊发。
)
4 ) 终点不是结局,而是新的开始
🎬《脐带》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后,病情使她变成了一个孩子。
夜里跑出家门迷路在荒野,整日哭闹着要找阿爸阿妈,穿上漂亮衣服就不肯脱下,拿着随身听即刻随性起舞,然后就舞至了水泽的边缘。
总之一句话,她必须活动在儿子目之所及的地方,所以儿子便用一条麻绳栓住了彼此。
于是,在辽阔豁达的大草原上,儿子带着母亲踏上了溯回之路。
白天,他们遇见了迷路的小羊;夜晚,他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原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竟也可以如此和谐共生。
以至于当死亡临近之时,如一只鸟展翅飞向天空。
在旅途行至最后的夜晚,母亲从容微笑着说:“谢谢你,我感觉很幸福”。
儿子流着热泪,解开了那根如脐带的绳子。
这一刻,生和死紧密相依、互为归途,仿佛是一颗半枯半荣的古树。
生命这场旅途,我们经历、遗失、寻找、归零,依稀望见尽头时,却总在追忆过去。
所以,无论正处于人生哪个阶段,都请用心去珍惜这趟旅程,用心感受每一次日出日落,珍视每一个与你同行的人,勇敢积极面对每一个挑战,因为,这就是人生,一段无法预知的奇妙旅程 。
脐带 (2022)7.92022 / 中国大陆 / 剧情 家庭 / 乔思雪 / 巴德玛 伊德尔
5 ) 断不了的双向联系
以下内容仅为个人的一点纯主观评价,毕竟每个人的感受和喜好不同都有所不同嘛,不喜勿喷噢。
四星。
基本符合个人期待,比较推荐去看。
可以感受到影片真挚的情感与剧组的诚意,尽管剧情十分简单,却能够直接触动人的内心,带给人一种哀而不伤的感觉。
让我体会到了家庭、故乡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
(1)这部电影的拍排片特别少,偏冷门,也期待能有更多人可以在影院大荧幕上看到这部电影啦。
不过可能是因为我看的这场有映后见面会的原因(比较可惜的是这场只来了监制姚晨,而且我去迟了,没有领到海报和明信片之类的小礼物),基本上是都坐满了,观影氛围挺好的,玩手机的比较少,观众比较热情,看得比较认真,提了好多问题。
(2)虽然是一部地域性和民族性相对较强的蒙古族电影,但普通观众却也能够很好地带入其中。
作为本片导演兼编剧乔思雪的新人作品,还是在疫情期间拍摄的,值得鼓励一下。
(3)本片呈现了内蒙古的独特风光,有曹郁在中间进行调度,本片的拍摄技术高超,视觉效果极佳。
在内蒙古的广袤大地上,草原连绵不绝,天空湛蓝如洗,仿佛让人置身于广袤无垠的世界中,有种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的感觉。
(4)影片的配乐是本片的一大亮点,所选取的音乐比较贴合,让人感受到内蒙古音乐的独特魅力,一首首旋律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一些美好与哀愁的情绪。
(5)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家,那个家位于熟悉的故土,家里有着爱我们的父母。
可是,父母在成为父母之前也曾是孩子,也曾深深地眷恋自己的爸爸妈妈。
影片的主题相对比较明确,就如电影标题“脐带”那般,本片主要讲述了父母与子女、游子与故乡之间的羁绊,父母对子女,故乡对游子,始终都有着一层断不了的双向联系,这种联系既是爱也是束缚,我们终将走向独立,剪断那根“脐带”,与亲人和家乡告别。
另外,本片还涉及了一些“阿尔茨海默症”、“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碰撞”以及“生死轮回”的议题。
(6)影片里最后出现的那颗一半生一半死的树真的有一种诗意的美(据说这棵树是真实存在的)。
这颗树一半的树冠蓬勃向上,生机盎然,另一半则枯黄萎蔫,这不仅是一种生命的缩影,更是一种坚强与美丽的象征。
6 ) 每个人都要割两次脐带
很细腻,音乐动人。
没有搞内部东方主义,人的境遇,天下是相通的。
不止这部,鲜卑主题的作品基本都没有,不像吐蕃是重灾区。
上一部印象深刻,《海的尽头是草原》。
本片借女二的口说:我喜欢你搞的东西,我们不是只有马头琴和呼麦,也不是永远生活在过去。
女二很美,质朴刚健。
最后母亲去了长生天,儿子骑着跨子,找到了半枯半荣的树。
7 ) “此心安处是吾乡”
1.生死相依阴阳树/生的一侧像子女,衰的一侧像父母。
他们以枝干盘根错节。
生的一侧开枝散叶,衰的一侧枯萎凋落,像一个生命的轮回。
新生和衰亡本就是对立,这样一个共存体像极了以血缘关系联结彼此的生物。
(感谢导演映后应证了我的猜想)
2.脐带和绳索/母体和子体以脐带为连结,物理意义上剪断了但会因为凝聚的骨血而绑定;儿子用绳索绑住母亲,好似回到胚胎时期,不同的是主客体身份的转换,儿子变成了驱使者,母亲变成了被动方。
母亲心智在倒退,儿子顺着自然规律在前进,睡前吟唱的歌谣,现在换我来唱给您听。
3.夜光篝火/游牧民族的旋律直击心灵,夜幕下的一切都是那么快乐、祥和、温暖、美丽,大家的脸庞被火光照得闪闪发亮,迸发的火星好像散落的星屑。
舞姬吟唱着动人的歌谣,身边是一如记忆中慈祥的爸妈。
儿子也终于挥刀斩断那根绳索,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静谧夜色。
好美,美得让人心碎。
4.独行归旅/其实直到昨天我还在猜测阴阳树是否真的存在,会不会仅仅是一个意象产物,但那已经不重要。
在我看来那棵树似乎已经化为阿鲁斯心中母亲的化身,在她的荫蔽下,他得以在蓝天下安躺。
5.景色好美,想去草原抱小羊,牛牛好可爱~
8 ) The cord of life.
The cord of life. 臍帶,是片頭草原上蜿蜒曲折的河流,也是綁在母親和兒子身上的繩子,是羈絆,兒子為了防止母親走丟的工具,也是束縛,如Tana所說的這是自私的。
很明顯這個草原上的故事並不是講述現代生活和傳統牧民生活的碰撞啊,更多的是關於生命的思考吧。
生命的輪迴很神奇,人年老了會重新變得跟小孩子一樣,或許人活一輩子也只有這兩個時期是完全不用考慮自己的社會身份吧,母親不再是母親,而是她自己,她也想自己的爸爸媽媽,她也想回她自己的家。
所以最後在火光紛飛中,映著月光傾斜在湖面上的一片湛藍,阿魯斯把「臍帶」剪斷,把羈絆剪斷,讓母親迎接自己的死亡,把束縛剪斷,不再留著母親,讓她跟隨自己的爸爸媽媽一同遠走。
樹,是我的家。
那棵半生半死的神樹,一半枯死,一半枝茂葉繁,就像母親那早已逝去同時又永存在心中的家。
阿魯斯和母親都找到了家。
最後,伊德爾未免太帥了,景色和音樂過於令人迷醉,可惜排片太少了,希望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去看一看。
馬上給媽媽打一個電話。
9 ) 生之知觉
如果说北京大学有哪个地方足够承载我迫切需要独处,又不至于带我堕入虚无的地方,那一定要属五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
这里没有任何人来往,而我却可以坐在这里,低着头就毫不费力地看着,在操场一圈圈奔跑的人们。
今天看完电影,带着眼角未干的泪,我从百讲再次走到这里,爬上楼梯,将浆布包从肩头取下,贴靠在怀里。
今天我不听爵士乐,只想在这里聊聊这部电影。
我真的也不明白,为何泪水便顺着那草原上轧出的车辙迹,悄无声息地流着、流着。
当苍穹的蔚蓝将一天中最后的火热挤出了视线,恍惚间,我坠入了湖水敲击堤岸生成的泡沫之中。
明亮的灯火不再,而透进的光线熹微,使得这里有些晦暗,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缺乏色彩的,光在外侧不均匀地打着,一切都是那样模糊。
即便如此,这种感觉确实温柔、舒适的,它有些闭塞,但总归,有着别处不曾存在的放松。
朦胧之中,眼前闪起了篝火。
它断断续续地,火光顺着并不凛冽的风在外面飞舞着。
这里似乎更亮了,我看清了四下的更多,但明亮之中,原本黑色的地方似乎更加黯淡了,一些不和谐的声响从湖面传入耳中,隆隆隆,隆隆隆。
天啊,不要再有更亮的光线了。
带着些许的颤动,我的内心祈求着。
而那渐强的篝火也渐渐与消失的夕阳中和,回应了我。
蓦然中,远处的大地上,卷起了一阵风的柔波。
她轻轻掠过,拂动着这小小的泡沫。
起初,她加剧了我的担忧,直怕将那薄薄的弧壁冲破。
可那夹带着泥土和青草的风,只是轻轻地抚摸。
她时断时续地诉说,却不曾将这泡沫吹破。
甚至,她掩住了莫名的声响,替以温柔地诉说。
此刻,我与她相隔,此刻,我不再畏惧树影斑驳。
“你是草原的鹰。
未来,请乘着我上升、盘旋,去向那片属于你的天空。
”“你是千里光的子,此后,请伴着我的余力飞腾、舞蹈,停留在你自己的角落。
”“你是……”轻风只是徐徐地吹着,吹着。
恍惚间,五四的灯光再次突入了我的视线。
王克桢楼上高悬的旧校徽,在暗淡中闪耀着来自中关村的灯火。
一瞬之间,轻风又起;一瞬之间,又被泪水淹没。
10 ) 《脐带》之外
遥远的草原小镇,电影却是连接我和世界的生命之绳。
我出生在内蒙古鄂温克旗的小镇里,九十年代的时候是每周末和父母看电影录像带度过周末,千禧年之后我开始自己租DVD看电影,北京奥运会之后网络下载电影资源永久替代了所有其他观影方式。
看电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穿梭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之中,体会生命中无法体会的情感,抵达无法抵达的世界,让我的视角不再集中在一件事情的正面,我学会站在侧面看它,绕道背后去看它。
也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和世界对话的欲望。
我的故事里总有一个游子,在世界的舞台上流浪。
或许是身体里的游牧基因在作怪,我的故事里总有人回到故乡,或是有人在地球的版图上游牧,但他们心中都有一片蓝色圣洁的高地。
生命中的偶然和突如其来的告别给生命以启示,伴故事里的人不断前行。
拍这个电影还是因为我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以及对与亲人告别的恐惧。
通过一个绳子将一对母子系在一起,探讨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探讨与故乡的关系,以及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
因为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面临和亲人告别,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支撑我们面对离别和死亡。
我想我出生长大的这片草原给了我答案,就像片尾母亲的那句“时间会一直不断向前,就像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一直盛开”生命有来有往,我们要接受万物的无常,以及生命在自然里有轮回。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离开草原到城市学习生活,我们把烙印在自己身上的文化带了出去,怎么让这份文化在城市里生根发芽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探索的,还有一些人从城市返回草原,把城市里的现代化文明带回到草原,怎么让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帮助我们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下去也是变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
其实伊德尔我在写这个剧本之前就认识他了,他做音乐的理念给我很大启示,他从小学习马头琴,到了北京他在探索怎么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他开始尝试用年轻人的视角,大众最能接受的传播方式做他的音乐,这跟我想拍这部电影很像,用我们年轻的视角,年轻人的方式记录时间,讲一个最质朴的故事,传播来自自然的信仰。
所以出走和回归不是对立的,像死亡和新生一样,就像片尾的那棵阴阳树一样,在盛夏的时候,枯萎的那棵树将它的营养传送给枝繁叶茂的那一棵树,让它长出新的形态,向阳而生,就像我们的当代文明建立在传统文明之上一样,以自己新的样貌不断繁衍生息。
蓝色的蒙古高原,心中的高地,你把我们凝结在一起。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拍一个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草原电影,把来自故乡的味道和草原的哲思用拍电影的方式保存在时间里。
很多人会说作为导演乔思雪很幸运,处女作就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确实作为一个处女作导演来说,能和这么业内顶级的主创合作,确实是一个小的奇迹,而且这个奇迹也很难在未来复制。
作为《脐带》的监制曹郁先生和姚晨女士,为《脐带》倾注了他们最大的热情和支持,从剧本到这个片子走进电影院,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疫情期间我们每天视频通话讨论剧本几个小时,把它打磨成一个真正可以接受考验的拍摄脚本。
拍摄期间监制曹郁老师除了白天要完成摄影师的创作,晚上还要和把控后面的拍摄计划,拍摄尾声曹老师经历家人离世,忍受巨大的悲痛和压力再次回到剧组陪我们拍完最后的两场戏。
最初在姚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为演员定下表演基调,作为表演指导老师的她还要负责帮助那些没有表演经验的素人演员进入角色,让他们真能在电影里活起来。
作为监制的他们,付出的远比监制这个工作要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热情。
在这个独特的拍摄体验程里面,他们不断地帮我认识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帮助我建立在片场的自信,直到这部片子走进电影院,他们还在四处为《脐带》而四处奔走,只为这部真诚的作品能跟更多的观众见面。
《脐带》的出品人制片人刘辉,最初在first电影节创投挖掘了这个故事,并全程陪伴《脐带》走到了最后。
两位制片人刘辉、胡婧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犹豫是否要继续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从未表现过丝毫的退缩,给了我心理上极大的支持,让我有信心坚持下去把这部片子做完。
更是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找到了我们的声音指导富康,美术指导赵紫冉,造型指导李宙,这些对我来说遥不可及的主创班底,给了《脐带》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最早进组的美术指导赵紫冉,往返于冰天雪地的森林和城市间,亲手打造了那个如梦似幻如同子宫一般的老房子。
造型指导李宙,跑遍了呼伦贝尔的民族服饰店、牧民家只为找到那些有生活痕迹的蒙古袍。
执行制片人姜乐从自己的仓库里拉来的帐篷桌椅板凳,在篝火那场戏因我们用完了六吨的木材,没有可烧的材料,把他带来的桌子椅子都扔进了火堆,只为让我们能再多拍几个镜头。
这部电影里我们的两位主演,巴德玛老师和伊德尔从最初的陌生人,慢慢的相处成了真正的母子。
巴德玛老师身上所带有的轻盈、纯真、质朴的气质,让母亲不再是剧本里角色,而便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草原母亲。
伊德尔奉献了他所有对生命和音乐的感受,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阿鲁斯这个角色。
还有那么多普通的素人演员,他们构建了这个电影最真实质朴的瞬间。
剪辑指导张一凡,将脐带的剪辑风格调整到了一个最靠近观众,又最大程度保留创作者意图的版本。
声音指导富康,在声音后期制作中,根据他的真实情感体验手动推音轨,把空旷的草原填满了属于人物内心的声音。
调色师张亘,将如此丰富细腻的色彩带给观众。
乌仁娜、伊德尔、欧尼尔三位音乐人的音乐作为一条隐形的脐带,将这部片子里母与子的情感纽带贯穿始终。
除此之外这部片子的大部分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来自于呼伦贝尔当地,他们带着对电影最赤诚的爱和热情,帮助我们拍完了这部有独特风味的草原电影。
《脐带》有种神奇的力量,将所有喜爱这个故事的人凝结在一起,帮助这个故事从最初的剧本到今天走进电影院,它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借助光影、声音、音乐的力量礼赞生命与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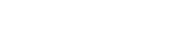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献给妈妈的音乐专辑》
《漫游在蓝色草原》的原名还是更符合这部电影的气质,《脐带》这个名字对意象的提炼则多少直白了些。看得出导演的真诚和对草原的深情,她的创作出发点并非来自社会现实,而是源于一种情感的拉扯,有关家庭生活中遥远的记忆。巴德玛面庞里的山川湖海,都被导演细腻地捕捉了下来。就成片内容而言,确实有很多横生的枝蔓是无关主线的,似乎只是为了把这个概念抻成长片的体量,但选角、配乐、摄影这些技术环节都完成得太漂亮了,到最后剪断脐带、放归母亲的段落,那种深沉而悠远的情感一下氤氲开来。和《鱼花塘》一样,在这个时代,是特别昂贵的私人电影。
看电影时候嗷嗷哭,看短评里的男影评人表演又噗嗤笑出来
作为剧情片的话实在是不合格,内蒙古这么美丽的地方其实随便拍拍都可以很吸引人吧,如果让人频频走神那就真的有问题了,还不如拍个自然风光➕音乐的纪录片,这看起来像是大学生交的期末作业。
听不懂,看不懂,看得好困,但里面配的几首音乐还挺好听的
上一次剪断脐带是初遇,下一次剪断脐带是告别。
如果我今天没有去看这部电影,那我的人生将会又多了一件遗憾。
有特色风情
故事温暖,画面诗意的一部电影作品!
空有美感没有才华的草原风光PPT
4.5⭐ 即使抛开我对女导演无理由支持,这也绝对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片子。一个好故事,难得一见的是,一个被讲明白了的好故事。片中非常多的使用了象征性的符号,但很真实自然,没有强烈的堆砌感。脐带联结的是血缘、母子、游子和家乡的土地。它孕育了生命,也困住了生命。而妈妈的执着,与其说是寻根,可能更是找回曾经的自己。“自己”,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母亲,是那个被还活着的人遗忘了的跳着舞的少女,在那棵一半是生一半是死的树下。
资料馆# 男主的表演有点糟糕,有几处我都觉得他睡着了hhh。基于大草原的摄影真美,也就这个吸引我看下去了,其他没多大惊喜。
哭了😭曹郁到底吃什么长大的 摄影这么牛逼
看到了篝火纷飞、明月点亮湖面、众人起舞的场景,那一刻我倍受震撼,眼泪似乎是为了想要记下此刻的文化图景,感受到导演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切断绳子的意象,总觉得不只是切断脐带这么简单,或许也在表达切断血缘、切断自私的眷恋。“生命的轮回”通过每一个细节传递得非常准确,创作者回答了自己关于生命的追问。最惊喜的是细节处理的都不土,洋气,很多极其容易变矫情的情感戏都用幽默/高级的方式处理了,母子戏的处理值得学习。音乐也可爱。儿子:“她会永远爱我,只是她不记得了。”母亲:“没事,时间会一直向前,就像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常青。” 什么神仙回答,极其具有牧人的特色,不含任何“牺牲、pua意味”的爱,对母亲最好的放手也许就是放她回到她的来处,这是草原的答案。
为了这个题材而拍这个题材,很制式。
拍得既老土又肤浅…
这种纯粹为了拿奖的电影确实不太适合普通人看,很难集中注意力看下去。故事发展属于那种典型的打哪指哪型的。没有什么抓人的包袱,就是一直这么演。亮点:歌比较好听;男主长得像胡歌+白客。
#海南#画面不错,监制曹郁的摄影指导发挥很大功力,但故事老套。妈妈扮演者是海的尽头是草原里的妹妹,情绪渲染到位,但终究有点用力过猛。男演员很灵。
东亚人伦关系实录。脐带的具象化初始确实让人感觉有些稚嫩,但最后剪掉的那一刻却极具冲击力。爱是对孤独的恐惧的抚慰,爱又是对自由的渴望的成全。相互依偎着的两个人是出于爱,送彼此离开的两个人同样也是出于爱。电影的音乐和摄影都好美,想去内蒙古自驾,在流淌着的马头琴声中追逐落日。
想起妈妈跟我说外婆去世前几日在病床上经常叫妈妈,她想扔掉生命里所有的角色、干净轻盈地回她的来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