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渊而立》剧情介绍
利雄(古馆宽治 饰)和章江(筒井真理子 饰)结婚多年,共同养育着女儿萤(筱川桃音 饰),虽然生活平静毫无波澜,但夫妻两人之间早已经没有了感情的交流,仅仅维持着婚姻的空壳。利雄的朋友草太郎(浅野忠信 饰)出狱后来到利雄的工作室干活,寄宿在利雄家中。一边是冷淡的丈夫,一边是和善温柔的同居人,内心空虚而又寂寞的章江很快就在草太郎的攻势之下沦陷了。 然而,当章江拒绝了草太郎的求欢后,草太郎便就此失去了踪迹,而萤亦遭遇了意外,余生唯有在轮椅上度过,利雄和章江不知道草太郎到底去了哪里,只知道萤的意外和草太郎有着脱不了的干系。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午夜的柳枝八月钱潮碧昂丝:新生与超越杀手寓言她妈妈不喜欢我女生规则恐怖假日当代风流失衡凶间狄仁杰之焚天异火悸动移山的父亲努尔哈赤秘史潜行吧!奈亚子RememberMyLove(craft先生)Office有鬼勇敢的人诱惑雪豹子夜叹息弗兰肯斯坦之恋混战特工公主代理人日本Noir-刑事Y的叛乱-男奴时代中途客栈波利安娜天才枪手欢迎光临流放者食堂!足球使命笑傲江湖
《临渊而立》长篇影评
1 ) 日式《西西弗神话》
这部电影大概讲了加缪书里的一个观点:荒诞与自杀。
人生是否值得是回答自杀的根本,生活是否荒诞是判断人生是否值得的根本,自杀是解决荒诞的切实手段。
加缪说一人拿着刀去冲击拿着机关枪的阵地是生活的荒诞性。
电影就是由一个个生活的荒诞组成的,一对夫妻结婚生子却没有感情是荒诞,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去容留杀人犯是荒诞,信守一个承诺却被受信人遗忘是荒诞,一个陌生人突然加入另一个家庭而不奇怪是荒诞,为了一个陌生人的热情而出轨是荒诞,孩子喜欢陌生人而不是父亲是荒诞,孩子受伤瘫痪使没有感情的夫妻有了共同的生活目标又成了有感情的夫妻是荒诞,最后生不如死的是这两个荒诞的夫妻,死既是生的反倒是无辜瘫痪的孩子。
最后的最后有罪的人还要荒诞的活在生活里,无辜的人本该幸福的生活却想死得其所。
人间是否值得?
有的人在痛苦中自杀,有的人快乐中期望被杀。
或许,这对夫妻永远也找不到凶手,因为那凶手不是浅野忠信而是荒诞的生活。
2 ) 《临渊而立》剧情初探
整个片子围绕一个自私自利、没有担当和责任感的男主人公利雄展开。
平淡的外表下,一个漠视亲情、友情、爱情的小男人。
由于片子没有交代利雄和草太郎是什么关系,因何事合谋杀人,搞得整个剧情如云里雾里,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只能靠猜测和判断。
看了很多影评,由于大多数或全部与我的判断相去甚远,不得不立文为解开真相提供部分借鉴。
第一疑问:利雄和草太郎的关系及合谋杀人事件的前因后果 利雄和草太郎可能是发小,关系甚密。
利雄可能喜欢上一位女子,但这个女子已有男朋友,为夺人所爱,相约草太郎干掉这个男子。
信奉哥们义气的草太郎欣然同意,共同谋杀了这个男子。
利雄成功占有了这位女子。
第二疑问:利雄的女儿萤是不是草太郎所害 我认为萤是出了意外车祸,不是草太郎所为。
由于利雄夫妇都怀疑是他干的,草太郎众有千口也难辨,只能远走他乡。
第三疑问:孝司是不是草太郎的儿子 我认为孝司不是草太郎的儿子,恰恰是利雄的私生子。
那为什么那位受害者的女友说是草太郎的儿子呢?
女子不能接受这个用情不一的利雄就是儿子孝司的亲生父亲,对那个两肋插刀,几十年来一直为受害者家属写信忏悔并寄钱的草太郎心存好感,在临死前告诉儿子草太郎是亲生父亲更可能。
以上三条,为什么我会这么判断?
一是从剧中每个人的对话中,找到蛛丝马迹;二是从利雄、草太郎迥然不同的性格和为人判断。
我个人觉得比较准确,这里就不一一指出依据了,一切尽在剧中。
3 ) 莫比乌斯
以前没有看过深田晃司的电影,所以对于其影片的“作者性”无权作出评论,那么就简单的聊一聊对于本片的看法,权当是观后感吧。
作为一位80后导演,深田晃司对于生活的感悟和对于影片整体性的把握都体现了他的成熟,镜头语言克制、内敛,叙事上做减法,但生活的细节处理毫不含糊,剧情交代的大量留白愈发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个突然来到利雄和章江家的草太郎究竟有怎样的过去?
他和丈夫利雄之间有什么过往?
他来到这的目的又是什么?
观看本片前我没有看过影片简介,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看任何片都不想先去了解它讲的是什么,好像事先了解的越多,就越觉得影片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我现在喜欢在无目的的、随机的选看影片中体验那种类似发现珍宝般的喜悦,回到了旧日时光没心没肺地享受影片,这种感觉好棒!
还是忍不住说几句影片技术层面的几个闪光点,个人非常喜欢几处室外的移拍镜头,像草太郎跟在小女孩小莹后面谈起她的风琴课的场景,还有章江和草太郎两人在路上有说有笑地聊着的画面。
室外的这几处场景,画面干净但透着一股阴冷的不详之感,应该是用了减光镜为了保持影片整体色彩的一致性,也为了和影片阴郁的格调达成统一和谐。
还有影片两处的转场用的也不错,一处是女儿小莹在弹钢琴,她看到妈妈拿着给她做好的表演服后,飞快的跑向妈妈,接下去的镜头她已经是穿着表演服并跑向屋外;另一处是章江梦见自己和恢复正常的女儿坐在路边树荫下的长凳上,突然脚被冲过来的水淹没,下一个镜头就是她们母女坐在了海滩的长凳上。
其实,诸如此类的转场并不是新鲜的东西,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好莱坞的影片中有很多类似的转场,但后来逐渐地被大多数的导演或剪辑弃用了,取而代之的是“生切”,转场本身不再具有时空压缩的平滑过度作用,说明导演也不想在转场上花太多的心思,很高兴深田晃司还固守着这一古典的手法。
回到剧情上,影片开始以女儿小莹弹风琴的背影镜头切入,接着是忙碌早餐的妻子章江,在一边看报纸的丈夫利雄,吃饭前母女祷告一番才开始进餐,而利雄在一旁还是一声不吭地边吃饭边看着报纸,就连妻子和他讲一会有个捐赠活动要参加,他都没有应一声,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到了今天的地步,但他们的婚姻看上去已是行将就木,名存实亡。
然而接下去利雄的朋友草太郎的到来,给这个充满压抑压抑氛围的家庭带来了欢笑,草太郎教授小莹风琴,所以小莹也很喜欢他,妻子章江也喜欢找他聊天,他们甚至还一起出去春游,一来二去的相处,章江和草太郎都没能把持住自己,他们互相拥抱并亲吻对方,但是章江拒绝了草太郎进一步的举动,这无疑激怒了他。
接下去利雄发现草太郎在屋子外面,身边躺着头部满是鲜血昏迷不醒的小莹,草太郎试图要解释但最终还是悲愤地离开了,一罪未平,又添一罪,这可能是上苍对草太郎的怨念和罪孽的惩罚。
小莹捡虽然捡回来一条命,但成了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半植物人。
小莹究竟是意外受伤,还是草太郎伤害了她?
影片没有讲,但我觉的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是导演想要表达的。
利雄一家人的命运从此被彻底地改变了,章江因为内疚而患上了洁癖症,每天不停的洗手,利雄着魔一般地想把草太郎找出来,想了解女儿当时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整整八年的时间过去了,草太郎似乎从人间蒸发了。
实际上,草太郎在住进利雄家不久,就和章江坦白了他曾为了自己坚守的原则杀了人,坐过牢,而且他经常的给死者的亲人写信,以期望得到灵魂的救赎。
利雄是当年草太郎杀人时的帮凶,草太郎并没有供出他而自己扛了下来。
他在和利雄一家春游时,曾和利雄半开玩笑地说,他才是应该有女人和孩子并过这样生活的人。
他到利雄家,相当大的原因是他没有供出利雄,而利雄却从来没有去监狱探望过他,他是带着恼火和敌意的,他嫉妒利雄在外面世界自由地活着,有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但事情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小莹的受伤,这应该不是他的本意。
实际上,作为他杀人的帮凶,利雄虽然没有坐牢,但他的灵魂也随着当时他的行为就已经被套上了无形的枷锁,他不曾像正常人一样地享受天伦之乐,他活在内疚和惶恐中,他和妻子冷淡的关系就是源于他把自己关进了内心的牢笼,一朝做错,一世偿还。
女儿的意外让利雄觉得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是报应,他做的孽,祸降到小莹的身上,他极端痛苦但却感到得到了些许解脱,他觉得这些年压在他心上的巨石似乎变轻了许多,这八年的时间他和妻子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他看上去比八年前还要精神,他觉得生活又燃起了希望。
然而真的是造化弄人,草太郎的儿子孝司却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他的工厂工作,从没有见过父亲的孝司根本不了解他父亲和利雄家的恩恩怨怨,得知他们的父子关系后,利雄想利用他找到草太郎。
后来利雄接到私家侦探的线报,一家人和孝司去找草太郎但未果。
妻子章江抱着女儿小莹从桥上一跃而下,利雄救上了妻子,然而救小莹的孝司和小莹一起昏迷在岸边,利雄疯狂地拍打着孝司,哭嚎着按压着小莹的前胸,影片在他撕心裂肺的哭声中结束…… 宿命轮回使每个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都没能逃脱命运的安排。
真是“万般皆带走,唯有业留身”。
4 ) 关于《临渊而立》的一些疑惑与补充
剩下一星留给未知的人性。
整部影片里有很多未解释的地方,比如第一次八坂为什么杀了人又为什么得到了原谅,比如八坂的信到底是不是寄给被害者家属,又比如萤究竟是不是八坂谋害的?
八坂和章江第一次认真谈话的时候,他说一生中犯过的四个错误:将守信作为信条,看得比法律更重要;认为别人也是这样做的;坚信自己不会犯错;为了守信而去杀人。
结合后面出现的八坂的儿子,和八坂寄信的问题,不知道以下猜测是否合理:八坂的确是寄信给受害者家属,但被杀的男子是八坂女友后来的丈夫,女友没有守信,也可能是被逼嫁给了另一个男子,但那时女友已经有了八坂的孩子,而八坂不知晓。
而将守信作为人生信条的八坂,出于对其人生信条的信仰以及愤怒,便杀了男子。
从这个假说看来,八坂对于章江,是诚实的。
当然也有可能,八坂从一开始就是以复仇为目的进入利雄的家庭,那么他做的一切都只是蓄谋接近章江,为了报复利雄。
但从谈话的细节以及对于萤的关爱表现来看,就算八坂一开始的目的复仇,之后的行为应该也不完全是表演,有一部分应该是真情流露,他应该是真心羡慕和嫉妒这样的家庭的。
关于荧的受伤:有三个假设,一是八坂蓄意谋害;二是八坂过失伤害;三是与八坂无关,他只是恰好出现在现场。
如果假设一成立,那么八坂便是从一开始就想用尽手段报复利雄,与他妻子通奸伤害利雄不成,便害他们的女儿。
那么电影最应该被批判的人便是八坂:基于错误的人生信条下杀人,出狱后见同谋的朋友生活的很好而心生妒忌展开残忍的报复,是为无情残忍之徒。
接着是假设二:八坂过失伤害萤。
在利雄家寄宿一段时间以后,八坂会发觉利雄和章江的婚姻是名存实亡的,而八坂是爱章江的,同时也清楚章江爱自己。
于是,八坂在向章江的最后一次求爱不成后,爆发了邪念,在途中偶遇回来的萤后将她误伤,被发现后无颜面对利雄一家,选择消失。
假如假设二成立,那么我认为八坂利雄和章江都是有罪的。
最后是假设三:八坂除了第一次杀人犯罪以外,他都是一个遵从自己人生信条的好人,他没有检举也没有想过要拆穿利雄帮助自己杀人的事实。
虽然他想和章江在一起,也是基于利雄章江二人名存实亡的婚姻事实。
他最后没有伤害萤,只是恰好路过,却又怕解释不清而消失。
假如假设三成立,那么在萤被害一事上,八坂就成了一个不该被批判的人。
从电影后半集来看,我觉得利雄更认同假设一,他果断地认为自己的妻子已经跟八坂发生过关系,也认为萤就是八坂故意所害,同时他还认为萤变成这样是自己的解脱,他将他认为八坂和妻子的罪恶变成了自己罪恶的出口,于是他让章江感到恶心。
而章江应该更认同假设二,她认为是自己拒绝了八坂,才会让八坂出于愤怒而误伤萤,所以她才会对萤倍感愧疚。
而章江对于利雄以前的罪恶也并不了解,认为自己才是萤受伤最大的帮凶。
其实无论相信哪一个假设,都是出于角色本身的。
相信利雄和章江都不愿相信八坂是个无辜者,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罪恶,而每个人的罪恶都需要一个出口。
5 ) 主的仁慈也抵不过人性的弱点
主的仁慈也抵不过人性的弱点,悲惨的故事!
剧情发展也比较慢!
饰演萤的真广加奈只演过这么一部电影,有点遗憾!
宗教戏的铺垫埋得比较好,主保佑了萤没有失去生命,进而坐上了轮椅,日后瘫痪得萤再也没机会在吃饭的时候感谢主的救赎!
父亲依然自己吃自己的,对于母亲来说吃饭也是为了女儿吃,也是为了女儿而活,人到最无奈的时候主也无能为力!
人性得选择与主得仁慈,怎样才能救赎自己?!
6 ) 我們都有罪,那些無法左右,又讓我們無法自拔的,是我們的原罪 。
「淵に立つ」 ——我的心底是一片盛滿眼淚的湖水。
我始終認為波瀾不驚比驚濤駭浪更高級。
就像緩慢的敘事在平靜的生活之中展開,其實划開了一道巨大的傷痕。
自以為是的擔當其實是自私,八坂以為自己為朋友隱瞞了共犯的存在,現在擁有妻子女兒幸福家庭的俊雄心裡就生活得心安理得並且應該時刻感激自己。
憑什麼報復,是你自己選擇的不說。
憑什麼嫉妒,你的緘默看來不是真心地袒護,只是在配合你自戀的角色。
俊雄要感激你帶給他的負擔嗎?
他什麼都沒有做。
你沒有的而俊雄有的幸福對他而言是真的幸福嗎?
你想看到的是他不可以過得比你好,因為你生活在深淵裡,所以他也要和你一樣不幸。
為什麼要讓自己的負擔成為別人精神的折磨?
對日子昭敏從不關心一味地冷落,既然承擔著重負的生活已經索然無味,憑什麼要讓一個毫不知情的最親密的人分擔去你的荒涼冷漠。
為自己的罪過為什麼不自己承受,清算人情自己欠的自己償,憑什麼心安理得地算在妻子女兒的頭上?
你說女兒被你欠下人情的八坂搞成了植物人就算是對你的懲罰了。
一直受到妳冷漠對待的昭敏被溫柔體貼的八坂輕輕敲開情慾的門扉卻依然為你守住了底線,你卻以為妻子和朋友已經發生了關係並以此為由,暗示昭敏不可以責備你??
究竟該怎樣選擇一段婚姻呢?
在全家人的生活遭受了巨大的打擊,心靈與身體都遭受了巨大的創傷之後,男人才開始關心保護你,因為他自己的過去。
會不會太遲了呢?
螢,貴,還有貴的母親呢?
如何忍心說他們的存在是一個錯?
為什麼人人都選擇默默地承受卻默不作聲地走入圈套?
為什麼就這樣跌進生活的漩渦?
比起暴烈的形式,我更喜歡這樣緩慢而不漏聲色的訴說。
一次眼神的流轉,一句欲言又止搪塞的回復,一個曖昧模糊又彼此心領神會的象征。
長鏡頭的緩慢推動,畫面的定格。
這也正是我喜歡電影勝過戲劇的地方。
隱匿在生活之中,除了刻意彰顯背後的別有用心之外,生活全部呈現給你了,只看你看不看的透。
生活就是一條寧靜的長河,有看得見底的淺灘和不可測的深淵。
一念之間就可以臨淵而立,那時的你要不要回頭?
7 ) 色情设计
看评论,一半在讲罪与罚,一半在讲鬼。
没有人提到占据影片大部分的时间都非常色气...希望不是我的问题。
一个雅致的影像外观,藏有许多性喜剧/AV的特质和逻辑,最后却落达沉重的命题上。
浅野忠信是古馆宽治的“身”:起先是“完美无瑕的好男人”(无论是伪装还是事实如此),以试图性爱未遂为代表,展现男人于家庭中控制欲无法满足后的畸变。
古馆宽治的温良替身浅野忠信第一次出现时:
接应他的是古馆宽治——丈夫。
筒井真理子无法看见这样不安的情景。
直觉,她提出抗拒,丈夫却领浅野忠信步步深入。
不妨看作丈夫接了另一个自己到家里。
让我们跟随浅野忠信,再来一遍,或,重演一遍。
有豆友对比《岸边之旅》,确实容易联想到。
它们最大的区别是:《岸边之旅》是最熟悉的人空降在房间内;《临渊而立》是“陌生人”出现在空间的外部,透过视线蕴含着一种入内的趋势。
注意到这个空间,幽深、秘密、存在敞开的切口;线条结构硬朗,物理构成。
第二次出现这样的情境:
同样的幽深、秘密、存在敞开的切口。
区别在于,此时即将进入的是浅野忠信与筒井真理子两个人,进入的场所线条结构自然,不断发出声音的河流、鸟以及苍翠的林莽将空间修饰成了环境,某种意义上的“生理”构成。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必知的。
在两次之间发生了什么。
浅野忠信一分为二:表层的欲望(身体-色欲为首、才干、特征)牵引,内层的丈夫的理想情态。
我始终认为色欲这一层非常重要,亦是深田晃司别于其他“幽冥影像”作者之处。
基于共同目标,其余演员表演思路也非常一致。
以一个自来熟的身体示人。
表层即是色气满满的相遇情节。
内层是,他“以为”自己是丈夫。
特别的,时刻处于光明之中的男人。
(噗)
吃饭非常快,吃完后自主洗碗。
表层是极富活力的身体展露。
内层是,不现实的丈夫形象,或,为暴力存在提供基础。
饭后紧接的场面,浅野忠信已经更深入了一些。
(他初次的工作形态露面,靠近大门入口处。
)
很多年前、小时候、学过一点,天才。
依旧是表层添加魅力值与内层的丈夫臆想的叠加。
善良,优秀的品质。
浅野忠信自外向内一点一点、近乎打卡式地解锁一家三口的住宅的区块(图例未展示完全)。
并且呈现了诸多优点。
此时...但是家宅还是太理性了,需要切换一个场所。
筒井真理子顺势提出野游(回收文章开头对比图)。
至此非常顺利。
一个孔武俊朗的闯入者,一个相对孱弱瘦小的丈夫和一个美丽的妇人。
如果这是一部AV巨制的前戏,旋即在树林里展开一场大战,也是合理的。
但这终究不是AV(却惊人地拥有了AV的特质——AV是最能调动知觉的影像,在期待的必然中前进),当然也不必然...反复地确认失效后,他们选择了拥抱,然后走出深林。
古馆宽治的暴力现身男人没有放弃,“征服”、“权力”、“骄傲”等词汇占据了大脑。
色欲延续。
美好的品质消失了。
推搡。
(过程穿插古馆宽治的日常,默许,或者说操纵着。
)
再度,扩大动作幅度。
(在两段推搡间加入了荒诞性喜剧般的街景。
)无法在筒井真理子身上得到满足,于是将暴力宣泄在筱川桃音身上。
红,当然是红,鲜秾的红。
古馆宽治的真身第三幕启依旧是色欲的延续。
因代表热量的浅野忠信退场,填充了道具和表演细节。
搓肥皂。
洗净某些东西/充当润滑剂。
声音,手势。
完美的道具。
(AV般)蠢得可爱的情节:人物单独接触,笨拙、尴尬又浅含某种暗示的对话,接近,关系“升温”。
等同于前文提到的浅野忠信裸身见筒井真理子及浅野忠信开灯睡觉的片段。
同时,又是肥皂。
筒井真理子的眼神,游走在正洗手的太贺的身体上。
抽纸,第二个道具。
刚刚太贺掉落了一些颜色,筒井真理子拿纸去擦。
此刻真光加奈在哀嚎,疯狂地抽纸,试图擦去/抹净什么。
骇人的形象定格。
无所谓是否病状的必然结果,一切都是深田晃司的导向——AV中最简单粗暴、直接可以展开剧情/控制的模式:时间停止器。
而古馆宽治的真身在哪里?
依旧是一首一尾串起第三幕(真是一部“工整”的电影...)。
并且都是以喜剧的形态,接入悲悯的心态。
极度讽刺。
玩得很开心。
后来我们得知,另一名玩家是追查浅野忠信的侦探。
落水时的阳光。
救起时已日落。
拙劣的救人历程。
用巴掌想拍醒筒井真理子,还真拍醒了。
浅野忠信是古馆宽治的“旧身”,因冲动或操纵失控而犯下罪恶不得不弃用,而太贺作为名义上浅野忠信的儿子/浅野忠信的替代品(替浅野忠信接下了一个巴掌),成为了古馆宽治的“新身”(“新身”依旧在去吸引、接近着母女二人;同样的,筒井真理子提出质疑,古馆宽治主张将“新身”留下来——AGAIN?),所以他选择先救太贺。
一个缺憾,最后一镜应是真广佳奈的主观视角的。
8 ) 原罪意识与家庭,对片子做点精神分析
看这片我总是在想,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是防人之心的缺失吗,是被忽视的人性之恶吗这很像小时候我们听到的童话故事一只披着白羊皮的大灰狼,吃掉小羊羔的寓言故事而此片中,也有这么一个闯入的他者他身穿白色整洁的衬衫,像个虔诚的基督徒似的真诚忏悔,有一双弹风琴的温厚的手却豹变如恶魔可八坂并不只是单纯的大灰狼,我们很难相信影片前半部分的形象全是伪造人们总说恶人一开始就是恶人,就应该被丟到大牢里关几年就好了但正如福柯说的那样,监狱往往并不能教会人向善,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惩罚的规训,规训的惩罚它最能教会人的,莫过于对习得权力的潜规则八坂这个人物无疑从中得到了莫大的教益他出狱后露出天使的脸庞接近人们,却行了恶魔之事但问题是谁饲养了恶魔?
背叛朋友的利雄吗?
对婚姻不忠的章江吗?
如果你能从每个人身上都发现一点点原罪,或许电影就达到目的了达到了欺瞒的目的仔细想想,利雄真的有罪吗?
八坂没有招供朋友是他自己的选择章江有罪吗?
章江拒绝了八坂和萤的受害也是没有必然关联的章江和利雄的原罪意识是电影隐隐透露着的,也是两个人主动承担起来的八坂的消失和萤的受害只是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原罪意识,而掩盖了家庭不和的根源他们通过“八坂”建立起了自己的主体性,并通过“萤”维持住了一种真正的夫妻关系而其实无论是八坂还是萤,本质上都是他们原罪主体意识的在场而这种假象的崩塌始于“八坂”的再现当他们真的可能将要见到八坂时,他们反而无法面对自己了无法承受自己内心真正的罪恶——欲望对于利雄而言是丈夫的尊严,对于章江而言则是性欲的释放对于“萤”的凝视正是为了规避这个欲望的真相“萤”在片中成了一个彻底的物,没有自己的思想沦为了一个极致的象征这个象征对他们进行征召,以逃离主体性的真相而八坂的可能出现让他们越来越逼近这个真相,从而瓦解掉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失去现在的家庭但电影告诉我们事实上即使八坂不出现,这个依靠“萤”维持的家庭也是摇摇欲坠的他们从来不敢面对真实的萤,真正地重新开始生活在对萤的幻想中弥补着内心的空缺电影的最后一幕,对八年前的重返似乎证明了一个早已死去的家庭
9 ) 更像我爬到了上苍的面前
8.0山上孝司这个角色的出现其实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和那些照片或信件一样,只作为叙事工具。
可后半段呈现效果仍被低估了,它纵然只为八年前的事件提供一个原因和结果,没什么情节可言,必要性其实可以很高。
翻来覆去地追求一个结果而不得,也不止是为了再让观众思考为什么他不愿意离婚。
如果只看到了八坂草太郎的“凶恶”或铃冈利雄的“冷漠”,那便是未得其中之意。
若要先讲结论的话:童谣和红白衣的变换是在欺骗观众,八坂是不是恶人也完全不重要。
唯独对观众诚实的是两段式的幕布是视听语言分水岭,八年前几乎遍布客观镜头,八年后的镜头则极其主观。
它在暗示的只有一点,八坂是否邪恶、八年前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其实根本无需讨论,重要的是八年后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
不止是利雄,他们对自己的罪都比他人的苦要敏感得多。
哪怕本身没有罪恶的人,也以苦难为耻,山上孝司的母亲分明是受害者,还能将八坂认作孩子的父亲。
每个人态度都类似,极具尊严感。
铃冈利雄足够懦弱,那天发生了什么本不得而知,如果在内心将其合理化为蓄谋已久、轮回的报应,就会更好受一点,妻子被出轨也忍气吞声的动机同理。
而八坂既像一时怒气,也像被认作凶手的无辜者,和河边聚会那次一样,否则怎么会留在现场被利雄发现时也一直在叫着他的名字,举步维艰。
再者讲,八坂本在招待所有住处,在别处也有工作,他的留驻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利雄的决定。
影像利用了红白衣的变换欺骗观众,女儿的残疾本极大可能是偶然事件,能得出这个结论都得益于镜头语言,为我们提前辨明什么是客观事实、什么是主观视界。
非常明确的是,电影并不讨论八坂的恶,而只讨论这对夫妻的信与不信。
无可避免,二人都将这个偶然事件理解成了一种必然之恶,于是八坂的无关形象就变成了提醒他们有罪的幽灵。
关于蜘蛛的交谈是在讨论起于“欲”的原罪,蜘蛛幼虫的妈妈也不能上天堂,因为她也吃过自己的妈妈。
蜘蛛的寓言讲的是“罪”,猫与猴子的寓言则讲的是“信”。
丈夫本身是没有类似信仰的人,哪怕在饭桌上也不轻易交流,可在出现这件事之后也开始以上苍报应作理由,剪着脚趾甲平淡地论证一番,女儿遇难让他反而敞开心扉;他是猴形的人,会主动爬到母亲的肩膀。
妻子随着家庭学习了信仰,但会痛苦于丈夫的想法,要求离婚,不断用流水清洗自己;她是猫形的人,曾被叼着走来走去,可放下时自己会溜走。
有罪者能看见幽灵,而无罪者身上附着幽灵,时刻提醒他们自己做过什么。
是而夫妻无法死去,否则那位儿子和这位女儿身体所附着的意义就会消失。
那位儿子在副驾驶回头提醒过他们,杀死我也可以,女儿或许也以其他方式这样提醒过。
他们给出了上苍的指示,杀死这个幽灵也没什么不可以,全在于你们的选择。
画,相片,信件,风琴乐,日常之物都有意义所附着,它们制造声光,就展示了幽灵的存在。
保证自杀成功的方式,非要选择“水”这个贯穿全片的意象也多少有些刻意,但非常有效。
丈夫是希望留下幽灵提醒自己的,妻子却希望脱离幽灵;所以妻子入水自杀,丈夫则要远离水。
他八年前如何救起妻子掉落水中的帽子,八年后就如何救起妻子。
铃冈利雄在结尾依然在给萤实施心肺复苏的原因,就是他最开始时愿意收留八坂的原因,他希望幽灵能常在,以便提醒自己是有罪的人。
萤若去世,他又变回影片最开始坐在餐桌以左那个冷漠的人怎么办?
10 ) 《临渊而立》杂谈
这部影片我真的是很喜欢了影片前半段叙事方式仿佛流水一样,细密绵长,而在八坂露出鲜红的T恤开始,仿佛水流跌落瀑布一般,每一步都开始让我屏住呼吸。
电影的开端,正在吃早餐的一家人简直不像一家人,一个餐桌仿佛深渊一样隔开了丈夫和妻子,爸爸与女儿。
这个家庭从一开始就是疏离并破碎的。
八坂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位闯入者,入侵者,更是破坏者。
八坂首次出现的时候梳着一丝不苟的发型,穿着整洁挺拔的白衬衫和西装裤,连坐姿都是端正的,一副禁欲又自律的样子,好像这么多年的牢狱生活真的改变了他。
他自律又温柔,勤劳且大度,终于搅动了这个一潭死水一般的家庭。
这个家的女主人对他动了心,彼时的章江穿着色彩明亮的衣服,漂亮温柔且又充满生机,而这样的女人面对着一个和自己完全没有交流的丈夫,疏离地生活这时出现的那位受难忏悔的、并且和她有交流沟通和互动的“好男人”八坂,对章江来说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于是在不知不觉间,她被吸引了。
她对八坂的态度从起初的轻度排斥到后来的喜欢,她会想了解八坂的过去,想去抚慰八坂,会在深夜的时候敲开八坂的门,在他的房间里做针线活,会在她丈夫看不到的地方和八坂接吻。
而这个家的女儿显然也是更加亲近这个突然出现的,会教她弹琴、听她说话的八坂叔叔。
这个家的男主人,成了真正游离于这个家庭外的人。
“我在那个鬼地方,和一群人渣关在一起的时候,你却娶了女人,上床还生了孩子,这算怎么回事?
”“待在你家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想,为什么过这种生活的是你而不是我!
”在江边的时候,八坂的那句话究竟真的是一时的玩笑话,还是这么久以来积压着的不满、仇恨与愤怒?
章江也许还是觉得愧对丈夫的吧,于是几次拒绝了八坂的求欢。
终于在那天,看过了情侣交合的八坂走在街上,一边哼着歌,一件脱下了自己洁白的工作服,露出里面鲜红刺目的T恤。
如果说萤的红裙子代表着活力和希望,那么八坂身上的红色则是欲望,愤怒甚至仇恨吧。
在章江的极力反抗下,八坂最终没得到满足,他离开了利雄的家,而下一次出场,就是站在昏迷不醒的萤身边。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最让我欲罢不能的地方就是故事情节的留白了吧。
在很多情节上是言之未尽,留出残缺空白之处让观影人自行猜测体会。
我们无从知晓在八坂离开利雄家之后究竟做了什么,他到底是不是使得萤从此失去行动能力的罪魁祸首?
他是从一开始进入利雄就是带着愤怒和报复,还是最初的他并没有想这么多,是在相处过程中逐渐想要取代利雄?
他是早有预谋故意伤害萤?
还是在没有满足欲望后对无辜者的迁怒?
还是伤害萤不是他故意为之而只是个意外?
又或者,他只是一个不幸事件的目击者和旁观者?
毕竟当时站在萤身边的八坂没有半分复仇胜利的得意,反而一脸痛苦的神情,一个劲地喊着利雄的名字。
这些我们无从而知, 但我们知道八坂自露出红色的T恤之后,就暴露了自己的欲望。
利雄和妻子对着脑损伤且完全瘫痪的女儿,度过了八年时光,直到孝司的到来。
在这八年的岁月里,章江逐渐有了极为严重的洁癖,她的衣服也变成了黯淡深沉的颜色,她剪去了长发,身上长了赘肉,她的身上透出了压抑和近乎绝望。
利雄反而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他一直固执的寻找着八坂的踪迹,在章江想要放弃的时候也紧抓着不肯松手。
而孝司的出现,再次搅动了这一家人的生活。
这个男孩循着母亲的遗物摸索着来到了利雄家的。
他第一次在影片中出现的时候,是在晨曦下骑着单车,风吹过他的身旁,阳光洒在他的身上。
他背着一个红色的双肩包,这里的红色大约代表着青春和活力吧。
在他第一次提起八坂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
“这个孩子不会是接替他的父亲,继续来折磨这家人的吧?
”但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孩子真的是对八坂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吧,他大约只是想要抓到他那未曾见过面的父亲的一点模糊影子,才来到了利雄家。
所以他敢说出八坂的名字,问起八坂的事迹,敢安心做工即使利雄手里拿着工具站在他身后。
其实利雄站在他背后沉默地看着他工作的那段镜头,我一直看的胆战心惊,生怕下一秒利雄就会举起手中的工具,狠狠地砸在孝司的后脑,就像他以为的八坂对他女儿所做的事情似的。
还好,他并没有。
利雄对孝司做的,实际上也不过是在询问了一番关于八坂和孝司母子两个之间的事情之后,突然打了孝司一个很重很重的耳光。
那时的孝司还不明白为什么会挨这一巴掌,于是抬头一脸茫然地看着利雄。
其实关于孝司的身世,也是电影中的留白。
我们对于孝司身世的了解,仅仅来自于他自己的叙述。
十八年来,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
前面十年八坂在坐牢,后面八年八坂人间蒸发。
可八坂真的是他的父亲吗?
八坂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没有家人,家人全部死掉了,那孝司和他的母亲算什么?
八坂和利雄相识那么多年,彼此知根知底,像八坂说的,“连利雄喜欢的菊花是什么形状都知道”,他们甚至其实杀过人,可为什么利雄却完全不知道孝司和他母亲的存在?
八坂说过自己有在给受害者家属写信,可关于“信件”这个话题再次被提及,却是八坂给孝司母亲的信。
孝司说他的母亲却几乎没有向他提及父亲,他的父母亲也没有结婚,他的姓氏也和八坂无关。
尽管他的母亲一直有和八坂通信,可他却说,“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吧!
”为什么母亲不向他提起父亲呢?
为什么父亲不曾来见他们一面呢?
为什么母亲其实知道八坂的去向却不来找八坂呢?
为什么八坂作为父亲或许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呢?
更何况,他曾说过自己的母亲像章江一样对灰尘恐惧,那么是否是因为,他的母亲也曾是受害者呢?
关于母亲深爱父亲,也只是孝司自己的猜测吧,毕竟那句“八坂不肯供出自己的同伴”真的是母亲对父亲的欣赏吗?
还是说,这句话是带着怨恨的抱怨呢?
毕竟他的母亲可不怎么向他提及过八坂呀!
他真的是八坂的儿子吗?
八坂十八年前杀人坐牢,他十八年前出生。
是否有可能,“八坂是我的父亲”这件事一直都是孝司的误解呢?
是否有可能他其实是死者的遗腹子呢?
不然为什么时间如此巧合,为什么八坂不去找他们母子?
或者说,在杀死了受害者之后,八坂强迫他的母亲与自己发生关系,这才有了孝司的呢?
所以母亲对他一直很严苛,因为虽然是自己的孩子,却也是仇人的儿子呀。
于是他的母亲才会像章江一样有严重洁癖,所以自尊心极重,因为不管是上述哪种猜测,对他的母亲来说都是极为痛苦的事。
电影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对孝司的身世始终存有疑问,但也只停留在猜测阶段而已,我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的想法,而也是因为无法证实,所以才有无限可能,愈发让我着迷。
还有一处留白是关于八坂的去向,八年来仿佛人间蒸发,半点踪迹都没有留下。
一个人如何能消失的如此彻底呢?
章江一直有看到八坂的幻觉,这是因为过于憎恨和自责,还是说,其实早在八年前,章江就杀死了八坂复仇呢?
所以她劝说丈夫寻找八坂,她一直洗手是觉得自己的手上沾满鲜血。
可这似乎又有她对孝司所说的那句“我们当着八坂的面杀死你”冲突了。
无论如何,八坂的去向始终成迷。
我对孝司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台词是他在听到章江说要杀死他之后所说的,那时他已经知道了八坂的所作所为,于是这个男孩一脸平静地说:“无所谓,如果你们杀掉我也无所谓。
如果能让你们释怀,我死掉也无所谓。
”明明八坂的罪孽与他无关,这个男孩依旧愿意偿还父亲的罪孽。
孝司和萤,大约是这部电影里最为无辜的两个人了吧。
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局真的压抑。
父辈三人都背负罪孽,八坂杀人,利雄是逃脱制裁的从犯,母亲是不忠的,爱上了魔鬼的妻子。
利雄没有掐死受害者,却相当于是给凶手递刀子的人。
他同时也是导致八坂伤害萤的最根本的因素。
“我没有供出你,我一个人认罪,我在坐牢的时候,你有妻有子,凭什么?
”因为害怕被抖出真相而允许魔鬼进出自己的家,接触自己的妻女。
甚至在八坂伤害了自己的女儿之后,他把将此认为是“对自己的惩罚”,从而得到心灵上的宽慰——“我当年协助杀人,我逃避法律制裁,可我遭到报应了,我的女儿成了这副模样。
”可是他却未曾想过,自己的女儿又何其无辜?
为什么报应要报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他能一脸平静无澜的说出自己曾经协助杀人,能轻易的问妻子,“当年你和八坂搞在一起了吧。
”他早就知道,甚至默许了妻子的出轨。
这个男人,何其可怕?
他和八坂,很难说到底谁才是真的的魔鬼,或者说,两者皆是。
章江那时候也终于能明白十八年前在法庭上抽自己耳光的受害者家属的心情了吧。
绝望压抑,却无可奈何,自己的一生都被毁了,可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在这个故事里,孝司和萤完全区别于背负着罪孽的父辈。
他们代表的应该是纯真的无罪者。
如果非要说出他们的过错,那最多也只能说萤错在亲近八坂,贵错在说出了自己了解的事实。
但这些其实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过错,更不是罪孽。
然而无罪者却受了有罪的父母的报应。
萤的一生都毁在了八年前的那天,从此她被困在了自己的身体里,不能动也不能发出声音。
我相信萤是有自我意识的,于是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煎熬着折磨。
最终断送在了那条清澈湍急的河里。
而孝司的心脏也在十八岁的那年停止了跳动,他最终还是为八坂的罪孽付出了性命的代价。
最后四个人躺在河边,像极了八年前在河边躺着拍照的场景,只是这次的四人是两具冰冷的躯壳和两个从此生活再也没有光芒的行尸走肉。
在最后的这个结局里,无罪的子辈失去了生命,却也是一种解脱吧,就像利雄在幻觉看到在水中游出水面的萤,死亡对他们来说也许也是摆脱了父辈的罪孽和枷锁。
而利雄和章江夫妻二人则会背负着罪孽继续活着。
此后,对他们来说,人间即是地狱,他们从此就在地狱中行走,每一次呼吸都是痛苦和煎熬。。。。。。
我其实挺喜欢孝司这个角色的,抛开父辈的恩怨情仇,孝司只是个很普通的,甚至有时候有点怂怂的男孩他会悉心照顾自己病重的母亲,他喜欢画画,他对别人始终报有善意,他认真工作和学习,他愿意为了自己的父亲赎罪,即使他是个彻底的无辜者。
在这部真的飚演技电影里,太贺没有丝毫拖后腿,我认为他真的把孝司演绎的很好。
当他谈论起自己病重的母亲时,那掺杂着无奈却故作轻松的笑也好,那垂下来遮住眼睛的眼睑也好,还有沉浸在回忆时那些细微的神情变化,以及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之后的慌乱,我真的觉得很真实自然。
在章江说到要当着八坂的面杀掉他来复仇的时候,孝司的眼里却只有平静,那段台词我真的印象深刻,甚至因此变得非常喜欢孝司这个角色。
孝司这句台词就该这么提现吧,平静地接受,不是不反抗,而是愿意背负起父亲的罪孽,愿意为这家人都的不幸赎罪。
孝司其实是个温柔的孩子吧,父亲做了恶,狠狠地伤害了别人,他亲眼目睹了这个家庭的灾难,于是他甘心用自己的性命向这家人赎罪。
真是个傻孩子。
这样的傻孩子内心还是纯净的吧。
若有来世,孝司可千万要降生在一户好人家,有爱他的父母,然后幸福地长大啊。
千万千万不要再背负不属于自己的父辈的罪孽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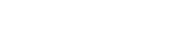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日本电影总是喜欢来这种,不把一些观众想知道的内容说出来,而是让人无尽的猜想各种。
故事淡出屎。浅野忠信的线还可以挖一挖。
都说这部特别好,我看得坐立难安。
猩红衬衫诡异微笑的浅野忠信,真是比恐怖片还恐怖片。
中规中矩 并不出彩
后半部分连故事都没了。
这几部,和《摇晃》的观照和对罪与愧疚的处理像(包括吊桥和河景),和《跨越栅栏》的配乐手法像。主题是如何过渡/平息内心中的罪。凡人对道德的理解,刽子手和审判者形象(八坂)的着陆。太长,不喜欢,说教明显。
结合身边人与事,我最大感触是“你真的无从得知你的丈夫到底隐瞒了怎样的过去”。替女主骂脏话。
浅野其实只是个是个隐喻吧?丈夫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妻子有难以启齿的出轨。。。但无法面对早晚崩溃!
就这个名字挺好,整整比《小风琴》好了一颗星。
竟然没有标记……
拍出了绝望感,但是并没有那么深刻
比起<怒>这才是怒。母亲的两难困境挺堪玩味,接纳浅野的性要求是违逆教义的通奸之罪,拒绝意味着浅野之怒会在女儿身上索取酬偿,无论作何选择都难脱罪疚。浅野的悖论是:我如此正确,以我之正确去行使处决权却犯下深重罪孽,我讲义气信公正,得到却是这个世界的怀疑和拒绝。索性我勃然大怒,一罪到底。
台版译名临渊而栗,宗教设定似乎没有展开。
刻意笨、糙的打光,稳定的中景缓慢的节奏,无配乐。形式的用力主要在剧本和细节的堆砌上,这个罪与罚背景拜访者模式的故事有十足文学性,但跟小说改编电影不同的是,它更仰仗镜头的叙述能力,是作者电影的一个小证据。另外所有人物之间的闭环因冷漠的气质隔绝了《海角七号》一类的直楞煽情,结尾太绝望
太欧了
2016.3
浅野忠信以干净利落的白衬衫和鲜艳夺目的红衬衫意念式地出现又消失,象征着意外和罪孽。而他的面目却又温柔而成熟,意外往往就是这样,平常、荒诞、模糊不清。7.5。
太贺小哥演技不错
日本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