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剧情介绍
此条目为国内上映合集条目,上下集条目分别为: 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http://movie.douban/subject/10450409/ 赛德克·巴莱(下)彩虹桥 http://movie.douban/subject/6393127/ 在险恶的日据时代,赛德克族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信仰,男人须服劳役不得狩猎、女人帮佣不能编织彩衣,骁勇善战的英雄莫那鲁道(林庆台 Ching-tai Lin 饰),见证三十年来的压迫统治。因一场误会种下日警和赛德克族的紧张关係,自此族人便活在恐遭日警报复的阴霾中,忍辱负重的莫那鲁道在深思后,虽知将面临灭族危机,但他明白唯有挺身为民族尊严反击,才能成为真正的赛德克人,于是决心带领族人循着祖灵之训示,夺回属于他们的猎场……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天地之间不朽的园丁承诺盛唐妖异志狗与剪刀的正确用法婚后事通往火星推奴波澜万丈Muv-LuvAlternative柔美的细胞小将第二季临床爱情教学!最爱你家道王媛媛他们只属于我的女神信使死亡寿司共助2:国际神弃之地特种神枪手安妮卡第一季刺客2小锅盖离婚死亡修女变身舞后长风万里芳心谋杀案东方
《赛德克·巴莱》长篇影评
1 ) 生命的条件
这两天在youtube上看完了关于整部电影拍摄过程的一个纪录片,未尽之路。
然后又翻了一点豆瓣上的长短影评,终于还是觉得忍不住,好像不说两句心里话,就正事也干不下去了一样。
很多人说这个片子就是在渲染“抗日”的英勇。
其实“抗日”属于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框架下的概念,这个片子和“抗日”不那么相关。
倘若导演就是想讲“抗日”,他实在没必要写铁木瓦里斯和“味方蕃”的事情——这英勇抗击日军入侵的“少数民族”里面怎么还出了那么多“内奸”呢?
如果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来看这个事儿,铁木瓦里斯就完全属于内奸了。
(sigh,还不能叫“汉奸”。。。
=,=)但是片子里完全不是这么描述铁木瓦里斯和道泽群的。
倘若铁木只不过是想借日本人之手报私仇,他不会在看到雾社妇孺集体上吊以后那么痛苦,对日军喊着说不干了,也不会在和儿子讨论彩虹桥的时候显得那么内疚。
他儿子问他说,我们现在和莫那打,是不是将来死后在彩虹桥另外一端相见,就和解了,相亲相爱了?
他听不下去了,只好叫儿子赶快睡觉。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当时也体会到,日军用的那些手段,和赛德克崇尚的那种公开、不为私仇且面向和解的“出草”,是两回事。
让他痛苦的不是要去砍杀邻近的族人,因为从他们的视角出发,那完全可以不算自己的“族人”。
让他痛苦的是这个手段。
用我们平日里的话来说,就是“这事情这么做着就变味了”。
编导基本上是从赛德克的角度在描述这件事情,而不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讲故事。
所以铁木瓦里斯和味方蕃的事情以及细节就非常重要。
有兴趣的人可以比较一下维基和百度对雾社事件的叙述。
百度完全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所以几乎就没有讲到味方蕃的事情,只在“第二次雾社事件”里略略提及。
而维基对道泽群协助日军的来龙去脉是有很多分析的。
据说内地上映的版本把这些都当成影响故事主线的枝蔓给删掉了。
但这些是不能删的,本来是维基,一删就变成百度了。
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我看到很多人在说,这个片子是以“中立”的视角来描述殖民史,因为片子里提到很多日本人帮赛德克建学校、邮局的事情,还找了个长得挺帅的人去演一个愿意“理解”赛德克文化的日本警察——小岛。
在我看来这个也有点误解,这个片子其实一点都不“中立”,它没有试图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来讲一个故事(日本人、汉人、赛德克),它自始至终就是站在赛德克的立场上在叙述。
所谓的邮局和学校,并不是为了让叙述看起来更加“中立客观”,而是反衬莫纳那些人的痛苦——即使有了学校、邮局这些东西,也没办法缓解我们的痛苦。
其实影片的上半部分“太阳旗”通篇都在讲这个痛苦,以及痛苦的缘由。
经济上被克扣工资,不能去打猎。
被日本人随意打骂,社会地位低下,不受尊重。
脸上不能纹面,没有赛德克的图腾,结婚的时候请人家喝杯酒竟然还被推到一盆牛血里面去了。
没有人因为被文明人统治而感到幸福,相反大家都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莫那的原话)。
所以明知前面就是死路一条也要揭竿而起。
有些人说,导演把战争的场面拍得那么血腥,把那些砍杀妇孺的赛德克都描写得像英雄一样,最后就为了脸上刺点儿青,用命来换图腾,这种价值观不正确。
但我更愿意反过来想这个问题。
导演是在用“死亡的惨烈”来反述“生命的条件”:一个人活着,尤其是还有点decent的人活着,需要有基本的尊重,对于未来的预期(死后不被祖灵遗弃也算“预期”的一种吧),以及对于生活的信仰。
“信仰”这个词可能太大,但我在这里就是指一套比较基本的对于生活的看法:我这么活着,做着这些事情,和这些人产生这样的关系,是有价值的。
一个人要活着,不是说你给他一点福利,把他养起来,他就活着了。
对某些个人来说可能可以,但是“人群”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不能指望说,我只要给某一个人群一些福利,他们就OK了。
而这个恰恰就是现在的人经常要忘记的事情。
我们得明白,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并且在大多数时间并不需要花上很大的代价去维护某一种信仰的人来说,我们并没有立场去指责历史上被逼上绝路的一群人在反抗的时候太过激烈啊。
我对自己能够喜欢上这种满眼杀戮、血溅屏幕的电影,也稍微感到有点吃惊。
但它确实让你觉得活着很不容易,而且其实挺好。
相爱或者死亡啊~
2 ) 考究史實,從霧社事件遺族的觀點來說史
有自称是人类学专家的人说赛德克巴莱「没有相当的可靠史料与口述历史支持」,这样的说法是没做功课且乱批评。
赛德克巴莱是电影,电影不是学术研究,因此有一定比例的戏剧效果。
它珍贵的地方在于尽可能从赛德克人的文化信仰观点来说史,而不是以汉人,日本人的角度强压在他们身上,跳脱枯燥的叙史方式,拉近大众与历史的距离, 赛德克族的郭明正老师是赛德克巴莱的文化总顾问,研究雾社事件二十年,搜集大量史料,探勘遗址,亲访部落耆老,并推动赛德克族正名运动,使其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族名,负责剧本翻译&族语教学,全程跟拍,他没点头,过不了关。
伊婉贝林本身是赛德克族,长期研究部落历史,同样参与剧本&歌词润饰,也担任文化顾问。
饰演莫那鲁道父亲的曾秋胜老师父亲也是遗族,他的伯公、父亲都曾参与事件,是电影中巴万等少年队成员雏型,搜集很多口述资料,娴熟于赛德克族的传统文化。
邱若龙老师研究雾社事件三十年,在1997年拍摄雾社事件纪录片时,年轻的魏德圣导演自愿无酬参予,亲身采访许多当时还在世的遗族或亲身参予过事件的族人。
03年魏导拍出短片后帮忙募款的许多学者专家都是民族学者或研究员,有些本身也是原住民或赛德克族。
电影的录音师汤湘竹自己也是雾社遗族纪录片「余生」的导演。
是以上这些人,让几十年来噤若寒蝉的遗族,有了微弱的发声机会,从赛德克族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雾社事前的前因后果,有谁比他们担任文化顾问或编剧导演,来的更有份量?
电影正式上映前导演带着上下两集到南投县雾社乡,播放给雾社事件的遗族看,当中很多年迈的老人都留到最后没离开,他们很感动,他们说虽然某些史实被更动,但这是电影,可以看的出来很用心很认真,也感谢导演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这些人从当初的质疑到现在认同电影。
可是,这个出言批评”自称”人类学者是否先了解过电影制作背景,他会比以上这些人更清楚雾社事件是什么吗?
这几位随便哪个人都是投入二三十年的心力研究这段历史,甚至本身就是遗族,难道,只有此人的数据才是正史,赛德克人自己讲的都不算?
这个批评的人又为赛德克族做过什么?
为雾社事件遗族付出过什么?
查询这个批评之人的数据,有很多论文著述没错,但没有任何一篇跟雾社事件或赛德克族有关,关于原住民的部份也只限于大方向的研究,他所说的话,难道比上述这些担任电影文化顾问的分量都重?
魏德圣导演没有回避电影改编更动部分真相这件事,请电影的文化总顾问郭明正老师针对电影中不符合史实的部份出书说明,并且以更详尽的篇幅解说赛德克族的文化信仰,以补足电影不足的部份,是电影的系列书之一,名为「真相巴莱」。
电影一开始第一幕就以黑底白字告诉观众,这是「改编自雾社事件」。
<改编>是什么意思?
电影不是纪录片,观众也没有耐心看五六七八个小时巨细靡遗的细节,电影有其戏剧效果,需要更动一些细节,但大方向是不变的,如果想看纪录片,何必看电影,根本是走错地方。
这样的评论实在莫名其妙。
「改编雾社事件」本来就不是百分百完全一样。
真要讲史实,去看纪录片,这部电影还有甚么好看?
真要讲史实,那何必来看电影?
我不知道选择看这种通俗电影的人,想从里面考究哪门子的史实?
真的很厉害就应该在二十年前趁着赛德克耆老都还在的时候,赶快去做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真的很在乎就应该针对政府的原住民政策提出针贬,对偏远地区的原住民有更多关怀认同,不是更好?
批评的人搞错重点。
任何研究,任何电影,都不是完美无缺,都有其限制,作业疏失,时间压力,财力限制,数据误差等。
电影不完美,有瑕疵,可以批评,但请先做功课,请先找好相关资料,不是看娱乐版或凭空臆测就妄下断言,不是套上似是而非的理论,写论文做研究不该是先搜集好所有资料再来火力全开吗?
拿自己看似文明的学术身分来进行野蛮粗暴的批评,怎么连最基本的正确性就大错特错站不注脚?
说电影没有足够史料左证?
郭明正,依婉贝林,邓湘扬,邱若龙的研究都不正经 不被认可?
亲访遗族的口述都不算?
自己才最厉害最权威?
这种人,当然不用指望他看懂电影,以这种心态看历史,能懂多少个中真滋味?
正如台大戏剧系教授纪蔚然在之前评"海角七号"时所说的怪现象:「出现检讨异音本为好事一桩,然而目前听到的大都属卖弄聪明,乍看之下,这些评论拉大格局,见人所不见,从本片的基本命题上釜底抽薪;殊不知,评者眼光如豆,以点论面,以伪学术语调讨论。
若无时不刻戴着意识型态的有色眼镜,或以文化警察自居,秉持「取缔的」「去浪漫」的心态走进电影院,不如在家读论文。
」 虽然电影资金匮乏,从开拍到结束都是借钱借到快崩溃,但是,导演&幕后的庞大的顾问群尽力做到讲究细节,那些我们所看到的雕琢出来的考究与细节,是由多少人,累积了多少年的资历,十年炼一剑,因此我们能在赛德克巴莱里看到了这样的功力。
现在雾社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遗迹留存,要无中生有有多难?
邱若龙老师参考很多旧照片,以前还有好几栋石板屋还在,不少是他亲身拍摄的。
电影中年马关条约交割时,日本横滨丸上10几种军种的制服都都全部作出来,戏电影中只出现几秒钟,大可不做,也没人知道,但是幕后团队做了。
实地搭设的马赫坡部落中,半穴式家屋中的柱子都是一根一根先熏过再搭建,美术设计的苦心只为让这些柱子看起来有"岁月的痕迹"....,像是真的有人住过一般,只为做出老物品的质感,何必浪费这种时间,随便用油漆涂一涂观众也不会注意到?
以上只是规模庞大的制作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在三百个幕前幕后演职员中,这样的苦心和用心,处处可见。
有些部份需要有戏剧效果,或配合剧情而做更改,但是史实的大方向是正确即可,而且,电影最吸引人之处是抽离了单纯说故事,加入核心的精神信仰,很多人根本不懂,拿着史料来掐着导演的脖子。
这世界上有哪部电影,那部史诗片能够完全遵照史实,而史实又是根据哪些证据?
很多我们以为的「正确版历史」出自胜利者之手,出自史家一人之观点,又有何真凭实据说是"史实"?
很多受欢迎的历史剧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想问这些批评的人,这是看戏的重点吗?
如果他要从这种娱乐通俗的戏剧中,拿放大镜来寻找 “史实”,真的是太可笑。
有哪部电影哪出戏或哪本小说,敢说完全照着史书?
真的如史书般枯燥,观众看得下去吗?
所以,不用看金庸,二月河,高阳,也不用看康熙帝国,雍正王朝,大秦帝国…建议把电视机砸了,小说都烧了,这样,比较符合这种 “讲究史实”的人的风骨吧。
不管虚构或真有其人并非最为重要,那是剧本当中的线头支线,要引出来的是莫那鲁道和赛德克族人,在这样的时局中的精神,作为,无奈,不堪。
甚或,莫那鲁道更是个幌子,想投射的是人性的纠结挣扎,谁是文明谁是野蛮,重新建立价值观,认识原住民的文化历史,观众透由电影懂得尊重,谅解,包容…….这才是重点。
看电影来求百分百史实??
真的是搞错方向。
3 ) 信仰引导我们前行
魏导说,五个小时去爬一千米的山,和一个小时去爬山是完全不同的。
我赞同,但是这次能在国内的影院里看这样一部主旨明确、情绪饱满的电影真的非常痛快!
国内的院线从来不缺妇联这样的爆米花电影,是的,很好看,但是我们知道还会有2、3,总之是奥特曼打小怪兽。
但是我们呢?
我们的肉身经历这一程,不会有续集,不会有第二种选择,不会有两种版本的结局。
首映之后,一个观众问“会不会有续集”,大家都笑了,导演很无奈,“所有人都死光了,没有续集”,那一刻,我为身边的同胞汗颜。
肉体的延续,灵魂的自由,哪一个更重要?
我想现今大多数人都会和某个族长一样选择苟且的活着延续命脉,或者像警察说的,再熬20年,那时我们就不再有差异。
我们一直被教育,好死不如赖活着,被教育要好好活着,想一下,是活的越来越像早晚高峰地铁站里那一张张疲惫而麻木的面孔?
还是活出我自己的颜色?
梦想是什么?
是否正在一步步接近?
是否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信仰引导我执着前行,即便荆棘占满道路,即便各种声音忙着为我出谋划策。
很开心的是能在影院看这样一部充满梦想的电影,不只是在滂沱历史中曾经呐喊过的梦想,更是现在有人执着去发掘、重塑,最终重现梦想的过程。
期待有更多有意义、有意思的电影在院线出现,期待更好的观众。
4 )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
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
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
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
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
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
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
“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
”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
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
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
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
”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
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
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
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
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
“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
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
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
“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
”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
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
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
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
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
“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
”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
“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
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
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
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
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
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
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
“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
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
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
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
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
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
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
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
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
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
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
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
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
5 )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赛德克•巴莱》
11月26日,当刘嘉玲、陈国富和侯孝贤在台上念出“赛德克•巴莱”几个字的时候,守候在新闻中心里的台湾记者们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
在此之前,金马奖已经把最佳导演、影帝和影后三个最重要的奖项全都拱手送给了代表香港来参赛的《桃姐》,如果连最佳剧情片也旁落的话,那几乎就是宣告了本年度所谓“中兴”的台湾电影只不过是局限于本土的一场自娱自乐式的狂欢。
好在这个假设的情况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赛德克•巴莱》如愿得到了金马最后的嘉奖,也在质疑声中为台湾电影“翻滚”的2011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颁奖礼结束后,我给魏德圣的助手打电话,她第一句话就问,你看过完整版吗?
没有。
那你一定要看下在台湾上映的版本,跟之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的完全不一样。
毁誉参半是否真是因为删剪过多的缘故?
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离开台北前的最后一晚,我特意跑去101旁边的影城买了2张《赛德克•巴莱》的票,从21点40分一直看到凌晨3点多。
这绝对是一次不同凡响的观影体验,算不上美妙,但极度震撼。
从电影院走出来,游荡在台北之夜空荡荡的大街上,我脑海里被三个字填充的满满:不简单。
魏德圣太不简单了!
虽然电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导演的获奖感言所说的,他做的还不够好,比如特效太假,情节拖沓,但题材和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
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赛德克•巴莱》的观众都或多或少会想去了解一下“雾社事件”这段历史,而这恰恰也是这部电影存在的最大意义。
发现“南部”:台湾本土化意识的觉醒很多人把《赛德克•巴莱》的成绩归功于台湾观众的本土情怀,但据我所知,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台湾同胞对“雾社事件”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简单介绍。
却不想在魏德圣的推波助澜之下竟引发了台湾人“全民自修”这段历史的热潮,诚品书店里的畅销书专柜上,有关“雾社事件”的各种书籍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等待着接踵而至的买家。
重新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无疑是为缺乏历史感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虽然有关“雾社事件”的书写、论述和研究从战后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文学作品,但电影作为最受大众关注的媒介,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作品的总和。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集全岛的力量支持这部多灾多难的影片?
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字幕上,“天使•巴莱”的名单里会有包括周杰伦、言承旭在内的那么多台湾人(“天使•巴莱”名单里的人都赞助过这部电影的拍摄)。
事实上,经历过灭族危机的赛德克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支,直到2008年4月23日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人数也仅有数千而已。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在“外省人”的统治下,原住民若非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即已成为边缘人。
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长期被“外省人”所占据,也使得外省文化即对大陆的文化想象成为正统,甚至在历史课本上也较少涉及台湾本岛的情况。
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十几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不是身在台北心系着神州。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老一代的移民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便开始了自觉的聚焦台湾本岛的文化。
《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完全以赛德克语和日语对白贯穿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年轻观众日渐觉醒的本土意识和发现台湾历史的真挚愿望,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也都在计算之中。
公式化结构:反殖民斗争的野蛮骄傲电影的开头,大清朝的官员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然后带着愤恨的眼神逃离日军雄伟的舰队,台湾也由此进入了长达50年的殖民地时代。
随后,电影里的情节都变得异常熟悉,强权欺凌弱小,文明征服野蛮,枪炮战胜刀剑,铁路毁坏家园……这就和我们在诸多西部片里看到的场景如出一辙,只不过印第安人变得了赛德克——同样都手持着弓箭呼啸在山林之间。
甚至要把《赛德克•巴莱》说成是一部台湾土著版的《阿凡达》也不为过,虽然没有强大的特效技术做后盾,但在两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抗争意识都如出一辙。
你还可以列举出太多雷同的故事来拼出《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公式,比如《斯巴达300勇士》(300赛德克人对抗装备精良的几千日军)+《勇敢的心》(莫那•鲁道领导族人奔向自由)+《断头谷》(赛德克人好砍敌人头颅以标功绩的风俗),大抵是因为世界文明的进程只有时间的先后,而过程本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赛德克•巴莱》并无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胜在对台湾原住民风俗的尽情展现,它一方面激发了台湾观众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岛外观众的猎奇心理。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和上述种种好莱坞大片不同的是,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峙中,《赛德克•巴莱》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也令观众无所适从。
文明固然可贵,但在卑躬屈膝的文明面前,野蛮的骄傲也足以让人尊敬。
冷酷:后殖民视域下“中立”视角《赛德克•巴莱》不是要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莫那•鲁道塑造成一个华莱士般的英雄人物,让他高呼着“freedom”浴血厮杀,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
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
他说,“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打我的。
”就是这么“正当”的理由,血洗了无辜的生命。
杀戮总是能将人变成魔鬼,哪怕他还只是个孩子。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
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
小岛的参战,也是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而爆发的怨恨,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
而即便是带有种族主义的军警也并非多么的十恶不赦,反而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
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
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
在《南京!
南京!
》中,陆川曾试图用一个中立的视角来反思战争,而《赛德克•巴莱》虽然也是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
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
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
如果说《南京!
南京!
》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与无奈。
纠结:身份认同的危机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
从何而来?
要到何处去?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
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
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样,这种危机在当下的台湾也同样存在。
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当有根的老一辈逐渐卸任,无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二选一的尴尬。
而台湾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身份认同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台湾日渐式微,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持续升高,1992年为17.6%,2010年达到52.4%。
“去中趋台”是当下的一个趋势,虽然未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
饰演该角色的徐诣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并最终夺奖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
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名叫达奇斯。
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
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
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被日本同事嘲笑“两个番人生不出日本孩子”,学历最高收入却比日本同行低一个档次。
一张原住民的的脸,就断绝了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已经忍了二十年,本还想再忍二十年。
最终,赛德克人的起义,他们被迫卷入其中。
面对莫那•鲁道的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
他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并最终先后自杀。
花冈一郎选择了用日本武士的方式——切腹——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但他使用的工具却是原住民的弯刀。
他死前和弟弟的对话是赛德克语,但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却用日语说了句“谢谢”。
弟弟的话更叫人难忘: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哪也别去了。
而我猜,这也正是台湾人最真实的想法!
6 ) 以野蛮人的骄傲
虽然《赛德克·巴莱》在岛内的票房收入没能达到赢利点,但是,魏德圣拍摄了前所未有的台湾大片。
要谈论《赛德克·巴莱》,那开篇部分必然会是不同版本的考证。
因为观看的版本不同,那也会直接影响对电影本身的评价。
就以删减版的《美国往事》和《天堂电影院》为例,其故事甚至发生了实质改变,观众很容易偏离作者意图。
《赛德克·巴莱》的第一个版本是威尼斯电影节放映的国际版(电影节版),片长150分钟,映后反馈以恶评为主。
尤其是内地记者和影评人,清一色的狂殴痛骂,此举也引发了台湾媒体的反击。
后来魏德圣解释说,这个版本不是自己剪的,它是为了赶时间参赛,吴宇森公司那边剪出来的。
正因如此,这才有了后来的第二个国际版,也就是送去美国放映和参选奥斯卡的导演剪辑版,片长155分钟,简称国际通行版。
毫无疑问,第二个国际版比第一个要强,也肯定比台湾的上、下两集连映要强(276分钟)。
可能考虑到影片实在太长,无异于“膀胱大作战”,香港上映时,下集被删减到109分钟,大大缩减了长度,无奈依然评价反响不佳。
到了引进内地时,那肯定是在第二个国际版的基础上删改。
所以,你没看错,没发行DVD之前,光是参加影展和上映,《赛德克·巴莱》一共就有五个版本……显然,魏德圣拿了吴宇森的钱,又拿了很多人的钱。
他“不得不”沿用《赤壁》的上下集发行模式,另一边还舍不得删减素材,好以此向世人证明:你们看到了吧,我把钱都用上去了,没有任何私吞。
简而言之,如果《赛德克·巴莱》仍旧沿用上下集的模式,我会觉得上集不错,有新意更有锐气,其格局比《海角七号》要大出太多,耗费导演不少心力。
但是评价一旦落到下集,那当真是又臭又长,硬伤无数,只想快进。
我们常说,大片不只是大投资、大导演,更不是搬来一堆巨星,那就能拱出个好来。
对《赛德克·巴莱》而言,大片并不一定就要276分钟的片长。
恰恰相反,一百五十分钟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从投资级别来说,《赛德克·巴莱》耗资巨大,动工了台湾大批的技术人员,质量完成得也还不错,岛内震动。
只是对着一堆素材不知道如何下手,这点上,魏德圣多少有点优柔寡断,没有快刀斩乱麻的利索劲。
影片的最大优点是独树一帜,它以原住民的历史题材入手,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在香港是没有历史条件和天然环境。
在选题和执行上,魏德圣完成得很出色。
他对雾社事件的关注,对身份认同的反思,这些都促成了《赛德克·巴莱》的拍摄。
影片的拍摄成功,又给华语导演的励志故事添上一笔。
对很多台湾人来说,《赛德克·巴莱》的意义就是把历史课本上的一行字,变成了一部有血有肉还有“人头”的历史大片,算得上精彩好看。
对华语观众来说,他们终于看到了气质不大一样的大片,技术出色、演员朴实,内容激荡,更能引起一定的反思。
然而,《赛德克·巴莱》也有它的莫大缺陷,那就是主要人物太过平板,缺乏内心戏。
尤其是赛德克族一方,从强势、隐忍到反抗,其中是有明显的挣扎过程,不过这些都太表面化了,流于形式。
到了后面的战斗场面,那就是千篇一律,毫无悬念可言。
不过解释起原因可能也很简单,这些非职业演员能改造身体,更能顽强坚持,但是他们难以驾驭住情感,控制自如。
试想,如果没有一郎、二郎这般角色的存在,从剧本上去描画,《赛德克·巴莱》将失去真正的灵魂,同时缺乏讨论的意义。
在他们身上,电影呈现了身份认同的痛苦,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属何方,自知万劫不复,惟有以死谢罪。
再不然到日本一方,无论是小岛源治还是派遣军司令,他们除了在血樱花下感慨一番,似乎功能无多。
但即便有明显的瑕疵不是,《赛德克·巴莱》依然展示了惊人的信息容量。
在还原历史和文化习俗的决心、对信仰和神话传说的表现、适当提拔和升华的英雄主义、穿越林间的运动长镜头、近乎外语片的观赏语境……这些东西不仅在过去一年极为罕见,即便放到过去十年的华语电影里,《赛德克·巴莱》依然值得肯定。
有趣的地方还在于,《赛德克·巴莱》完全没有对野蛮和文明的话题指手画脚,它赞美原住民的勇气和信仰,又表现了他们残杀日军妇孺的血腥场面;它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上抛出了武士精神的同源之说,对原住民的行为产生了敬佩之心。
它重现了上世纪30年代的雾社事件,展示猎场和家园之争,让斑驳的岩石壁画从模糊到清晰——一场关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战。
无论选择抗争还是选择自刎,赛德克族都抱有野蛮人的骄傲,这恐怕也是最能打动魏德圣的地方。
【北青报】
7 ) (转)賽德克巴萊觀後感/林開世.
賽德克巴萊觀後感/林開世.by Nien-Ru Tsai on Tuesday, October 11, 2011 at 4:26pm ·.林開世(臺灣大學人類系助理教授)原文刊載於《人類學視界》第七期當觀看一部有關台灣原住民的電影成為全民運動時,唸人類學的人似乎必須對這部電影發表意見。
連我80多歲的母親都到戲院排隊進場時,我就知道,我再也無法逃避一件難以逃避的任務:對一部很難讓我喜歡的電影,發表一段不會太影響別人觀看慾望的評論。
首先,讓我說幾句好話,賽德克巴萊作為一部具有娛樂目的的電影來說,顯然在很多方面,比起魏德聖導演前一部作品《海角七號》,是有相當程度的進步。
本片節奏明快,剪接俐落,比起海角煽情的拖泥帶水,敘事方式的確更顯順暢。
龐大的成本與卡司的加強,讓導演更有餘裕具體呈現其視覺構想,更讓這部電影的整體成果有了國片少有的自信成穩。
更重要的是,本片大量使用業餘原住民演員,並以賽德克語為主要對白語言,挑戰漢族中心主義的視野,也具有尊重在地族群主體的意義。
單就這些成就來說,這部電影已經穩穩的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的里程碑。
而就一個電影迷來說,觀看過程中,我主要的抱怨還是導演那種高中文藝青年般的傾向,炫耀又重複使用「象徵性」的符號,例如血紅的櫻花與通往祖靈的彩虹橋,彷彿擔心觀眾看不懂他所營造的「深層意涵」。
先不去深究這些象徵是否合適用來表現賽德克人對於死亡與獵頭的意像,全片持續的賣弄已經造成觀賞上的困擾。
然而作為一個人類學者,面對賽德克巴萊所敘述的故事與支撐起這這個故事背後的歷史觀,比起觀看時的不快,更加的造成我的不安。
我們可以從戲院中,以年輕族群為主的觀眾,對於這個電影的正面甚至愉悅的反應,以及在報紙與網路所掀起的一連串有關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的討論等等的現象中可以發現,這部電影成功運用多種「再現」歷史的手法,一方面肯定社會目前存在的多元文化主義教條,另一方面,製造一種彷彿可以允許不同觀點爭辨的詮釋深度,讓所謂「霧社事件」可以繼續安全的,安置為台灣歷史編撰學的一部分。
但若是這部電影已然肯定多元文化的價值,又允許不同的觀點爭辯,那麼,這種將「事件」歷史化的工作為何會令我感到不安呢?
首先我想從電影如何鋪陳與解釋「殺戮」切入。
賽德克巴萊的第一部,一直到運動大會當日高潮的殺戮場景之前,主要的敘事主題就是要交待與解釋:為何莫那魯道會帶領賽德克族人展開一場毫無勝算,而且血腥殘忍的反抗?
電影把重點放在兩個面向:日本殖民政權的剝削與歧視;以及賽德克族人渴望尊嚴的面對與連接其祖靈,並保衛他們的傳統生活型態。
有趣的是,在沒有相當的可靠史料與口述歷史支持下,電影在此顯然運用了大量想像力與臆測,讓莫那魯道內心掙扎的過程,成為支撐故事的主要戲劇張力。
因此,我們看到的觀眾反應,基本上是圍繞著:這部電影是否對霧社的殺戮事件提供滿意的答案。
有人認為,無論反抗異族壓迫的名義有多崇高,從人道的角色來說,殺害婦女稚童的行為就不對的。
有人則認為,反抗外來政權,維護文化尊嚴,是值得我們付出生命的代價。
不過編導想要傳遞的訊息,還頗為「在地性」的:他們認為這整件事件,從賽德克人的觀點來說,就是延續祖先們出草的傳統。
要活得像個男人,殺戮是必須的,獵頭也是必然的。
可以預期的,這樣的詮釋方式會引導出一些相當複雜的議題。
對具有眾多長期互相敵對部落的賽德克人來說,莫那魯道的重要性與英雄地位,本來就是充滿爭議。
如果他只代表了某些敵對一方的部落,無法說服與代表全部的賽德克,那這個事件可以被視為是件反殖民抗爭嗎?而就詢問「文化」內涵方面來思考,議題將更為尖銳。
如果出草獵頭其他族群代表了賽德克族的核心文化價值,那這種違背最基本的人權的制度,我們可以接受嗎?
然而,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這些看來冠冕堂皇的爭辯,其實是建立在某種合理與安全的歷史觀之上。
我們只是利用一個異文化的傳奇,來製造出一個可供消費的道德想像空間。
殺戮與毀滅如何被呈現,在歷史書寫上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如何能用文字或影像去再現那些陰暗與恐怖的存在,卻又不會把它們正常化與美感化,成為曾經走過那些黑暗幽谷的作者與倖存者來說,努力尋求的救贖。
然而,那些嘗試用寫實的手法來做忠實的歷史重建者,發現他們往往無法解釋那顆鬼魅般的黑暗之心為何存在?
而那些採取脈絡化與心理動機解釋的人,卻發現他們細緻的掌握主觀與客觀面相解釋的結果,卻是一步步持續的在合理化那些邪惡與殘暴的行為。
我們賦予了過去一個個解釋的框架,將那些難以理解的事件,轉變為可以被評價的的歷史的同時,我們建構了一個排除非「合理」的世界觀,也讓我們距離事實越來越遠。
人類學在面臨異文化時,也往往面臨這類呈現知識的難題,人類學家用自己的語言嘗試去作跨文化翻譯,我們借助各種既有的理論框架,來幫忙我們尋找了解他人文化實踐中的關鍵秩序。
然而,如果有所謂「他者文化」存在,那最難描述與解釋的,正恰恰是那些不符合我們解釋框架的思考與行動的關係形式;這顯得人類學家在意的「在地文化」與「土著觀點」的框框只是某種笨拙的理解方式與論述。
我們常常忘了:理解與翻譯的別人的文化現象是建立在各種物質與權力關係之上,「他者」並不該是因為滿足了我們的多元文化價值,才能得到認可。
在這種以一種合理且具有心理深度的歷史觀來敘說一起異族的傳奇,就是我面臨賽德克巴萊時,產生不安的來源。
整部電影的敘事是以一種全知的歷史框架,嘗試重建編導心目中所謂的「在地」觀點,來合理化一場基本上可能是無法也不需要被合理化的殺戮。
它採取的策略是將這群人塑造為異文化的他者,並將他們的出草文化浪漫與美感化成為即將消失的鄉愁,最後再讓莫那魯道與他的族人的行動轉化為延續賽德克祖靈的血祭。
於是,「霧社事件」一方面在殖民史與大社會的脈絡中得到了一個位置,另一方面將原本被視為「野蠻」的蕃人,轉變為傳統文化的守衛者。
這樣的詮釋固然比起過去那種反抗異族壓迫的國族論述高明,但這也更進一步把莫那魯道變成可以被定位的歷史人物,讓他的意識與行動成為我們以為的對錯與合理性爭辯的題材;更讓賽德克文化成為現代化所生產出來的那種永遠不可能彌補的鄉愁。
於是,獵首與殺戮成為可以被理解、同情甚至讚佩的行為,文化與祖靈成為神聖、遙遠但又抽象的象徵。
傳奇與圍繞著傳奇的騷動與危險,沉淪為那些有關族群、尊嚴、人道與認同的道德論述。
我不是主張因為難以呈現,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去拍攝有關原住民事蹟的電影,相反的,我們更可積極的讓發生的事件被呈現出來。
但當我們面對謎團、疏離、矛盾與空白時,應當保持尊重的距離,抗拒深度詮釋的慾望,讓觀眾嘗試用自己的想像與困惑填補那些裂縫。
面對賽德克族人難以撫平的過去,我們不需要再添一個馴化版本的詮釋。
面對這群活在不同世界觀與不同的歷史感的賽德克人,過去留給我們的就是一些破碎的記載,以及太多不可靠的追憶。
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這群人的內心世界,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人有沒有內心世界,即便有,所謂的內心世界是否可以以對談與反思的方式來陳述。
但是,面對詮釋的困難時,我們有必要用各種想當然爾的祖靈觀,族群意識,人性尊嚴,父子親情,來虛擬化出一位我們可以接受的英雄嗎為什麼,我們不能尊重那些我們所不知道的,那些無法被合理化的,那些不能被再現的;而讓自以為是的重建真實與歷史評價,留給我們自己。
8 ) 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
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近期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将“雾社事件”那段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烈历史,以一种“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推到了观众眼前。
电影在台湾大卖,在大陆虽然票房不佳,但同样收获了丰盛的口碑。
导演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与台湾相比,大陆遗留的历史创伤更多,这恐怕也正是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但当微博上出现大量拿“高砂义勇队”来否定《赛德克·巴莱》的言论时,我们知道,这种疗伤还很遥远,因为我们的历史观,还相当陈旧和落后。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
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
”——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
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
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
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
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
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
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
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
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
”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
“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
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
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
《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
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
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
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
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
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
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
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详细]原住民高聪义却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
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
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
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
请收我为军夫。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在当时。
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
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
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
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
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
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
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
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
朝鲜人金在渊说:“(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
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
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
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
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
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
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
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
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
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
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
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
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
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
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
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
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
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
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
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
”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
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
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
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绝不装逼”[详细]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9 ) 重建彩虹橋
賽德克巴萊上映了,只是上集聽說三天票房就破了一億新台幣。
一張票算它250塊吧,那就是四十萬人看過了。
這簡直是打選戰的規格。
偶像、金主、悲情、拜票、假想敵、造勢晚會,一應俱全。
和它的本土主義號召相映成趣,這恰恰是一部十分「非我族類」的電影。
電影裏不論原住民還是日本人,他們的信仰、價值觀跟人生態度,都和我大相逕庭,和我所認識的大多數台灣人(受儒道佛三教薰陶)也大不相同。
為什麼這麼異文化的事物,這麼充斥仇殺跟血腥的故事,能在三天之內吸引四十萬台灣人走進電影院裏?
真是想不透。
只是廣告行銷的魔力使然?
還是在這個社會溫良恭儉讓的表層底下果真潛藏著一條由累世無明的仇恨、殺伐與血腥匯合成的伏流,這部電影只是喚醒了或點燃了觀眾的集體潛意識,教他們經歷一場集體出草與血祭?
就在這種時刻,特別使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有其長處。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伯夷說「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也」,這兩句話就是我給這部電影的最終評價,也希望所有看這電影的人別忘了這兩句話。
在我看來,原住民的勇士氣概、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都太偏頗狹隘。
可以理解,但不能同情,更不可能服膺。
本片成本據聞是七億台幣,如果七億成本只為了回應武士道精神的感召,那真是可惜了。
另外有幾點心得。
第一,有人批評此片對日本人的惡行揭露太少,相形之下賽德克人過於野蠻。
我認為導演本來就不覺得日本人壞,抗暴不是他的主題。
事實上日本人的理蕃政策必有其長處,否則難以解釋為什麼原住民在二戰期間踴躍從軍、大規模同化。
第二,有人批評此片對賽德克人的祖靈信仰、出草習俗交代得太過簡略空泛(例如如何血祭祖靈完全沒演,若回不去祖靈天家會去哪裏也沒說明)。
我也認為如此。
原因何在?
我認為和導演的基督教信仰有關。
交代得太清楚,便有所謂偶像崇拜、祭祀邪神而違反教義之嫌。
導演是虔誠的基督徒(長老會),男主角更是。
男主角在現實生活中根本就是長老教會的牧師,他不可能只為了一齣戲違背自己的神職。
上網一查,今年8月15日,台灣長老教會總會曾發文勸諭:「最近,原住民部落為因應鄉公所舉辦的傳統祭典,許多地方開始興起祖靈崇拜,並築壇拜祖靈。
…若沒有經福音轉化和信仰連結,實在令人憂心。
」在電影裏,別說祭壇了,任何祭祀儀式一概闕如。
第三,長老教會希望原住民的信仰能夠「轉化」、「連結」上基督教。
我認為導演正是這麼做了。
他拿「彩虹橋」來表徵賽德克人的信仰,應非偶然。
因為在《舊約‧創世紀》裏,彩虹正是人神和解的象徵,彩虹的一頭是人間世,另一頭是永生。
另外,電影裏又說祖靈住在天家,天家有肥美的獵場,「天家」的基督教色彩比「天堂」還濃厚。
「彩虹橋」和「天家」都是把原住民信仰往基督教連結、轉化的中介。
第四,莫那魯道的仇恨根源為何?
確有殺父之仇,但導演淡化處理(頗難理解)。
顯無奪妻之恨(女性都是配角)。
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因素比重很低,阿凡達式的生態主義貢獻不大(獵場二字雖然常掛口邊,但比較夢幻,缺乏一個阿凡達式的地景聖物發揮錨定作用)。
我認為:電影文本給的答案仍然是宗教信仰(死後必須回到祖靈的天家),而且是頗為原教旨主義的宗教觀(不獵人頭、保護不了父祖的獵場,成不了真正的(男)人,死後就必定上不了天家)。
有太多熱心的觀眾一再告誡我們:片中原住民的殺戮行為不帶仇恨甚至還可化解仇恨。
這奇突的教諭,正是依循一種宗教思維。
非常可能,這部預算與票房雙破紀錄的台灣電影,其實是部帶有基督教色彩的宗教電影。
本片的票房持續累積,僅管媒體已逐漸(率先)退燒,但電影埋下的種子已札根發芽,不知道明年春天來時會結成怎樣的果實?
不知道經歷了這場集體出草與血祭的年輕觀眾,你們的彩虹橋究竟在哪裏?
-◎2011年10月20日後記:本片下集9月30日上映,據說下集殺得更兇更久,有人看了連做三天惡夢。
如此少兒不宜,三個週末下來台北票房仍然破億,真不簡單,難為了那些行銷高手。
我還沒看下集,等二輪吧。
隨緣吧。
據說下集結束時畫面上真出現了一條特效不甚靈光的七彩虹橋,一眾原民武士的靈魂真在觀眾見證之下載歌載舞遊行上橋走向天家消失不見。
有人刻薄它說像是二十年前台灣鄉土神怪連續劇常見的八仙過海戲碼。
究竟七億台幣搭起的彩虹橋真面目如何,還請親眼看過的網友不吝賜教。
純粹猜測:我猜導演非要「殺很大」、非弄條彩虹橋不可,也是緣於信仰之故。
殺戮是衛道殉道,過橋是淨罪救贖,哪樣也不能少。
◎2015年7月26日後記:讀B. Riftin (李福清)教授《從神話到鬼話》,得知1930年德國學者Otto Scheerer到北台灣山區采錄的泰雅族神話,其中就有一個「死人靈魂過橋上天堂」的神話,被認為是台灣原住民族神話受到基督教影響有文獻可考的最早例子。
《賽德克‧巴萊》所講述的霧社事件恰好也發生於1930年。
但是關於霧社事件自身的史料,畢竟不存在能夠證明莫那‧魯道乃是出于相同或近似的神話信仰而自殺的證據。
因此,本片的彩虹橋,仍然只宜看作是後來的台灣人根據自身的基督教信仰(如導演魏德聖)或者受到基督教影響的神話信仰(如泰雅族牧師林慶台)而回溯建構的歷史想像。
由于原住民族自身沒有文字歷史,給人乘間抵隙的機會太多,這就讓本片提供的歷史想像獲得了遠超出聊備一說的通俗力量。
10 ) 台湾人拍给台湾人的电影
这是一步台湾人拍给台湾人看的电影,各地票房口碑都不太好,只有在台湾票房口碑双收。
导演还是借由历史唤醒台湾人的民族独立精神,不要被大陆“殖民”了之后忘了根,不要做夹在两岸里的懦弱之人,到反抗的时候不要做台湾人的“叛徒”。
唉,已经被无数夹带私货的台湾导演给弄怕了,之前的还愿,还有电视剧里的争议地图,只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最喜欢做一个优秀的作品里面夹带私货,然后看我们大陆人不停的吹,之前的盛况大家应该也已经见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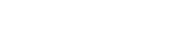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搞不懂主旨是啥,我俗气了
但從電影的角度來說,無可挑剔。但是就事件來說,我有種種的“這不科學“的呐喊!!!
很早便知道了这部电影,也看过海角七号,不管是土著人还是台湾人,都是中国人,每次看到打小日本都忒兴奋,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底蕴,听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
野蛮与文明纠葛不清。但男人亲手杀妻子和婴儿,女人亲手把孩子摔下悬崖…恕我理解无能。
不自由,毋宁死。
文化入侵远比领土入侵可怕得多,一个民族可以输去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如果你的文明是让人背躬鞠膝,那我就带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木卫二说得对,《赛德克·巴莱》的意义就是把历史课本上的一行字,变成了一部有血有肉还有“人头”的历史大片。十二年磨一剑,魏德圣真的不简单
不必看。大陆版的合集减缩到153分钟,能剩下什么?起承转合遭人诟病那也是必然。
经典中的经典,十年来中国最优秀的电影
这名字我一直记不住,今天cctv6下午播看了一下。无底洞的投资,宏大的题材不好驾驭,很多小的地方拍的还是很感染的,没有预期的好
没有觉得那么好呢。。 a little too pure for me。。。 歌很好
才看完一天就忘的差不多了。。完全没有什么感动落泪,但应该说还是比大陆的什么历史巨片要强,能把一个少数民族这么有血有肉的完整呈现出来。但实在太冗长拖沓,导演舍不得剪片
根本不懂人家的骄傲的人就当战争大片来看你说你怎么看的懂!
对内容不置评,但拍得很棒!!
对全片视人命如粪土的价值观实在接受不能。两星已经是我能打的极限高分了。另,前半部这么拖还把人物刻画得这么弱,着实不易啊……
那些类似《天空之城》的配乐在实际观影过程中没有起到太强烘托,看的过程竟然比预期的要平淡。
对小日本和台湾,永远道不清说不明的赶脚
看过这部电影,了解到了雾社事件,场面宏大,确实很有震撼力,配乐是一大亮点,但毕竟是讲台湾原住民的故事,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偏,也没有如想象中那么精彩,可能电影中人物缺少更多的内心描写,但确实是一部好电影!
因为魏德胜童养媳般的民族主义,我还偏就不看赛德克巴莱了。自始至终,没喜欢过他的一丝一毫。说真话,他也就是个绿营的冯小刚。哭天喊地的说,你们看的不哭,有没血性啊有没道德感啊,不哭不是人。是台湾人就转!
好像主题并不突出,但至少说明了人是要有尊严的活下去
没去电影院看好可惜 看了影评和背景之后这部电影的形象瞬间上升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