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的需求》剧情介绍
来自法国的旅行者伊丽丝在韩国担任法语家庭教师赚取生活费。语言的隔阂让她和学生之问的交流充满错位感,东亚文化中不善于思考和表达内心情感的“痼疾"又与渴望交流与开放的心态交织在一起,触发了只有异国旅行者才能感受到的特殊孤独与惆怅。被誉为韩国作者电影第一人的导演洪常秀继《在异 国》《克莱尔的相机》之后与法国国宝级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再度合作,用极简主义的拍摄手法呈现细致入微的人际关系精妙互动,斩获2024年第7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银熊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我叫郝聪明一息尚存绝对达令刘海戏金蟾海魂驯龙高手2我的朋友很少OAD复仇木偶人寻找刘三姐代号47春晖常轨脱离发现女巫第二季坏家伙四重星永远的铭记龙门笑传2热血同行天空念恩桥幸福迷途少年侯德榜求精心切境·界拉字至上第六季天国与地狱吸血家族汉密尔顿时尚王执法者侍女
《旅行者的需求》长篇影评
1 ) 旅行者的需求(24年8月一刷;24年12月二刷笔记)
(一)与一个亚洲艺术片导演三度合作,对于佩尔阿姨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经历。
前两部《在异国》(2012),《克莱尔的相机》(2017)。
第三部《旅行者的需求》,洪常秀2024年推出的两部长片中的前一部,片长90分钟,是他制片生涯中第31部长片。
(二)于佩尔对洪常秀深深佩服。
尽管受邀主演《旅行者的需求》时她对角色一无所知(当然,洪片的主演们,总是有此感觉),但谈到与洪的合作,她说,“这让我非常兴奋。
我只能希望永远这样下去。
”“他让我深刻反思电影的意义,洪常秀的拍摄方法让我记住了电影可以如此庞大,也可以如此渺小。
他几乎是一个人在工作,却能同时保持电影的力量和规模。
这令人着迷。
”(三)三次当中,于佩尔总是以旅行者形象示人。
即便第二次是在法国本土拍的,她依然是一个溜达在戛纳海边和小巷的拿着一次成相相机的旅行者。
再一次地,有于佩尔的影片将跨语言文化交流中的尴尬和不可理解,作为考察对象。
《克莱尔的相机》中,于佩尔身上有股神秘莫测的气质,异于电影中其他角色,有点像幽灵一样。
到《旅行者的需求》里,这一气质甚至更强化了。
尤其是,这次她是游荡在异国,在陌生的语言符号包裹的地方,她更加有势单力孤之感,仿佛随时会被生存困难吞没(虽然电影里与她交流的韩国人,多以积极热情的笑容面对她,体现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崇拜和谄媚态度),但她身上的幽灵气质承袭自上部(第一部《在异国》里还不具备这种气质,充满肉身感)。
我感觉洪常秀是把于佩尔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韩国人的“民族性”。
当然,也借此表现出洪一贯的主题:真相在语言之外,人类操持着语言,永远无法真正互相理解。
以及,人永恒的孤独。
从对世界的看法上,洪是个不折不扣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从语言中寻求真理之不可能),而从方法论上,他是个德勒兹主义者(在差异与重复中折射出真相)。
(四)虽然洪常秀的电影毫无疑问地是反英雄的,他的影片中充斥着自带矛盾性的普通人,即便偶尔有角色在语言中突然迸发出惊人的思想火花(此时我便感到,那是洪常秀的一个分身),他也立马又表现出愚蠢、庸常的一面。
但于佩尔是个例外。
幽灵是没有这些缺点的。
因为他不在人间。
《旅行者的需求》中,我能感到于佩尔和上一部《我们的一天》中老诗人奇周峯有惊人一致之处,都在浑浊的人间清醒地提出“要活得真诚”。
毫无疑问此时他们都是洪的分身。
但奇周峯还藏身于人间,所以免除不了身上的油腻。
而于佩尔是不知从哪里来的,突然介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虽然常识上推知,她来自法国,但她表现得如游魂,甚至身份的不确定引起人的怀疑)。
这次,与上两部中旅行者形象不太一样的是,她离荧幕上的韩国人更近,她走进他们的家庭,她甚至和一个年轻的韩国人发展忘年恋的关系。
但她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韩国人自身。
她微妙地影响和改变着一些人。
将他们从生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人”。
但她也面对她的挑战,和她的孤独考验。
(五)我反复提及洪常秀影片中某些富有智慧特质的人是洪的分身,好像他是个无比自恋的导演一样。
我没这个意思。
洪不是为了讲故事或出于自恋而拍电影的。
他是个拍电影的哲学家。
他有他的思想要表达。
他大多时候通过影像本身展示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把电影设置为结构主义的棱镜所折射出的思想光辉),而不是依靠某个有力量的形象,用台词说出他的思想(用语言说出来的,不是真理)。
但极偶尔情况下,也有几个角色说出了他内心的想法。
有时,是正面地说出的,有时,甚至是反讽式的,说出这些话的人,本身就不可信。
在我看来,他拍电影,就是要以影像的方式,留下一沓他的哲学思考笔记。
(六)《旅行者的需求》里在异国旅行和逗留的于佩尔,通过教韩国人法语来谋生——这是她的年轻韩国爱人告诉她的方法。
但影片前面大半时间是她与两位韩国学生接触的情景,50分钟过后,爱人才出现,更晚的时段,年轻爱人在接受母亲“拷问”的时候,才交代他们是如何认识的,这时我们才得知,她原来是在一处公园,过着流浪汉式的生活——这更加强化了她的幽灵特质,一个在异国的流浪的幽灵。
去故事化的影片讲述里,对主角身份信息的碎片式揭示,以这种倒金字塔式结构展开,这种“倒行”的手法,真是老法师的魔法手指。
刚开始,我们只感觉到她的某种特质,到后来,我们才寻找到她的路径。
(七)影片在黑幕上出完标题后,直接将观众扔在一个宽敞明亮的韩国居室里。
一个年轻漂亮的韩国女孩跟于佩尔在探讨学法语的事。
她看起来简单快活,积极配合学习。
但又感觉得出,她有某些对学习的畏惧态度。
聊了一会学习后,她起身去钢琴边弹起了钢琴。
仿佛这是她更放松更能找回信心的时刻。
但于佩尔站在她身后听了一会后,悄悄走出门到阳台上去,身体语言透露出她内心的某种不融入。
也许是出于交流上的困难,教学意志的难以抵达。
在阳台上,二人聊起弹钢琴的事。
于佩尔发起了一系列追问。
“你在弹钢琴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女孩说,感到快乐。
“然后呢?
”然后是,感到旋律很美。
“你觉得你弹得好吗?
”我弹得还行,没出什么错。
我对自己有一点满意。
“有一点满意?
是满意呢还是不满意?
”面对追问,女孩哑然,陷入沉思。
一种被欢乐掩饰的忧伤,浮现在脸庞。
“你弹钢琴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优秀?
”对,是的,我想展示自己的优秀。
一通追问后,事物走向了反面,一些更接近真相的东西流露了出来。
我们能看到韩国人被遮蔽在焦虑、虚假的热情和快乐之后的别的情感,一种更底层的东西。
没有于佩尔这样的追问者,可能难以显示出来。
相比之下,于佩尔这样一位来自西方的人,显示出对真相本身追问和探究的好奇。
这既可说是西方文化与东亚文化的差异,也可看作洪常秀在他所置身的文化环境里体现出的个体差异。
他有点如鲁迅。
拿解剖刀在解剖他所在民族的国民根性,文化对人内心的塑造(或说遮蔽)。
洪常秀在访谈中就说过,大家仿佛活在某种共识里,对事物有相同或类似的看法,只要追问几个问题,就会发现,每个人所谓相同的理解,其实并不相同,“就像吃冰淇淋,你永远无法将你品尝到的味道真正地让他人知道”。
显然,东亚文化更大地遮蔽了人对自身真相的探究,所以,他起用于佩尔,塑造一个来自异国文化的幽灵,来映照自己所置身群体。
接下来,于佩尔和女孩到户外溜达,二人各吃着一根雪糕(洪似乎在用这个表演细节,来互文自己曾在访谈中用冰淇淋打过的比方),在一块纪念碑石前,女孩谈起自己的父亲,此时台词显示出她出身富裕,父亲很爱她,也是个慷慨的社会事业捐赠者,她因为父亲的离去而伤心落泪。
于佩尔摸了摸她头发以示爱怜,拿出卡片写下了此时能表达女孩内心的几句话语,然后将法语读法用她的便携式磁带录音机录到磁带里,把磁带交给女孩,让她反复诵读。
通过这种方式,她让学习者先从自己最有感触的话语,来接触法语这门语言。
这是她独创的学习方法。
女孩感激地,支付了她这一次的授课费,她们约好下周再见,女孩与她在公园里告别。
这既是语言教学,明明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理治疗。
通过一系列访问,令对方“明心见性”,被遮蔽的东西,真实流露出来。
被文化压抑的真实的人,得以释放。
(八)接下来两组过渡镜头,先是于佩尔在小餐馆吃了拌饭,后是她在公园里,脱鞋踩在一个小小水坑里。
似乎借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帮她恢复丧失的元气一样。
然后她来到一个富贵人家的楼下。
年轻女孩介绍的另一个客户。
李慧英和权海骁是一对富贵的夫妻,拥有自己的企业。
想学语言的是李慧英。
她与于佩尔交谈,试探。
对她自创的教学法充满了质疑。
她对这位法国女人热情有加的同时,有着明显的防范。
以及富贵人特有的一种傲慢气质。
对她来说,她不愿当小白鼠,何况还得付出金钱。
“但金钱不是器官,我不会害你的。
”于佩尔对韩国人将金钱看得很重要这一点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但有的时候,金钱跟器官一样重要。
”富贵李慧英反驳道。
交谈在客气、克制但出于不信任而有些僵的气氛中进行。
李慧英谈到自己女儿(她学过三年法语但在于佩尔面前不愿意开口讲一句),对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如今什么也不干,在家如废柴。
于佩尔说,没问题的,她这样也挺好,挺有个性的。
这种对人的无条件的接纳,让李慧英仿佛找回一点面子,她明显兴奋了一些,似乎有些喜欢这个法国女人了(尽管出发点可能更多出于东方人的“面子”需求)。
洪式的“重复”元素在此片中也是被屡试不爽的技巧。
本片分三段,每一段都出现韩国人在聊了一阵天后,拿起乐器来弹的桥段。
每一段都是先在室内聊天,后转至户外、公园。
在相似的规程上,导演让观众看戏剧发生的异同。
有时连台词都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第二段中,先是丈夫趁妻子离开的空档,拿起吉他来在外国女人面前炫耀了把(他性格柔和得多,对于佩尔有种性别立场上的宽容和好奇,一种压抑住的热情),于佩尔也趁二人的空档时间对他逗趣道,他们介绍说你是公司董事长,但我看她才是董事长。
权海骁说,对,她是这个家庭的董事长。
随后李慧英拿着马格利酒回来(于佩尔在本片中酷爱喝马格利酒),也拿起吉他来弹。
于是,几乎与第一段中她和女孩一模一样的对话,发生在她和李慧英之间。
李慧英的回答,以及回答背后的空洞感,与第一段女孩也一模一样。
她们仿佛是同一个模板刻制出来的产品,只不过年份不一样,阅历和复杂程度不一样。
她也压抑着真实内心的另一面,表现为一个坚强刚毅的女性形象,有点苛刻精明。
他们三人也在公园里游荡。
在韩国早逝的诗人尹东柱的纪念碑前,他们品读并讨论着尹东柱这个诗人及他的诗。
诗,是对生命状态和内心情感的真实展示。
但他们讨论着,敬重着(权海骁还突然对着尹东柱纪念碑跪拜),自身却过着远离诗与真实的生活。
一种凝重的生活。
这种凝重与于佩尔的轻盈形成强烈对比。
李慧英也谈起了自己的父亲,她对父亲有遗憾的情感。
但她长期以来不愿意面对。
父亲也早早地离开了她的生活。
成为内心隐痛。
在她流露出真实(脆弱)内心之际,于佩尔拿出卡片,写下了几句话,几句原本不是李慧英之口说得出来的话,作为对她心声的描绘。
于佩尔给她看卡片上的话,念了出来。
她不再表现得抗拒和质疑。
她接受。
同意将此作为学习材料。
她拿出一叠钞票交给于佩尔,感谢她,并且抱歉钞票没装在信封里(显然准备得太仓促)。
她们约好下周再见。
第一段约15分钟长度,第二段约35分钟长度,时间长度似乎与两段中两个女人的年龄长度相匹配。
我们都感觉到了文化的压制,家庭结构带来的隐形心理伤害。
感觉到韩国人和法国人活得如此不同。
活在效率、目的、戒备当中的韩国人,精神上的痛苦成为生命的底色。
而法国人活得如此轻盈,她像一个生命的旅行者,走到哪里,都睁开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世界。
告别这对夫妻后,于佩尔还经过尹东柱纪念馆前,一位韩国年轻女孩与她搭讪,讨论着这位早逝诗人的另一首小诗。
以这种方式,洪的影片将我们一次次从滞重的生活拉出来,走向诗的轻盈。
(九)第50分钟左右,于佩尔回到她的住处。
是她和一位韩国年轻人同居的寓所。
他很穷,为房租发愁。
她拿出今天的两笔收入,有1000块(20万韩元),对她和他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钱,她交给他,希望贡献出来做房租。
年轻男人是位诗人。
她告诉他一定要坚持写诗,她相信他会写出好诗。
他们在充满阳光的房间里,坐在床上,温暖的气氛笼罩着他们,明显的爱意荡漾在空气里。
他也走到电子琴旁,弹起来,她认真地听着,告诉他,要忘掉记忆里的音符,要弹出每一个音符的当下感。
她将她的人生哲学贯彻在每一事、每一细节里。
然后,他的母亲不期而至。
他想隐瞒他跟于佩尔的真实关系,但她说不要这样,她还说“我会保护你的,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母亲跟于佩尔打了个尴尬的照面,于佩尔走出房去抽烟,实际上是回避,将空间交给母子二人。
母亲看望儿子,关心儿子,仔细询问他生活的境况。
问的全是吃的喝的住的,全是物质性的关心,全然不顾儿子的精神世界。
谈到与那个可当妈的法国老女人的交往情况,母亲终于发现儿子是把她当作不一般的关系,儿子谈起她来两眼放光,谈到她的真诚,她对生活美好的态度。
当母亲得知儿子只是在公园偶遇她,就信任她跟她相处后,勃然大怒。
觉得他有可能被一个骗子忽悠而不自知,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
她拼命质问,你说她真诚,那我真诚吗?
儿子不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母亲解读出儿子的否定之意。
“我虽然不是个真诚的人,但我很努力地在爱你呀,你是我的儿子呀。
”她有些歇斯底里,儿子终于在她的咆哮中安静了下来,似乎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
“努力爱着”的母亲终于占了上风。
她去给儿子煮了好吃的,看着儿子吃,她心情好起来。
两个“母亲”,在同一个小小空间里,用约半小时时间,在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出强烈对比。
一份爱,让人感到自由呼吸,一份爱,让人窒息得要死。
第三段中的“父母”不是缺席的角色,是鲜活的存在,她带来的不是隐形的痛,是强烈的桎梏感。
(十)年轻诗人走出门来(这个年轻诗人角色,这个演员,我们在洪的前作《逃走的女人》里已见过,这是再度见到,但在此片中,他变阳光、帅气了),等着于佩尔归来。
但她迟迟未归。
事实上在他与母亲相处的漫长几小时里,她一直在附近等待,还到门口张望,但最终还是没有敲门而入。
他到附近公园寻找她。
在一个长椅上,他看到吹笛子的她(流淌在空气里的诗),但没有走近,犹豫着,擦肩而过。
他来到显然是他们常一起呆的地方,一块石头上,他在那里思考了片刻。
然后,在显然是山顶上另一块更加巨大的石头上,我们发现,于佩尔躺在那里,睡着了。
此时给了她睡着的脸部一个巨大特写。
也许是洪常秀的所有电影中唯一的、大型的人脸特写。
但我们看不清她的面孔。
她如一个睡着的幽灵。
她脑袋后,他出现了。
停顿了片刻,他喊醒她。
她醒来,他说,回家吧。
(十一)在经历了两位“母亲”的拉锯战后,我们欣喜地看到,年轻的诗人还是寻找着她,精神上的母亲,还是渴望着她跟他一起回家。
这似乎是洪常秀留给真正的“人”的一点希望。
虚无主义的洪,并不想将这世界弄得彻底黑暗。
而于佩尔,这样一位幽灵式的人物,一位生命的先知,她在此片中是轻盈的,流浪的,并且受到怀疑的。
因此她自身也充满不安全性。
这似乎正是真理在这世间的待遇。
我想起土耳其一个叫热哈·埃尔坦的导演拍的《宇宙》(2009),村庄里,来了一个流浪汉,因为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又说着饱富智慧的话语,起初,他被村庄里的人看作先知,顶礼膜拜,后来,村里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他们开始怀疑他,甚至要杀死他。
最后,他,逃离了那个村庄。
留下了一个复杂的传说。
241220
2 ) 卡片式的探讨内心与生活中的回归自我
一向常用的推镜几乎没有了,整个影片看下来就像在日常生活中过了一个多小时,毫无跳脱感。
大概导演是想告诉我们,生活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陌生与真实,半点深入内心的可能性几乎都没有。
场景由公园绿植、室内坏境、流水石头构成。
公园绿植让人放空自我,室内环境给人提供交流场所,流水石头营造一种真实日常。
电影讲了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差异,还有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距离。
个人与群体从表达内心到肢体动作都是千差万别的。
法国女子伊莉丝来韩国教语言,她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挖掘内心感受来学会新语言”的新方式来授课。
第一位年轻女学生弹钢琴,表达弹奏感受是:快乐、觉得手艺不够专业、想要炫技,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很有趣的是第二位女精英弹吉他后,说出了和年轻女学生完全一样的想法。
她们看起来都是社会中发展较好以及即将发展的人,但她们对于自己的感受却毫无新鲜的表达。
只是浮于表面,相似又普遍。
反观伊莉丝就是热衷探索内心世界,创造新的卡片教学模式,在群体中显得独特又显眼。
这大概就是导演想告诉我们的:探讨内心、找到真正的自我是多么重要。
更有趣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呈现。
女学生认为父亲捐款在石头上刻下名字很好笑、男子喜欢喝米酒妻子却从来不知道、最离谱的是母亲对儿子从头管到脚却不懂儿子喜欢什么样的人。
这一切都由一个闯入者法国女子伊莉丝来揭晓。
当问题被揭晓,也仅仅只是呈现,还是按原样继续着,毫无更新的可能性。
我们也像是生活在这样类似的原生家庭、家庭生活、以及这样的亲子关系中,明明大家朝夕相处,可我们就是说不到一块去。
最最可笑的是那个精英女人,法国女子伊莉丝离开后,她在公园小径对着丈夫笑说:“她走的真快,就像个疯子一样。
”探讨内心的人,独特风格的人,反而成了坚守普遍信条人眼里的疯子。
形式上也结合内容,展现这个被普遍充斥的真实的世界。
影片两次通过物件来暗指独特与普遍。
两次的石头来代表刻板、而利用自由而灵动的诗来体现深刻的内心与自由的灵魂。
这也是伊莉丝念诗后不自觉地感叹:“为什么要带走那么美好的诗人。
”“他为何离开那么早。
”电影人夫妇念诗需要找注解才能读出来,也很难说出对诗的感受。
倘若人连自己都不了解,又怎么会有机会走近身边人?
最妙的还有通过新的个人来区分个人的特立独行与群体的千篇一律。
导演通过法国人来韩国教语言争取旅行的费用的场景,以一个新的个体来凸显群体的相似性,一时之间便让人联想到自己,给人新的想象和决定。
另外从叙事上也是分别从与女学生、夫妻、母子进入,几乎遍及大部分的关系群像,从而引申到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人有了新的联系。
说来说去都是探讨内心的电影,我们原本以为的内心充实也在影片的揭露下显得如此匮乏与单调。
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如回味一下电影中的另一面,关于静谧宜人的绿树蓝天、悠然自得的露台闲聊、以及闲来无事的看小鱼游泳、还有自在的石头上的酣眠。
这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回归自我”。
3 ) 到底谁才是旅行者
这是一部很有趣的片子。
我觉得反应了东亚人很多有趣的小点已经和欧美人巨大的文化差异比如片中女主可能觉得自己在问一个非常开放式的问题,但结果两个不同人却做出了同样的回答。
非常对称的回答那一段不仅很好笑其实也很引发思考。
这好像是一种东亚人逃不出的框架,永远希望有教科书,哪怕没有教科书了,却又还是逃不出回答的程式。
这里面其实有组很有趣的关系是女主是来到了他们的国家,却教他们法语,对于韩国来说女主是外来者,但对于法语来说他们却是外国人。
东西方文化或许有一种无法消除的隔阂,就像要黄油结果要来了拌饭一样,就像她和男主人那段无比尴尬却又继续进行的对话一样。
同时整个片子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点就在于女主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但却是这个陌生的地方的人都在迎合着她。
接受所谓新型授课的观点,哪怕看上去像是小白鼠,愿意像西方人一样不问过去地交往,甚至于用法语读一首当地的诗歌。
这时候谁又是客人呢,谁又是那个旅行者呢?
在这个对女主来说的外国,她却能过的比当地人还悠闲,她在公园里散步,不用付房租,随便聊聊天就能挣到钱,这或许也是一种荒谬吧。
我觉得这个片子非常好地去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个很有趣的片子。
2024-6-21看
4 )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and you?
6.5也不知道为何看完后脑子里一直浮现出这段东亚式的经典问答,这面镜子的投射,好笑得很真实。
而在洪常秀高产的影像中,《旅行者的需求》又在强烈的文化对比下将当代东亚人与人沟通的本质贴上了新的标签——机械、尴尬、质疑和无意义,而本片以随处共鸣的情绪展开,似乎也多了某种“圈地自嗨”的意味。
当回答被规训,真正的情感还能表达出来吗?
这也是该片带来的第一个有趣点,东亚的内敛通常也表现在面对文化差异的同时不主动展开话题,而通过一件实际发生的事、一个明确意义的物品引出话题。
就行片中的钢琴与吉他,在无话可说的时候成为一种交流的载体,随即有了于佩尔发出的关于“感受”的问答。
毫无疑问,“感受是什么?
”、“感到疲惫的态度”、“想要进步的目的”……带来的所有回答也都像是“How are you”一样刻在脑子里的近乎麻木的情感堵塞,而转念又能在已逝人的墓碑前诉说感激,忏悔落泪,仿佛放下真实呼吸带来的隔阂与戒备,才能拥有的内心的表达。
真好笑啊,我们不难想起自己考试的日子,提前背好的答案,哪怕语法、情绪,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用疑问……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刻在脑子里的知识让人说话不再过脑子。
产生尴尬,逃避尴尬如果说第一个故事侧重个人情绪的表达限制,那么第二个故事,一家人因为于佩尔突然的到来形成了夫妻的尴尬、母女的尴尬。
通过对话不难看出入赘的男主人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的律师职业选择了为妻子打工,也不难看到女儿也早已对“才艺展示”这一项厌倦无语,交谈间不离手的米酒也没能缓解尴尬的氛围。
大笑声中微妙的氛围也伴随着“夫妻信任”这一话题戛然而止,很好的接上了男女主人吉他演奏的话题——和故事一近乎相同的一问一答。
户外墓碑的场景,男主人在跪拜中对自己放弃律师行业的feel sorry或许也是为数不多的隐晦情感,而女主人自认为清楚其中的意义。
“再喝一杯米酒吧?
”“已经足够了”。
第二个故事从打开话匣的“米酒”分享欣然展开,最后也同样由无法再分享的“米酒”尴尬结束。
有人说,东亚父母勒令子女的show off是种无法逃避的宿命,就像我们总在相互要求,相互不满中持续着尴尬的进程。
何必呢,换句话说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东亚母亲的自责,窒息永无安宁?
第三个故事的窒息感,同在大东亚的大家都可以说太熟悉了,该章节中,平时并不那么关心儿子的母亲对于儿子生活状态极度算计与盘问外,在发现家中住有“过往经历不明的年长法国女性”时大喊大叫中也是金句频出(真的非常真实压抑又好笑)。
模糊的关系界限,可以在于佩尔身上看到需要与支持,也能在男子表情语句里发现这是一种爱意的肯定。
对于母亲的癫狂,歪果仁是不理解的,文化输出到了这个程度也变成了崩溃的崩溃,不解的不解,就像暂时离开的于佩尔也只能无处可去,带上米酒随遇而安。
最后,“do you still love me as a friend”,她还是抛出了模糊的疑问,山坡上无所谓的环境与问题本身,和妈妈间的对话产生巨大反差。
旅行者的需求是什么呢?
是语言?
是感受?
是情感的依托?
文化的认同?
还是稳定的住所?
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了东亚人根深蒂固的情感与思维,比起短时间的需要与欢乐,旅行者实际带来的是不可言喻的“尴尬”与“入侵”,最后还是说回我们熟悉的感受的吧: 故作热情的礼貌、假装充实的生活、里外炫耀的交谈、以退为进的谦虚,一生都在规训中的东亚人还有真正的inside feeling吗?
5 ) 伊莉丝的等待
公园里的石碑旁,有好几种绿树,叶子都不相同。
针叶的是松树,阔叶的,也许是茶树,或者樟树,我们狭隘的知识面,并不能确定它们的名字。
“都是普通的行道树罢了。
”那些懒得辨认的人就这么说。
但是,如果你非要问:“再看看,还瞅到了什么吗?
”你坚持地问他,他才会回答:“对哦,这棵树颜色深,叶子细细的!
那棵颜色浅,叶子嫩嫩的!
嗯,它们的层次很明显。
”
我见过这样提问的人,她是《旅行者的需求》里的伊莉丝,她教韩国人学法语。
伊莉丝的教材是一叠空白小卡片,她会根据学员某刻的想法,在卡片上写一段抒情的法文,让对方念诵。
法国人和韩国人说话,用的是英语,就像此前于佩尔与洪常秀的合作。
但是,继《在异国》和《克莱尔的相机》到现在,大家的英语还是很生涩,就像用着一件不趁手的工具,挤出“开心”、“旋律”、“美丽”、“炫耀”、“不满”这些基础词汇,统统都言不及义。
伊莉丝的英文也差,但她总是问:“还有什么呢?
”所以,她的写作总是失真,她的课程也会雷同。
比如一位女生弹了钢琴,另一位叫元珠的女士弹了吉他,当被问及弹奏时的心情,这两个学生的答案一模一样,而伊莉丝写给她们的句子,也完全复制。
我们悲观地认为,伊莉丝也是个骗子,她像作家一样统一发文案,没有真正贴心的对话,英语是人们之间最生硬的地带,又或许,任何形式的沟通,都只是被妥协的中间地。
可虽然语言被阻塞,这种无法相融的中间状态,也制造着清新的空气,它让社交失效,让人们的行为变得笨拙。
于佩尔一直都是旅行者,是文化上的陌生人,《旅行者的需求》把这种身份变得更加本质:一方面,文化上的隔绝成为了伊莉丝的生计;另一方面,她在用更陌生的方式,与他人建立传统或非传统的关系,她的旅途和来意都是未知的。
同时,那些本土的演员们,她们面对伊莉丝/于佩尔,表现出的不同的紧张感,形成了人物之间的差异。
尽管伊莉丝给了她们同样的礼物,但对方各有各的局促,比如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她总是用笑声来掩饰表述的困难,还在刻有父亲名字的石碑前哭起来,于是伊莉莎拍了拍她,然后举起卡片,以诗人的姿态给她写下一段话。
元珠是这个女孩的阿姨,当她和伊莉丝对谈时,总是致力于说出标准的词汇。
她丈夫更是滑稽,他询问伊莉丝的帽子,耍弄她的圆珠笔,酒过三巡,还抱起吉他,煞有介事地拨起来,弹着哆啦咪发······这是一个介于刻板身份和出格举动之间的人。
在散步的时候,他甚至对着石碑上的诗,跪拜了下去。
对丈夫的表演,元珠女士也只能看着。
这时,伊莉丝轻轻地摆着手走过去,碰了碰石碑,再走到元珠身边问她:“看到他这样拜,你心里怎么想?
”元珠背对着镜头,手拿着一条捡来的树枝,说出自己敏锐的心声。
于是,伊莉丝为她写了一段独特的文字,一段并非印刻在石头上,而是徘徊在树枝头的文字。
而她写下来的话,总是对实际情况的增强,对方要是“有一点不满”,会被她说成“我对自己很不满”,同时加以延伸。
这到底是对真实情绪的揭示,还是基于某个词语的发散,你不得而知。
既然选择了一个脱离实际的老师,你也无从去纠正她的手法。
结果,这一张张卡片,都成了别致的礼物,是人给未来自己的礼物。
是的,洪常秀已经来到了他最简洁的阶段:如果两件事很相似,那就让它们完全一样,而其中细微的对比,却能成为人物最鲜明的特点。
环境也格外简单:一个长焦镜头里的森林和青山,檐角的天空,楼群的平面,某片对焦不清晰的树梢,或者公园里的那些石碑,它们正面和背面都刻了字句,这些画面,像手机相册里简陋的一角,但它们已足够美丽,成为最确切的舞台幕布,而对话的双方,就这么站在它前面,做当下的语法练习。
我们可以把伊莉丝献给仁国的话,送给更多学员们:“拒绝沉迷于记忆的诱惑,回答每一个音符,让它成为独立的存在。
”观众确实在抵抗记忆,我们知道,即便两个人说了重复的话,她们的状态也不同,大家都是语言和行为上的初学者。
况且,语言之间并没有高下,如果有人说:英语是更功能性的;法语是更抒情的,也最有表达力;而韩语在伊莉丝眼里,是外国人的窃窃私语。
那这只是刻板印象。
当伊莉丝把一天赚来的钱都给了仁国,对他说:“一半房租是二十万韩元,总共是五十万韩元,我想和你一起分担这笔钱。
”这就是最真诚的表达,对共同生活的成本的计算。
只是与此同时,她一定还有别的话,是用英语无法说出来的,甚至用法语也讲不出来,只能转化为笨笨的动作,和你一句我一句的“谢谢”。
另一场算账,发生在仁国与妈妈的餐桌上,伊莉丝与仁国之间有语言的距离,而妈妈与仁国长期不在一起,彼此都不算很熟悉,因此,她那些关于吃住、关于生活、关于伊莉莎到底是谁的追问,都变成了典型而错位的关心,哪怕在最熟悉的韩语中,她也找不到合适的表述。
除了这些隔着物质的关心,我们还能说什么来接近对方呢?
它们诚然是最重要的,但或许,大家还需要一门陌生的语言,它是感受力的根据,“看着好久不见的儿子,除了给他做一顿饭,我还想说什么?
”这便是伊莉丝课程的启发。
有一点很肯定,伊莉丝也是个初学者,她不只在学习英语,还在学习运用自己的肢体,还学习着与一栋房子、一块石头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她见到青草地里的小水潭,就脱了鞋子,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进去,水流没过了脚踝,她也哼起歌来。
一不留神,把鞋子掉了,她赶紧“啊”地捡起,正要去擦鞋擦脚,却还恋恋不舍地又泡了一会儿水。
这种行为,像极了一部叫做《chiikawa》的日本动画片,那部了不起的作品,每集一分钟不到,都是些小团子一样的生物,尝试着各种对它们来说很新奇的事情。
无论是《在异国》、《克莱尔的相机》,还是《旅行者的需求》,于佩尔一直在做旁若无人的事,当大家在正常地走楼梯,她却一跳一跳,拍着扶手跑上去,好像一阵微风的化身。
当她为了配合仁国躲他的妈妈,跑到一个绿色的天台上,然后走去东张西望,远远地瞧瞧他妈妈走了没有,那时她把高跟鞋防水台踩得嘎吱响,这就是人物对于动作的尝试,一些与实用性相反的尝试,只是把一双鞋子挤出声音来。
我们很珍惜于佩尔的喜剧,它们显得陌生,因为它们不导向共鸣,而是一个人的私密选择。
洪常秀理解私密的必要,正如他已经很少创造共情——至少是作为舒适区的共情——而走向了对更多可能性的学习。
所以,我们不会对电影得出相同的结论,甚至总是有相反的感受,我朋友觉得《旅行者的需求》很孤独,而且人与人的沟通有点恐怖;我则觉得恐怖不可避免,但也存在治愈。
而重要的是,孤独与治愈不会相互抵消,也不存在哪个更本真,它们共同组成了生活的层次,这就像人物关系的开放,就像伊莉丝一样,她既可以喜欢吃面包,也可以吃韩国拌饭,在那些相似的幕布前,她做着自己才知道的小事。
其实,于佩尔的来头始终都是个谜。
《在异国》是一部棕色和橙色的电影,我们会记得民宿的棕色环境,以及救生员的橙色帐篷,它和他工作服的橙色一模一样,而一次次的重新写作,更将民宿变成了一个临时住所,而她作为一个虚构人物,可以有很多种临时身份。
接着是《克莱尔的相机》,得益于她那件黄风衣,我们总觉得那是部柠檬黄的电影,她是一个拿照相机的精灵。
《旅行者的需求》是绿色的,绿胶带、深绿色的玛格丽包装纸、各种各样的树,人工的绿和自然的绿区分得很明显,因为人工的绿色非常平面,或者说,它们看起来太不自然了。
伊莉丝穿着她的绿开衫,和这些常见的绿,组成了远近前后的层次,比起知道她是谁,我们只能看到她是什么样。
她有时在圆珠笔上贴一圈苹果绿的胶带,有时在山路上走了个没影。
但最温馨的绿色,是手工的,是她和仁国的绿格子窗帘,卧室里的台灯都开着,还有盏绿莹莹的桌灯,把窗帘变得透明,变成一丛嫩芽般的浅光,他们的家,这没有来历的家,犹如发亮的春日。
但,越天真的人,越知道纯粹是最难的。
仁国不计较伊莉丝的身份,但他必须对妈妈撒谎。
而伊莉丝在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那一刻,难道不会辨析出生活与理想的差距吗?
暂时回不去的伊莉丝,她走了好大一圈,来到了一条新路上,那是块赭红色的大岩石,背靠着葱郁高山,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山顶,当她住进仁国家里之前,她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她斜靠着岩石,拍了拍它的质地,然后躺下来。
妈妈走后,仁国去找伊莉丝,从街头找到公园,在公园的小径上,他遇到了她的背影,捧着一支笛子,在吹一首不成调的曲子。
他路过她,又绕到她面前,看了看,没有上前,他还不是他,这还不是相认的时候。
因此,这场看似抽象的剪辑,就是伊莉丝的等待。
仁国也爬上了那块石头,在上面坐了好一会儿,又走向更高的山路,之前情境的杂质,正在被一个个蒙太奇所过滤。
伊莉丝在山顶出现了,太阳已经落下,她闭着眼睛正睡着,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她这么近,看到她抿着嘴唇,手上有粗粗的血管,还戴着那根与裙子配套的花手环。
一个陌生的特写,在此之前,镜头从未如此直面人物过,尤其是对没有来历的伊莉丝,她从来都不是透明的,却总能说出最清透的话。
因此,对于这个睡着了的朋友,比起询问她是谁,我们选择默默相信她。
接着,切到全景,仁国把伊莉丝拍醒,她转过头来,喊出了仁国的名字。
二人确切地认出了对方,她给他喝了一杯玛格丽,和他一起回家去,那仍然是属于友谊的家,当他们先后走过了新路,这个心愿再次被确定。
6 ) 影评|那些年对洪常秀的误解和不理解
作者:发条辰首发(带图):耐观影不知道从几何时“洪常秀”三个字成为了形容词活跃在国产文艺电影的评论区,常用作形容那些形式先锋酷爱对话的影视作品。
被说像洪常秀变成了对影片和风格的“嘉奖”,当然通常情况下这三个字也是用来阴阳影视作品的词汇。
洪导的作品也因为近几年平均一年两部的速度被冠以“洪氏vlog“的称号。
《旅行者的需求》在放映前一度被认为是金熊奖的有力竞争者,但看完大概只会劝洪常秀真别拍了…《旅行者的需求》主要讲述了伊莎贝尔·于佩尔饰演的法国女人生活在韩国但由于没有钱或手段养活自己,她被善良的房东建议去教法语。
通过这种方式,她成为了两名韩国女士的法语老师…从简介来看,洪尚秀这次似乎会致力于讲述一个真正的故事。
然而正好相反,洪常秀只是把上述文字作为影片的背景。
从第一幕就露出了陈旧的气息,影片的开始便是经典的“洪氏vlog”固定镜头开场,于佩尔与她的学员开始聊天、谈话。
姑且不去谈论对话的内容,当然洪常秀的对话内容远没有林克莱特在《都市浪人》中那样后现代主义和天马行空。
但是连最起码的让剧中的角色讲的一口正经的台词都没有,洪常秀让韩国人和法国人用塑料英语对话,这种感觉恍如隔世,一下子回到了初中英语听力的年代,原来电影真的能造梦,造的还是童年的听力噩梦…尴尬虽然是洪常秀电影中的底色也是他讨好观众的利器,但是在这部电影中塑料般的对话尴尬是目光和听力所及的真正的尴尬,场内观众的笑声也许是真的嘲笑和费解。
如果抱着期待来看一部喜剧电影,或许在这里已经足够回本了。
虽然没有幕的区分,但是洪常秀还是贴心地把影片分成四段。
在第一段把观众和电影中的角色都尴尬到后洪常秀也没有善罢甘休,接连摆出了剩下看似与第一部分形成照应的三个部分,且都与第一部分神似。
在余后的叙事中他甚至装都不装了,直接把大量的台词和人物间对话的方式照搬形成新的段落。
也许有人会为其辩解特意设计,但细想这些东西真的有必要吗?
内容形式表达几乎一样的四场戏或许是在表达社会化使人的个人感受消退,或者是异乡人如神秘幽灵般的松弛游离,又或者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本质和语言的探索…这些都有可能也都有迹可循。
但他是否知道自己真正想要表达什么?
一个半小时里他精心地设计了四场英语场景对话,没有任何的内容和形式上的输出,全凭观众的臆想和猜测,这样的电影是否是真正的cinema,倒不如真正地像《房间》这样的烂片与观众直接物理互动,而不是靠猜测的精神交互。
他的电影状态给人一种等待的观感,有可能是等待角色的下一句台词又或者是下一个尴尬的地方。
又或则他大概也在等待电影之神的降临来告诉他这一段应该这么这么拍了。
可惜他在尝试了这么多年后依然等不到这一时刻,反倒是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早已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舒适圈,多年来影像风格几乎没有变化,在他大举进军三大电影节的这几年他的作品风格从未真正迈出过自己的安全区,最多也是在技巧上下功夫(比如对近视眼友好的《在水中》)。
《旅行者的需求》就完全符合了他以往作品的特点,说好听点叫影像风格序列一致,说的不好听其实就是连续剧套路反复诈骗。
认为其无意义是真的,不理解也是真的…他是一个很“鸡贼”的导演,他展现出来的“Vlog”从来都是没头没尾的中间片段,角色间的互动对话也极具个人的目的性,他把不必要的全部剔除,让角色只讲设计好的话语。
这样虽然表面上形成一种虚假的现实主义纪实,但实际上做作的无法让人接受,尤其在这部中更是被无限放大。
消除“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般的毛边,留下做作尴尬的对白,不得不说洪常秀还是有“构思”的。
如果说该片是洪尚秀对自己无可救药的重复,那么于佩尔的表演便是一成不变中的闪亮光点。
她的这个角色非常特别,她有着异于其它人的灵活的肢体动作。
她为这部电影带来了一些生机,她在行走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轻飘飘”的奇妙感觉,她在完成某些肢体动作时(躺在石头,抽烟,戴帽子摘帽子…)极具神秘感和松弛。
在一众纸片人和尴尬人中显得格外的“可爱”,这不像是洪尚秀所能带来的力量,可能是在完全不知道人物背景和故事的情况下于佩尔阿姨自己向角色抑或者向观众传递的角色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最后只能对洪尚秀导演的作品给到一个“这很难评,我祝他成功吧。
”这样的评价,过度沉浸在自己风格和舒适区里的人是很难被拯救的,洪导好似找到了影展密码便自顾自的如法炮制宛如打游戏般的刷成就,却从未停下脚步去思索自己的表达方式。
换句话说,你永远也叫醒不了装睡的人。
7 ) i
这是一部7分电影,我依旧无比无比怀念金敏喜在时的洪尚秀,我被那种微妙、彷徨、坚韧、柔软深深打动,那些电影里的金敏喜呈现出一种内核稳定但却总在迷茫的模样,她摇摆不定,就连她的坚定也是她摇摆中的一个状态,我在那无数瞬间感受到了灵魂共鸣的强烈震颤。
在小说家的电影后,我再没从洪导的作品里看见演员金敏喜的名字,一直都在翘首以盼,这一部可以说是没有金敏喜参演后相对不那么无聊的一部,也是有着非典型洪导特征的一部。
典型洪导特征就是,谈话气氛尴尬微妙,人物间讲些不着边际的话语,永远在推销韩国的米酒。
但导演两段重叠的诙谐幽默让我想起早年间他的这时对那时错,也是很精妙的一个结构、这部电影用同样的方式,看似很无意义的重复话语结构,却让观众在无意识间自行比较,然后发笑,让东亚人跳脱出东亚人的视角框架,看到外部角度里东亚人对于语言学习的莫名其妙的痴狂。
后面男孩和于佩尔在之间的感情就很洪尚秀了。
来日可以好好分析。
这部片让我看了头皮一紧的原因是,开头的语言教学尬聊真的很像雅思口语考试现场。
8 ) 旅行者的需求
从抛出的诸多议题而言近乎一部文化批判电影,但其中又晓畅地亮明那如许珍贵的漂浮、游移、充盈着不确定性的碎片,享受白人身份便利、乃至近于招摇撞骗的Iris大啖拌饭、沉醉马格利酒、透过门缝嗅闻浓郁大酱汤味,毫无愧色地接过“课时费”,借助英译评点韩国民族诗人,表演与融入、庸俗与诗意被诡异地搅拌混合。
然而洪对片中流水的韩国人一个赛过一个真是刻薄得紧,几乎无一幸免成为叙事工艺的零件或民族性批评的靶心(除了权海骁保留了一些异样灵动)。
然而Iris的教学法,实际上也就是借助语言是否足以直入并反托心声这一疑问,如她所言也只是一个尚不得证的实验,所以一方面用貌极华美的法语即兴手写诗句保存心绪,一方面却又每每以现实的庸俗腻味失效的沟通而保留意见,那么观众也就是洪的小白鼠,第二段已借角色之口托出洪当前的一些电影观念自白,当然,这个也是要观众付钱的。
但,不妨一试呢?
这些人大约是些好心的俗客,迎赶着去面见那有些茫茫然的智者。
9 ) 我被里面的父母深深伤害了
看到第二段的时候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喜欢的洪常秀了,可能是这种语言的壁垒和完全不同的文化在短暂言语中的展示和氛围的尴尬与观念的大碰撞让我感受到了荒谬的同时,又感受到隐隐约约的熟悉和认同。
而第三段脱离了某种对比之下,对我而言是真实的伤害的展示,或许是我也曾生活在这样窒息的亲子关系里,也许是我终于理解脱离这个环境并成功挣脱了定式的束缚学会了更自由的更内心化的表达,所以我才格外的喜欢这一切的冲突和对照吧。
客套的吹捧,对于规则和准确表达的执着,对于技术和能力的过度追求以及对于生活真实感受的忽视。
当然有语言表达的壁垒,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东亚环境里的贯彻的攀比和要求,而对于自由散漫的法国人来说,语言之外的观念差异似乎让他们的沟通更困难。
于佩尔的格格不入,和两遍都不甚完美的英文只是个开始,更多的来自于大家对于任何一种表达的需求从根本上的不同。
每个人都会乐器,但又不真正的享受演奏也不用它表达情感,沉迷于“好”的技术,像是展示的工具,证明我有某种“能力”并且对它的高度永远无法做到自我满足。
处处有诗却完全无诗意,诗人对爱情的解释被妈妈无情的反驳的拒绝,简直是东亚父母的真实写照,那些刻板印象和对于浪漫自由的鄙夷总是像刀一样在短短几声叹气和几句话里就戳到我。
爱是“约束”“拒绝”和“我不会害你”,而不是“支持”“尊重”“欣赏”,这实在是太东亚典型的伤害了。
于佩尔吃拌饭的画面,在绿色墙边漫游的画面,在岩石上和古建筑里睡着的画面,这些都是独属于法国人的松弛,也是旅行者的需求:吃饭,观赏,交流,居住。
环境是用来体验和享受,生活是用来突破和感受的,这才是诗人口中的真挚吧。
而可能对于大多数东亚教育下的我们,都会和那位妈妈一样,去提问“我难道不真挚吗?
”。
在我的成长过程里,“好”是有标准答案的,而时至今日依然“不好”的我,终于离开了这种思维定式,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和家人时,才意识到浪漫和自由生长的沃土是需要更西方的爱与尊重的。
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在最后痛击我的理由,不再是关于爱情行业,也不是单纯的文化对冲和表达障碍,而是在最后我看到了延续的观念上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我曾真正经历过的心灵上的冲击和思考,也是我发自内心的伤痛的共鸣。
10 ) 看不厌的洪试话唠片
我真的可以一直看下去洪常秀的絮絮叨叨的比日常生活还要慢节奏的电影。
经常想,要是现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导演想拍这种风格,还能不能行?
还是人们买账只是因为他是洪常秀?
这种极具依赖对话的电影比想象的要难拍很多,他真的掌握了语言最能表达人物关系博弈的微妙的那个层次,在这部片子里语言是贫瘠的、单薄的、弱小的,角色们用非母语交流,总有些词不达意的尴尬感;但同时语言又是强大的,特别是作为诗的语言,即便经过翻译,也还有撞击心灵的力量。
其实最开始对于于佩尔的角色Iris感到了如片中被闯入者一样的诧异甚至愤怒,后来竟渐渐理解她、甚至于对整个墨守成规一潭死水的东亚文化都产生了怀疑甚至抵触。
能通过简单的对话调动起这么多复杂的感情,是个很不简单的事儿。
影片很明显分为三个部分,三段“法语家教”引起的冲突逐渐升级,但Iris总能“修行”一般的不受影响,在母子争吵的时候,她喝着酒在石头上睡着。
洪的电影里确实不乏这类游离在世俗认知之外的角色,是否可以称之为“真挚”的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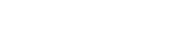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7.1洪尚秀04一个法国人和一堆韩国人说英语于佩尔是被洪尚秀绑架了吗
韩国人不是会钢琴就是会吉他
第一段戏剧性就很强,第二段是完整的重奏,让戏剧张力进一步加强,第三段是变奏中的重奏,让人疯魔。小切口讲大事儿,自由的洪常秀,足够日常,又足够优秀。
以尴尬、重复、拖沓为基调贯穿始终,反复就lost in translation进行深挖。大量无意义运镜、无效时长、无趣对话、拧巴的信息密度与节奏,都可以被解读为为此服务。文化的冲撞与行为难以消弭的隔阂、偏差、错位,语境的混乱与语言经翻译后的失真、简化、删减,不仅发生在异族、异语间,在诗与口语、代际间也存在。大多数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新鲜感、成就感后随之而来的总是间离感、浅薄感,searching is the fastest way;在不断的注意力转移与主题游离间试图找寻共识和锚点是绝对的挑战和折磨(诗人早死与美的短暂、恋母情结的猜测与母竞、理想与现实的价值衡量、谎言在信息差下的成效)。还是熟悉的粗糙未经设计的镜头和超大光比过曝的环境,反让人关注剧作、台词和表演本身,竟作为一种风格被驯化。
2024/04/21 BJIFF屡屡中箭,东亚人模板化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的一生,以及学什么干什么都要以show off为核心目的的精神传承。虽然这两个女学生年龄和身份不同,但都有令人尴尬的父亲/丈夫,都说不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都永远不敢自信说出proud of myself。女主不是来教法语了,是来给人家做心理咨询来了。女主真的牛逼,这就是欧洲人的松弛吗?不会当地语言,一分钱没有,食宿完全不考虑,先去小公园睡上一觉再说。被当地陌生男捞了就跟着走,在人家家躺了俩月才想着出来教法语。在去哪都需要申visa的我看来,惊讶的同时隐隐有点羡慕🚬
尴尴尬尬我的心,想要一份真感情
现在已不再是细节的拉扯了,可能是洪在情境内最抽象的一部作品。
于佩尔拍拍权海骁的肩是我2024年观影的年度时刻。
借旅行者/外来者的视角来审视韩国。在具体的情节构成上,依然是“重复与差异”的创作思路,尤其是两个学生在描述对音乐、镌刻名字、诗句的感受,都无意间泄露了自己的内心秘密。伊丽丝的转译就像在写诗,非常隽永。由此,观者想必也从质疑,转而体会到了情境所展露的幽默与人物身上的诚挚。第三段落的母亲训斥,又进入到了火辣的讽刺阶段。洪常秀又以拿手的梦境处理模糊这种尖锐感。开个脑洞,片中人物种对恋情的坚守是在回应现实中的汹涌舆论吗?
又回到洪尚秀最擅长的多层级结构,前两个段落,法语教学与石碑做出明显的循环设置后,又在二三段落中,对诗文做了对称的镜像设定。但到了第三段的尾声,突然出现了层级关系的进出位置,于是此前牢固的连续时空被动摇了。回头看第二段的尾声,“她去了哪里”,便打开了第三段落的入口。非常巧妙。
知道他拍的很节省 也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但是他拍的这个东西 不是给亚洲人看的
唯一没睡的
#BJIFF14-02 一模一样的迟疑和回答、反复确认的“这是一个问题吗”,全场大笑。东亚人的迟缓、谨慎,或者说愚钝、刻板,笑完也看到自己。第一部洪尚秀,这种小聪明的戏谑不算讨厌。
6.5。以近乎完全相同的對話結構描寫不同相遇中一致的日常片段,語言媒介的差異更加深了非英語母語者間對話套路的重複感。但洪常秀從去年開始接連三部都隨意過頭了,以上探討都不過是和于佩爾前兩次合作的老調重彈。
洪常秀近来的片子越来越欣赏不能。非要让要我写我也能写出两句,比如:“片中于佩尔饰演的法语老师的教学法(根据情景与交流随手写纸片然后朗读)之中几乎包含了洪常秀电影创作方法论的全部:即兴创作、小成本也无需负责、难辨真诚还是虚伪偶然还是必然并以此为乐、对自己娱乐上层中产的定位心知肚明却始终声称仍抱有一个穷诗人的理想……”但其实我只是想说:尬死了,不想奉陪了,你们开心就好……于佩尔在这部中已经成仙/妖了,按理说我们需要的是照妖镜。而洪常秀让每个人都看着她成仙,却不给我们照妖镜。
在东亚社会规范下被束缚的表达和被压抑的真实情感指向了语言的溃败、感受的无能、自我重复和自我欺骗。于佩尔作为一个在韩国教法语的旅行者,作为一个异文化的外来闯入者,她的视角像手术刀一样一下子在凝滞的东亚话语空间撕开一个口子,揭露出它的荒谬与空洞。人物在固定机位中被限制在狭小交际空间内,几组人物几乎总是占据整个画幅,直到一方终于忍受不住离开摄影机画面,交流中的压抑、窒息、局促扑面而来。最后主创交流环节也还原了电影里范式化的空洞语言,笑死我了
尬聊集。
笑死了
很尬,又尬得很假。像是邪教传教士统治下的i人地狱。从东亚的自卑滋长出了对欧美虚假的美化,和对东亚极端的贬低,甚至是恨
@Berlinale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