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梦墓园》剧情介绍
一种奇怪的睡眠病在士兵之中蔓延开来,患病的士兵们噩梦缠身,纷纷被送往了一处临时诊所之中接受治疗。金吉拉(金吉拉·潘帕斯 Jenjira Pongpas 饰)是一名平凡的家庭主妇,亦是医院内的志愿护士,乱世之中,这座似乎与世隔绝的医院仿佛世外桃源般宁静且充满了启示。 阿肯(雅琳帕特拉·鲁安格拉姆 Jarinpattra Rueangram 饰)是一位灵媒师,她通过通灵的方式使家属们和那些患病的士兵们相见。莱特(班罗普·洛罗伊 Banlop Lomnoi 饰)亦是这些士兵之一,可是一直没有任何人来探望他,他的存在引起了金吉拉的注意。莱特有一本记满了奇怪图案和文字的笔记本,也许事件的答案就埋藏在其中。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布莱顿惊魂叛逆少女宇宙中最明亮的屋顶鬼裤衩凯特琳事件办公室第七季朗·霍伯的灾难与女人们的对话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杀人依赖那些最伟大的比赛警中英雄重返天堂岛甜蜜海风坏总统皇后归来我在这儿暴雨梨花蜡笔小新:呼唤传说!三分钟嘎巴大进攻忠者无敌梦魇行者疾速追杀:芭蕾杀姬教训薇琪的秘密熟女镇第二季卡片战斗先导者overDress第二季娜塔丽归属何方史酷比:舞台风波两个恋爱
《幻梦墓园》长篇影评
1 ) 对散步意识与催眠术的观察:内脏学
拥有散步意识的主体是自为存在着的,它既是意识的运动,也是一种显现为现象的固定的现实存在,这样的主体的身体也就是由它自己产生的关于自身的一种表示,纯然是主体借以显示其原始本性的客体。
作为主体的诗意所观察的正是拥有散步意识的主体实现之表现的梦境形象,亦即主体的内意识本质所显象的现象与演绎的范畴,由于都是自为的、原初的存在,所有的内意识都可以以“人”的主体价值体系规定为作为有机体的器官与作为无机体的骨头,诗意在此所观察的正是器官与骨头在催眠术下的梦境形象。
眼球与政治 在所有的季节中,夏季是最年轻的季节,它把感性刺激放入内感官,控制我们的血液流动和器官功能。
被丛林覆盖的家宅是青春的、富有少年气息的,里面仰卧着被政治影响着的器官,它们还可以排尿、充血、思考、幻想,但政治已取代他们的眼球。
透过内感官意识,他们能冥冥感受到灯柱光色的变化,即使他们无法用眼球看见光色,但这些光色会透过政治影响他们的记忆,尤其是与他们散步过的街道、漫步过的树林相关的记忆:正是在夜间,在那被树荫包围着的青春家宅的夜间,灵魂交相传诵的食欲、历史记忆、感官经验在同样的光色转变印象中同化、无限化、秩序化,没有什么比寂静更能容得下这样的驯化了,我在寂静中进入这印象的空间,记忆中的声响——晚间摩托车的声响、电影院的声响、风吹树叶的声响、水车打在水面上的声响给印象重构了色彩,赋予它一个有声的躯体,这个躯体会在我们的耳边控制我们的灵魂、约束我们的言行,一种恐怖、无限、深邃的感觉在伪造的寂静中把我们紧紧抓住,这种感觉穿透了集会中的每一个人,让整个由政治主导的集会被黑暗的巨大静谧所迷惑,使集会也成为一个内感官的存在、成为一个具有印象色彩的躯体,它在夏日的夜晚之中,由夏夜的微风、嫩绿的树叶、清凉的湖水构成,它们如人体器官一样有节奏地工作、发出声音,进而催眠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相信自己被一所古老而坚固的家宅保护着,当我们觉得闷热,它让我们相信这是因为家宅外太寒冷,而家宅正与寒冷英勇地斗争着,正如我们的皮肤为了保护我们的内脏而与外在的寒风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变化着的灯柱已成为人性的存在,我们的灵魂便躲避其中,向它倾诉我们早已忘却的记忆,印象中的色彩如母亲的爱直达我们的心房。
这是多么伟大的催眠啊!
政治糊弄了我们的眼球,诱导我们把光色的印象当成了我们灵魂的母亲。
肠胃与语言 风雨过后,从树叶丛中落下的雨水嘀嗒就这样在闪烁,它使光线和平静如镜的水面发颤。
看到这水滴,就会听到颤抖声。
当眼球重新回到我们的外感官后,我们与家宅之外世界的联系逐渐明显、牢固,我们的血液流动也逐渐加快,肠胃开始蠕动、开始思念食物,当食物透过眼球刺激内感官时,唾液已潺潺流动,肠液也暗暗涌动。
当所有的唾液、胃液、肠液都得到满足后,嘴唇和牙齿会产生快活的景观,灵魂会喜形于色,通过语言表达出它们肠胃的快感,此时目光不再在指挥,词源不再在思考,只在痛苦中在快活中,在喧闹中在平静中,在嬉闹中在抱怨中,我们的行为如同在肠胃中蠕动的食团一样随意,听到唾液、胃液、肠液的流动声,如此动人、如此简洁、如此凉爽,好像随水车一起涌动的湖水,发出湖水的特别的叹息声,那种与我们的灵魂、身体、思想同步的叹息声,带着一丝忧伤、一丝淡淡的、展示的、流淌的、不可名状的忧伤,那是源于奴隶道德的一种同情,让灵魂惋惜在梦境中被规训的内感官并思念那规训自己意志的光色印象。
肠胃可以代谢食物残渣,但肠胃无法过滤灵魂对政治的同情;土地可以代谢人的遗骸,但土地无法过滤试图主导一切的权力意志。
如果说有什么是真正的爱,那肯定是肠胃对食物的同情和灵魂企图主宰食物的权力意志!
爱乐至极,话语便可颠三倒四,如溪流嬉笑着、细水流淌这,不会有任何干涩,似钟声一般如期而至,带着夏夜般的具有青春活力的青绿色声音——在我们的灵魂聆听大雨声、阵风声时也会听到的声音,语言从未如此这般湿润过,浸透了空气与身体,生出了白云与草履虫,在孕育的意志中灵魂感受到了生的纯粹的喜悦,那是肠胃第一次消化母乳的喜悦,口腔会通过发出“妈妈”的声响传达肠胃的喜悦,这是身体对灵魂的唯一一次凝视,它不在可以思考的记忆中,而是在语言的表达中。
骨头与音乐 灵魂在内感官的家宅中是无限的,骨头替灵魂规定了家宅之外的界限,同时,骨头和内脏相互通过对方规定自身的形象、形态:内脏通过骨架来规定内感官的家宅的结构;骨头通过内脏凝视主体的灵魂,骨头与内脏组成了相反力量的辩证法,它具有是非辩证法的判然两别的清晰性决定了空间意义上的内在与外在和时间意义上的短暂与永恒,可以用最简单的几何学解构梦境——通过四肢的运动来画出梦里的宫殿和内脏的喜悦,如音乐一般将兽性快感与渴求的细腻神韵相混合,反映灵魂的丰盈和生命的欲望。
骨头在凝视灵魂的丰盈和生命的欲望后随着音乐舞蹈,舞蹈带来人格的富有、内心的丰盈、洋溢和发泄、本能的健康和对自身的肯定,这些本该都是属于我们身体的,因为它们都来自我们所熟悉的经验的世界,在催眠中,灵魂脱离了骨头去追寻色彩和欲望,又是骨头帮助灵魂找回了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音乐把所有的身体聚集到一起,带着亲切的、乐施的、善意的信念去舞蹈,使自身生命充实,为了享乐而生活,却讽刺你争我夺互相倾轧,这是富人的、闲适者的社会,也是更自然的社会,因为自然不强求人们尊奉道德,只要求保持骨架的完整,这样人们才能回到现实、回到这个以音乐为本质的世界。
这里的音乐不似艺术般狂热,也不似美学般虚幻,而是如自然般真实。
艺术会腐烂,美学会消散,唯有音乐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
2 ) 看完电影后的午觉很奇怪。
幻梦墓园看完电影,去睡午觉。
睡前,脑子里简单的想了想《幻梦墓园》,就睡着了。
午睡中,感觉头顶空调有水滴落,用手摸头却没有水分,看了看手机,时间尚早,再睡一会儿?
又睡着了。
电话突然响了,以为是闹钟,原来是骚扰电话,挂了两次。
时间还有一会儿,再次闭上眼睛。
感觉时间在走,却始终走不到,闹钟需要叫醒我的那一刻。
听见外面有其他人在走动,很匆忙,关门声,然后安静。
我睁大了眼睛,看,悬挂的钟表,时间还未到,居然还能睡。
然后闭上眼睛,要继续睡完剩余时间。
这时候,闹钟响了,我奇怪的睁开眼睛,看已经到时的钟,转瞬间从1走到了5。
可是我还没觉的睡着。
3 ) 梦之境——与阿彼察邦谈《幻梦墓园》
(本文发表于“独放”公众号)用迷人的隐喻诊断病入膏肓的国度,于闪光的梦境中营造不断变换的体验。
作者:维奥莱特·卢卡(Violet Lucca)译者:Pincent校对:Rosine来源:《电影评论》(Film Comment)2016年3-4月刊
Cemetery of Splendor (2015)摒弃了《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 2010)和《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 2004)中对低成本泰国电影电视的致敬及其给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赋予的独特风味,《幻梦墓园》(Cemetery of Splendor, 2015)是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最鲜明的讨论泰国政治的电影。
当然,开放是相对的——电影中仍有大量神话和象征意义需要被解译——而这种神秘性是与泰国军事DCai政权的直接对话。
《幻梦墓园》也是导演最深沉感伤的作品,它以梦境的逻辑向人们诉说着泰国动荡不安的过去和暗淡的未来。
故事以导演的家乡孔敬(Khon Kaen)为背景,主要讲述了一位年迈的泰国妇女珍(由阿彼察邦经常合作的金吉拉·潘帕斯[Jenjira Pongpas Widner]饰演)的故事,她在一家诊所义务照顾昏迷的士兵。
这些士兵被安置在一所老旧的小学而不是医院,他们唯一的“治疗”方式是一种光照机,这种机器以前曾用于驻阿富汗的美军,能够帮助他们产生美好的梦境。
这些六英尺高、藤条状的光管在蓝色、绿色、樱桃粉色和血红色的图案中缓慢循环,这成为了影片令人眼花缭乱并隐含威胁的视觉主旋律,在士兵们瘫软的身体上若隐若现,就像是科幻片或美术馆装置中的场景。
(这些装置的概念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神经学研究,该项目通过将小鼠的神经元暴露在闪烁的光线下,成功地在小鼠体内创造出了人造记忆。
)与此同时,医院的医护人员关上了窗户,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将士兵们笼罩在黑暗之中,这是一次对柏拉图洞穴寓言的反写。
士兵们不时醒过来,珍照顾的年轻人伊特(由《热带疾病》中饰演士兵Keng的班罗普·洛罗伊[Banlop Lomnoi]饰演)第一次苏醒是在珍给他在胸口上涂按摩油时,但常常是话说到一半他就晕过去了。
正如珍发现的那样——多亏了神殿里的两位公主——学校坐落在一个古代王国的墓地遗址上,士兵们在他们沉睡时被征召参加一场为君主而战的战斗。
鉴于泰国波及甚广的“冒犯君主法”(译注,后同:lèse majesté law,亦称“大不敬罪”,是泰国的一项法律罪名。
泰国法律规定任何人“诽谤、侮辱或威胁国王、王后、王储或摄政王”,都可能面临3-15年的监禁处罚)的存在,公民因对君主制的轻微(或完全隐晦的)批评而遭到监禁的情况时有发生。
正如泰国的每个人都被剥夺了发表反对当局言论的权利一样,这些士兵也必须在不情愿和无意识的情况下服役;相反,他们的休眠也可以理解为公众消极地拒绝反抗DCai。
Cemetery of Splendor (2015)与阿彼察邦的其他电影一样,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许多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片段,它们表达了在泰国的感受:公园里有人指导的健美操课程、一只鸡在敞开的门廊里闲逛、露天夜市上的小吃摊位,但令人不安的睡眠阴影笼罩着这一切。
在影片非常尖锐的一个片段中,伊特和珍去了一家多厅电影院,坐在那里观看了一部淫秽的超自然恐怖电影的预告片。
正片开始前,观众在奏泰国国歌时起立(按照法律规定),但没有音乐,只有寂静。
接下来的蒙太奇画面削弱了任何关于进步的政治宣传:一群无家可归的人睡在路灯下,旁边是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泰国陆军元帅,独裁者。
1957年发动政变夺权,其后担任泰国总理,直到1963年去世)的壁画;一个在水库附近捡垃圾的人;一个睡在公交车候车亭里的人,候车亭上面贴着“欧洲婚礼移民”内容的广告。
当镜头回到霓虹灯闪烁的商场时,昏迷不醒的伊特正被抬出影院,沿着迷宫般的自动扶梯往下;画面慢慢淡出,并与其他士兵躺在教室里熟睡的画面交织,他们沐浴在梦境机器的邪恶光芒中,就好像伊特被拉入了地狱一样。
Fireworks(Archives) (2015)戳穿泰国政权的关于完美无瑕的虚假理念在影片中对护肤霜的讨论时找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这些护肤霜充其量只能护理皮肤表面,但通常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效果。
然而,阿彼察邦的作品中那种更加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是那些与某些意识形态在该地区蔓延有关的战争和种族灭绝相关的画面。
伊特带珍“游览”了一座只有他才能看到的宫殿;我们看到的丛林中到处都是来自萨拉凯库(Sala Keoku)寺庙的水泥雕塑,这座公园是由备受争议的神秘主义者/艺术家本勒阿·苏利拉特(Bunleua Sulilat)创建的,融合了佛教、印度教、万物有灵论和世俗艺术风格。
(苏利拉特曾在湄公河对岸的家乡老挝创建了一个类似的宗教公园,后在1975年的革命中被驱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拉凯库因被怀疑是某党人士据点而被泰国军队部分摧毁了。
)伊特和珍两人经过苏利拉特的两件雕塑作品,这些作品也出现在阿彼察邦的装置作品《烟花(档案)》(Fireworks[Archives], 2015)中:两个恋人在长椅上相拥,而在五英尺外有一对同样姿势的恋人,而他们是被摆成咧着嘴笑的骷髅。
尽管这些雕塑看起来很不吉利,但至少符合轮回的宗教信仰。
然而,在诊所外反复出现的挖掘机吊臂挖洞的画面(或声音)并没有提供如此舒适的环境:坟墓般的画面怪异恐怖地再现了今天柬埔寨杀戮场的模样——残酷地诉说着当局手下的死亡与苦难。
影片结尾处,当孩子们在坑上踢足球时,珍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些坑,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柬埔寨政权的批评者的觉悟。
挖掘机到底是在挖掘过去,还是在为未来建造坟墓,目前还不确定。
然而,对于面无表情强迫自己尽可能睁大眼睛的珍来说,要想从这场特殊的噩梦中醒来可能已经太迟了。
Cemetery of Splendor (2015) 以下为作者对阿彼察邦的专访 维奥莱特·卢卡(以下简称V):在我们采访的几天前,你在曼谷的Cinema Diverse放映了帕布罗·拉雷恩(Pablo Larraín)的《智利说不》(No, 2012),为什么是这部电影?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以下简称A):这部电影非常像泰国的一面镜子。
这几乎就像一个幻想,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投票。
我去投票了,但后来军队推翻了国家,所以我的投票无效。
《智利说不》是一部非常聪明的电影,它能让我们分享希望:“哦,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智利一样举行这样的活动。
”在皮诺切特(奥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诺切特·乌加特是前智利总统、智利军事DCai者,智利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统治智利长达16年,并在下台后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直至1998年。
1973年,皮诺切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建立右翼军政府)执政下的智利,人们过了16年才能出来投票,而16年可以让很多人忘记。
对于泰国来说,已经过去两年了。
因此,考虑到这种虐待人类的模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能需要10年或15年的时间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
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无法再拍电影了,但对于到那个影院的的观众,我向他们展示:“不要忘记,将来我们也可以拍这样的电影。
”
No (2012)V:《幻梦墓园》在泰国上映了吗?
A:还没有,我希望上映的,但我不确定现在是否是合适的时机,因为ShenCha制度的原因。
个人的人身安全也是一个担忧的因素。
V:这是你最鲜明讨论政治的电影,它与你对宗教和冥想的感受有什么关系?
A:这部电影是多种因素混合的结果,有一些政治影响,但我还是觉得这不是一部政治电影。
很多人都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冥想是我的兴趣之一,同时,冥想、无明(ignorance,又叫做无明支,佛教术语,名烦恼的别称,为明的相反词;为十二因缘之首位,一切苦之根本)以及佛教中的因果法则也有一点冲突。
我们是一个佛教国家,但却有如此之多的暴力事件发生。
所以这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这种宁静和时而发生的怀疑之间进行的拉扯。
V:在影片中,出现在珍面前的佛教女神来自于老挝。
你能谈谈泰国与老挝之间的这种关系吗?
A:传说中她们是来自老挝的公主,在那个时候,泰国东北部和老挝同属一个王国。
我自己与曼谷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因为我是在伊桑的东北部长大的。
我对历史研究得越多,就越觉得很悲哀,由于国家的统一,文化消失了,没有得到该有的推动。
因此,我最近的作品都是对这一地区的调查——几乎是一种想要接触并召回过去的渴望。
而对于金吉拉本人而言,她的亲生父亲来自老挝,所以当国家分裂时,她也与在老挝的父亲分离了。
Cemetery of Splendor (2015)V:这个地区还有GC主义的历史,美国对泰国的介入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A:美国与泰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合作,以反对从越南经老挝蔓延到泰国的GC主义。
人们对GC主义非常着迷,因为它承诺了更美好的未来。
然而在美国的影响下,人们摒弃了GC主义,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制造了许多怪物——尤其是泰国的将军(笑),(在电影中)墙上挂着的壁画里的那个人就是怪物之一。
V:美术对于影片很关键,宗教雕塑的运用有何意义?
A:整座寺庙,还有雕塑和标识,一直在宣扬佛教、因果报应和轮回。
这个雕塑就是苦难轮回的一部分,会让我想起在某些时期,我觉得在这里生活似乎非常压抑——被这种不断训导你的法律所支配,就好像生活在泰国你就一直是学生一样。
在学校里,我们也总是有这样的宣传、课文和诗歌,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孩子们被教育得要非常非常虔诚。
V:你是如何选择拍摄地点的?
A:这是在我的家乡,所以我知道所有的地方,而且这部电影大部分是基于我的成长记忆来拍摄的,有这家医院、电影院和这所学校。
我试图在影片中结合这三个地点的元素。
在前期制作过程中,我把所有湖边场景的剧本写作都转移到了我的家乡,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了。
拍摄场景里有一幅壁画,描绘了泰国最残暴政权的一位总理,但由于所有这些宣传,人们仍然对他顶礼膜拜。
孔敬,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地方,是他雕像的所在地,因为人们觉得他给这个地方带来了发展。
但对于我来说,看到他的雕像和所有关于他的装饰画,我是相当震惊的。
Cemetery of Splendor (2015)V:电影里人们在水边来回走的场景有什么含义?
A:我发现有时候群众演员并不擅长表演,但我也觉得这真的很美,因为这是一个电影制作的过程,一切都是关于控制的,关于成为木偶。
因此在湖边我想强调这种关于当木偶傀儡和拍电影的想法,以及我在泰国生活的感受。
V:你能谈谈与金吉拉的合作以及从她的生活中汲取素材的情况吗?
A:在过去的10年里,我和她合作了多次,不仅是长片,还有短片和装置作品。
她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已经融入到这些作品中了。
在这部电影里,我只是想拍摄她的新生活和她的记忆的本质,她与新的丈夫开启了新的生活,但她对新生活感到彷徨,并与年轻的女性一起反思。
V:去年秋天,你在韩国首演了一部戏剧作品《发烧室》(Fever Room, 2015),听起来像是《幻梦墓园》的延伸。
A:它们同属一个世界,在同一个发烧的梦里,实际上这是一场噩梦。
这两部作品有两个相同的角色珍和伊特,他们在记忆的发烧室里共同做梦,分享梦境与影像。
但《发烧室》更加抽象,它不受叙事的限制,它们就像一对双胞胎,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是我(接触戏剧)的第一次,当我走上舞台时,我感觉“这就是电影院”。
(舞台)上面就是电影发生的地方,然后观众在剧院里也与身处电影院极为相似,也许像是身处于子宫内。
所以我想,“也许观众会成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灯光照射在他们身上,观众几乎同时是角色也是观看者。
”因此就有了这种关于观看与被观看之间所存在的相互映射的反思,这对于《幻梦墓园》的理念以及做梦与睡觉的理念来说都很贴切,因为有时你只是在某种体验中进进出出——这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视角。
Fever Room (2015)原文:https://www.filmcomment.com/article/apichatpong-weerasethakul-cemetery-of-splendor/
4 ) 沉默在尖叫
到了澳洲以后越觉看国产电影的不易,能抓住的机会也只有电影节。
说起电影节,上月正是中澳国际电影节热火朝天的时候,听说黄教主得了影帝,听说他本人没那么高,听说……唯独没怎么听到电影的消息。
所以当我在街上瞥到亚洲太平洋电影节海报疾疾掠过眼角时,虎躯为之一震,终于……当然会先关注中国电影,聂隐娘,山河故人,心迷宫,塔洛……都是诚意之作,瞥到梦幻墓园,一间泛着绿光的安静病房,每张病床旁竖着荧荧灯管。
到了澳洲以后不知怎么的特别嗜睡,睡眠质量好像有所提高也不再做梦了,可能只是记不住了,但这张图分明就是我唯一恍惚记得的梦境,顿觉惊为天人,必去一探究竟。
扯远了……说回电影。
最频繁出现的场景是一间简陋的病房,十多张病床上每个病人都在沉睡,偶尔会有母鸡带着成群的子女在门口晃悠。
这些病人有时会醒来,又会在吃饭时把头摔进盘子里继续沉睡。
主角Jen是个残疾的中年女人,志愿看护,闲暇的时候看护们聊家长里短,有时还会没羞没躁地惊叹勃起的弹力。
Keng是个通灵的年轻姑娘,帮助家人和沉睡的士兵说话,Keng 和一老太描述她儿子的梦境,老太问他想吃什么,要多少辣椒,还要可乐?
要不要冰?
又有老太问沉睡的儿子,厨房装修什么颜色好呢。
为了改善治疗,新的机器被引进,那些变色的灯管能改善睡眠,士兵们不再打呼,不再噩梦。
Jen看护的士兵Itt没有家人照顾。
Jen经常一页一页地翻看他的笔记本,难以理解的文字和图画。
Itt有时会醒来,刚开始因为陌生而尴尬,后来亲近多了会一起去夜市吃路边摊,他们说到Jen 的丈夫,一个不打算回美国的退伍士兵,Itt 开玩笑:不会是恐怖分子吧。
他们一起看电影,恐怖色情雷电血腥特效的迅疾镜头,电影结束观众们静静地站起来等着国歌响起,虽然没有乐声,但他们还是一直站着。
Itt 告诉Jen 他想退休,士兵没有前途,还是卖月饼吧,说着靠在柱子上睡着了。
被Itt附身的Keng带Jen去看墓园,她们在废弃的公园里踩着树叶,Keng形容着Jen看不到的门槛,镜子,浴室…… Jen则指给她看树干上洪水留下的印记,树上挂着写有箴言的木板,情侣石像旁相同姿势的骨架,Jen给她看她残疾的腿,血线分割的肉堆在一起,Keng捏她的腿,问有没有感受到能量,之后一点一点地舔她的腿,Jen说你像小狗,继而忍不住流泪。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热带疾病,兽性在丛林的回归是阿彼察邦电影里不可缺少的部分。
Jen向女神祈祷,祈祷家人平安,自己不长皱纹,祈祷儿子Itt 醒来。
之后Jen和两个陌生的姑娘吃龙眼聊天,她不相信她们就是庙里的女神。
这里来自老挝的女神满怀善意特地来告诉她士兵们不会康复,因为学校下面古墓里的国王需要这些士兵为他战斗,然而外表与普通姑娘无异,个人觉得这种弱化戏剧性的处理方式很准确。
切换镜头时除了让政府的秘密项目没法秘密的的挖掘机,用的最多的就是灯管,它们慢慢地变成红色再变成绿色黄色蓝色,变化过程间隙很美,这种色彩变化偷偷幻化成背景,镜头切换到夜晚路灯下沉睡的流浪一家,切到河边静静坐着不说话的人,切到停车站的长椅上枕着手睡觉的人,背后婚纱照广告牌上欧洲男人和泰国女人笑着搂在一起,切到繁忙的商场里叠加的电梯,渐渐出现灯管的幻影,颜色仍然在变化,回到病房,只能听到蝉叫和风扇声。
个人很喜欢这组镜头,写实而克制,不矫揉不怜悯不呐喊,只是呈现。
有一幕让我想到超脱,所有人都睡着的晚上,Jen走过枯叶和废纸覆盖的地面,来到蟑螂出没桌椅推倒一片狼藉的教室,她和丈夫打电话:只有我醒着,我想起小时候忘了交的作业,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怪兽,她不自觉开始讲泰语,没说完就挂断了。
这段语言勉强沟通的婚姻必然是尴尬的,寻求理解也只能是徒劳,坐在看不见的墓园里时,Jen告诉Keng,也就是Itt,曾经对爱疑惑时常来这里坐着,又说起自己偏爱士兵,但更喜欢欧洲士兵,因为他们更有钱。
Keng问她那你现在还疑惑吗,Jen只是笑笑,我想她自己都不知道。
片尾镜头转到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有个男人嬉笑着浑水摸鱼。
镜头出现少有的缓慢移动,背景音乐欢快活泼,小孩们在工地尘土飞扬地踢足球,Jen坐在石凳上盯着他们,眼睛睁得很大,像Itt告诉她那样:睁大眼睛的话什么都看得见。
还有一句印象比较深刻,Jen告诉Itt,试着感受光的温度,姜文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思考电影时把闻到味道作为自己的标准。
这种对生命的感知,活生生的感觉,无关意义目的,与大家共勉。
整个故事无论情节还是结构都不算晦涩,避免了意识流,避免了零碎片段,克制着抽象的努力。
也许是阿彼察邦出于对资金需求的妥协开始寻求理解,但我仍觉得这是他满怀诚意想塞到观众怀里的一个故事。
只是个人偏好凌厉荒诞的风格,很遗憾没听到沉默之后或沉默背后的尖叫。
对于长时间的低质量睡眠,我一直用波德里亚的一句话安慰自己:绝梦比绝经还要糟糕,这是精神排卵的终结。
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多梦睡眠,我想迟早得血崩。
同理,每部作品近乎极致的抽象也离精神分裂不远了。
原载于看电影看到死公众号。
附:观影一天后做了个梦,梦里我试着坐在冬天里的长椅上,但感觉到椅子上冰雪的拉拽和危险气氛瞬间站起,我看到导演就在不远处,他好像在挣扎,但是不能动弹,我逃到某间房子里,大脑急速转动,我不能就这么逃走了,我得救他,扫帚?
用扫帚把他身上的冰块打碎?
那他得晕呐……于是我惊醒了……接受约稿对观影状态有一定影响,因为当时沟通决定基于剧情去写,所以观影时不时掏出手机在备忘录里记录片段情绪等,打扰别人也打扰了自己。
5 ) 请美丽善良的灵媒师为我们见证
战争很残酷,士兵们无法承受,身心俱疲,噩梦缠身,甚至病入膏肓,渴望治疗,渴望一座与世隔绝的、仿佛世外桃源般宁静且充满了启示的医院,让他们得以休息,得以疗养伤痕累累的身心。
为国家付出那么多,他们只是希望有个安身之所,而不是被国家遗忘。
但这终究还是沦为一场美妙而虚幻的梦。
所有的富丽堂皇都只是过往封尘的虚幻,等待他们的,是冰冷僵硬的断壁残垣。
他们当然心有不甘,死后的灵魂不愿去地狱,又去不了天堂,家人是他们唯一的归宿。
谁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呢?
——美丽善良的灵媒师。
灵媒师为这些漂泊的灵魂搭建了一座美丽的幻梦墓园,让他们得以拥抱家人。
梦是好的,但终究要醒来。
国家的强大有力的挖掘机正在轰轰烈烈地捣碎他们的幻梦墓园。
梦醒了,睁大眼睛看清眼前的现实吧。
睁大点,再大一点。
为国捐躯的士兵们,连个安静的理想墓园都没有。
感谢美丽善良的灵媒师,让尚在人世的家属,见证了这些为国捐躯的灵魂们渴望的茂盛的、充满活力又无比宁静的、幻梦一般的墓园。
在国家大灾大难面前,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在零零碎碎的生活里,记忆就是灵媒师,良知就是灵媒师。
请美丽善良的灵媒师为我们见证!
今日推荐《幻梦墓园》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YMNCE密码: f4r4
6 ) 利用色彩和声音营造的催眠效果
在阿彼察邦的镜头下,即便是最普通的树木、神龛、建筑物都能散发出摄人的魅力,那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灵性。
这部去年好评如潮的新作在我看来没太多新鲜的话题,梦幻与真实的交错,神灵与人类的互通早就在《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里探讨过了,隐晦的同性恋意味和政治讽刺色彩也是导演一向钟情的标签。
最让我佩服的是导演利用色彩和声音营造的催眠效果,不停变色的LED灯、旋转的吊扇和水车、错落的电梯,配合上几乎静止的长镜头,一种神秘莫测的致幻感渗透到画面上来。
7 ) 《看不见的战争》
(原文 Kong Rithdee from Film Critic,胖丁试译)阿彼察邦的《幻梦墓园》中,一个沉睡的士兵被征召,前去为古老的国王们打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由于他陷入了深眠中,一种几近昏迷的无知觉,一个忧郁的天堂,这位士兵无须移动任何一块肌肉,就可以在梦境中的战场中,为那些他未曾见过的大人物们发动无声的战役。
这揭示了一切:在泰国(或其他许多饱受相似苦难的国度),高高在上的权力不止想占有你的肉体,还想侵占你的灵魂。
你活着的时候他们需要你,而即便你成为了死魂,他们也不放过。
虽然阿彼察邦的手法是温柔的,却表达了他不懈的、从历史的黑洞中追索灵魂的挣扎——我的,你的,他的,他电影中的角色,甚至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灵魂。
有很多方式可以参考:依靠记忆和电影的洞察力,梦境和迷信的安慰,依靠痛苦和欢乐。
贯穿了阿彼察邦的短片、实验电影和摄影作品的那种张力,在这场无声战役中被充分表达:潜意识的救赎,以及在激变的洪流中渴望着亲密。
然而还不止这样。
即便是亲密关系也不能被完全信任:它太写实,太安详,太靠近无常的诱惑。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表层下翻腾的矛盾情绪,无休止地发生核反应。
(如阿彼察邦在清迈的展览名称《疯狂的安详》(Serenity of Madness),或是《幻梦墓园》这样既悲伤又华丽的词藻。
)灵魂颤抖着想要与肉体和解,忧郁又躁动不安的亡魂从死国归来,因为“天堂被高估了”(《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或者因为历史已经被遗忘(《纳布亚魅影》),或者因为在他的雨林中,今生和来世,过去和现实的区别早已模糊不清(这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有体现)。
这种张力,还体现了阿彼察邦另一种令人好奇的抗争:同所有的大导演一样,这位泰国导演的作品既是本土的,也是国际的;它既是他本人经历的体现,也是他意识形态的延伸。
它首先是一份私人日记,一种内化的痴迷,囿于这片他生长和生活的土地。
这份痴迷过于诚挚,乃至于感染了五湖四海的陌生人——对阿彼察邦来说,追索灵魂之战不仅是泰国东北部年轻人沟壑纵横的脸,也是阿联酋那些棕色皮肤的移民劳工们。
2000年初,随着阿彼察邦的事业逐渐上坡,关于他是否在故意创作“晦涩的艺术”来取悦外国影人(是指西方/日本/拉美?
这些批评从未说明)的争论在泰国和其他地方甚嚣尘上。
而“外国影人”们,却对他作品中的种种人类学细节,历史隐喻,宗教意义和政治影射一知半解,因为这些细节不幸地只有泰国当地人能够理解(有时甚至只包括东北部的住民)。
事实上,这是一场极其消耗的争论。
通过出身和国籍来归类任何艺术作品都是片面且未开化的。
但令人崩溃的是,这个问题反复浮现,因为它反映出了阿彼察邦创作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作品在他不断壮大的观众中的影响。
而阿彼察邦自己也深知这场争论。
在《幻梦墓园》中,他用一种狡黠而风趣的方式表达了出来:Jenjira Pongpas和她的美国丈夫造访了一座当地寺庙,来为神灵上供。
她献上了许多动物的小像,并且为Itt祈祷——那位沉睡士兵的灵魂正在梦境中战斗。
当她称呼Itt为“她的孩子(her son)”时,她的白人丈夫插话道:“我们有个新儿子了吗?
”“是的。
”Jenijira回答道,“他是个好人,他在为国家做贡献。
你是个外国人,你不会理解的。
”外国人不会理解的是什么?
是不理解为什么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是个好人吗?
或是压根不理解Jenijira所做的一切,在明亮俗气的地方寺庙里,为当地的神明献上这些超自然的贿赂?
更重要的是,这一幕结束时席卷而来的那种人性的温暖和希望,理解与否真的重要吗?
如果我们非要去理解这一切,或许我们需要先望向这片土地——更准确地说,这超越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更是他镜头下角色们所走过的那片土壤,跋涉过的那些森林,从长梦中醒来时的洞穴,还有那怪事频频的乡村医院长廊。
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布景,这是他天然的纹饰,是这片土地的灵魂。
不必多提的背景:阿彼察邦在泰国的东北部的Khon Kaen省Isan市长大。
他的父母都是医生。
这是一个饱受贫困和落后之苦的地区,一片被鬼怪和gong chan dang的故事锻造而成的高原,因暴乱的历史而伤痕累累。
在20世纪60年代,Isan是军队与越共作战的前线,而阿彼察电影重要标志之一的Nabua村,据称是武装叛乱分子第一次进攻政府军队的地方,枪林弹雨最终延绵了数十年之久。
直至今日,Isan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因为经济状况和政治倾向被边缘化。
千禧年后期,阿彼察邦的作品中体现出的那种颠覆性的能量,来源于上述不安的潜流。
但将时间往前推——1996年的《怒海狂涛》中,2003年的《鬼屋》,2000年半纪录片式的《正午显影》,2002年的长片《祝福》,以及2004年的《热带疾病》——阿彼察邦对当地社会朴素而专注的重现,已使观众难以忘怀。
电影银幕中的人物早已超越了银幕的表达:区分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界限被模糊,微弱且性感。
在1970~1980年代的社会洪流中,泰国电影中的村民形象大多浑身脏乱,总被忽视和边缘化。
这当然也是现实,在一个电影激进主义直接又直白的时期,这些农民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现实主义象征。
但21世纪的泰国是一个相对富裕,经济更加不平等的国家(至少在曼谷是这样)。
这种左翼的,极力呼吁公平和革命的宣传已经完全落伍。
虽然阿彼察邦的早期作品还十分生涩,但我们从中看到了他的真挚,看到他如何编织他人的命运,给予电影优雅的形式和神妙的轻灵。
这种在亲密和动荡中辗转的张力,使得阿彼察邦在肥皂剧和社会写实主义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正午显影》作为一部形而上的旅游记录,是对乡民生活的写意;《热带疾病》中的同性之爱串联起了关于丛林猛兽的民间传说;《祝福》中诊所的一幕既描绘了泰国医疗系统的写照,也描绘了我们绕开规则行事的本能;而缅甸人和他的泰国爱人的形象,显然是想引导我们直面两国之间普遍的敌意。
然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2006年,军队发生了针对Thaskin政府的政变(Isan是Thanskin拥护者的大本营);2014年,第二次政变发生,这次针对的是Thaskin的妹妹Yingluck。
除此之外,阿彼察邦本人于2007年被当局勒令从他的电影《恋爱症候群》中减去四幕。
他拒绝了,并且在后期中用黑框把这四幕强调了出来。
2010年,当《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即将创造历史,成为第一部赢得金棕榈的泰国电影之际,一场军方的镇压使得曼谷近百名的抗议者死亡。
当阿彼察邦飞去戛纳展映他的电影时,半个城市正在浓烟中燃烧。
我们不能把这些理解为一个导演成熟的唯一推力,但过去十年间的这些重要事件,无疑刺激了阿彼察邦的创作,来反映这激变的,被不安和恐惧笼罩着的政治社会现实。
这不是一种政治觉醒;无论其他影评家怎么评价,阿彼察邦的作品从未脱离过泰国的政治社会现实;不断升温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和阶级的急剧分化,这些仅仅使得他的观察更加锋利,更有勇气去直面现实的紧迫。
2009年的《原生》展览(Primitive),2012年用LomoKino拍摄的《灰烬》,以及《幻梦墓园》,蕴含了阿彼察邦一贯的对内在世界的痴迷,梦境的魔力,对回忆的信仰,Isan的地方身份,以及对历史的挖掘。
而在此之上,一种全新的、对当今泰国现实的理解和隐喻开始浮现。
从旧日的控制中挣脱,对灵魂的追索也变得更加大胆——同时也更悲伤了。
在《灰烬》中,阿彼察邦捕捉了他的朋友,他的狗,和偶遇的人,一切看似随意日常的印象拼贴——接着急促而来的,是一场抗议活动的片段,抗议者们为一名政治犯Ah Kong的关押而游行(他被指控为对国王不敬,不久后他死在了狱中)。
《灰烬》是一张以人为题的立体主义拼贴,同时也是一张支离破碎的亡魂的显像——一种无声的分离,脸孔与身体,光与影,人与人。
在那里,Ah Kong以精神而非肉体的形式存在。
于是有了那些士兵。
他们是阿彼察邦电影中的常客,象征着年轻,诱惑和破坏(比如《热带疾病》中的情侣之一,或是《原生》展览的短片中的那些士兵)。
但在《幻梦墓园》中,这部在2014年的政变后孕育多年的长片,士兵,鬼魂和集体无意识,终于趋于同一场绚烂的幻梦。
《幻梦墓园》的核心隐喻,围绕着一种沉睡怪病。
士兵们在Isan乡村的医院中昏迷着,被磷光闪闪的管子引导着,他们的灵魂被传送向无形体的战场。
其中一个人醒来了,然后又睡去,这次他一道攫去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灵魂,而她又引导着瘸腿的老妇人Jenjira进入了梦境。
这一切开始于那场参观曾是宫殿的墓地之旅。
这也许是泰国电影史上最奇妙,最温柔也最悲伤的场面之一,一个被失落的旧梦和意义占据的瞬间。
而据Jenjira的回忆,这片墓地也曾是泰国内战时期的防空洞,见证了人类因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互相厮杀。
一切都是明晰的,一切又都是朦胧的。
一切发生在我们清醒的时候,而当我们睡去,历史不断前进,平静于梦境的安详中。
真正的战斗,是艺术如何恢复自己独立的灵魂,而这场战斗还在继续。
8 ) 所有想升上天堂的人终将堕入地狱
作为阿彼察邦最后一部泰国电影,《幻梦墓园》跟他其他泰国片一样,呈现出潮湿,阴冷的印象,但全片都相当平和,并未出现《布米叔叔》里将恐惧物化出来的红眼黑影,而是单纯的展现出梦这个主题,当然也夹杂了导演的一些政治隐喻。
电影由一个又一个定景长镜头串联而成(如果我未记错的话,摇镜头只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节奏非常慢,而这其实与梦境的碎片化其实是相悖的,但另一方面定景拍摄所展示的旁观者视角却又和梦境如出一辙。
并且有非常多的对话对话,即便非常集中注意力还是差点睡着。
极少的镜头运动让电影本身显得单调和平淡,尽管这是阿彼察邦的作者风格,但还是有一点催眠。
低饱和度所呈现出来的荒芜感颓败感相当不错,修筑的新医院在一个隐秘的树林里,而其正好是国王宫殿的旧址,所有醒不来的军人都在梦里为国王而战。
这里也就涉及了导演的政治看法了,对缅泰关系的展示,对泰国国内的讽刺正是在此。
树林里的枯枝败叶,国王大厅的金碧辉煌;荒芜的树枝,粉色的大理石;奢华与衰败的对比相当震撼,而灵媒在梦里带着老婆婆进宫殿正是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一部分:导演并没有将宫殿本身拍出来,而是就在树林里拍摄树林的景象(挺像拉斯冯提尔的《狗镇》的感觉),所呈现出来的间离效果极具戏剧张力。
冒犯他人,就心求宽容;受人欺辱,却忘记饶恕。
坐过来和老婆婆一起吃水果的两个女神,在天空上蠕动的草履虫,最后在堆满土山的球场上踢球的孩子们...影片在梦境,现实与超现实中来回穿梭,就像颜色变幻的床头灯,上下左右交错的电梯一样,观影者也在随着情节推进而来来回回。
就像梦境一样毫无逻辑,却又非常打动人。
从这一部仍能看出阿彼察邦对毕赣的影响,很多画面确实让我不自觉的想到他,尽管毕赣的镜头运动是比阿彼察邦更加丰富的,但同样是表达梦境的电影,论电影所表达出来的故事本身还是更加深层要表达的东西,远远超过毕赣第二部《地球最后的夜晚》。
可以说毕赣在《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都将不同时空的人物放置到同一个画面里,能达到使电影有更多的解读空间,也更加难懂;但阿彼察邦的梦境相对来说就更加简单,他所表达的就是电影文本本身的东西。
2019年9月9日Leop
9 ) 《幻梦墓园》——无人不在梦中
第一次看泰国片也如此晦涩难懂:宗教半阴半阳、士兵半睡半醒、平民半福半苦、剧情半清半雾,现实难以分辨出不是在梦里,现世逃脱不出过往的束缚,心灵挣脱不掉鬼魂的羁绊,神灵赐福不来此刻的欢愉。
导演的镜头里既有一室似梦如幻的灯管霓虹,也有野地大便突遇妖风的诡异不解,分分钟要把人看的怀疑人生,难以明白自己是在看些什么。
影片讲述了一群患上昏睡症的士兵在一所学校改造成的医院里就医,一个年轻的灵媒女孩为士兵和他们的亲人传达信息,一个跛脚的中年女人作为志愿者照顾这些士兵。
医疗和神灵同时庇护着迷茫的灵魂,曾经充斥着杀戮的宫殿如今介于生与死的边缘,附身在灵媒身上的士兵牵引着中年女人跳跃在两世的华丽和苍凉中。
这里既是故土,也是坟墓;既有过辉煌,也尽归尘土;既呼喊过血泪,也已长出参天大树。
如果是现实,为何世界色彩的变化和士兵床头灯光的变化相同;如果是梦境,那么究竟世界是士兵的梦,还是士兵只是世界的一个BUG;如果现身的神灵是真的,为何如同普通的传教士般只说些鸡汤;如果有不息的恶灵,为何热爱杀戮却用梦境困住需战的士兵。
这些灯,究竟是引向前世的路,还是现世的桥?
导演的镜头太生活化,平直淡白像是在喝白开水,品起来无滋无味,却生生搅得头脑里懵沌难明,似有无数问题想问,又觉得一切自有他法,并不需一时。
像有关性的隐喻,一切自然而然,心安随意。
10 ) 这款床头灯哪里买?我也要一个
生产米田共的镜头,很直接。
管状床头灯好独特。
有趣的灵媒。
幻想能量球来治病。
“求神保佑我永远不长皱纹”,这女的要求太高。
扁担广场舞。
长镜头是为了让你体验那种场景,也是让你看清每个人穿什么衣服、鞋子。
神灵现身。
昏睡中支起帐篷,被女人玩弄。
椅子上坐来转去。
渐变色也有恐怖效果。
电风扇转啊转,仿佛要把鬼召唤出来。
床头灯卡哇伊,梦幻色彩,变来变去,太gay了。
画风跟蔡明亮有点像,某男主角甚至很像李康生。
突然到来的昏睡如同突然的一次死亡,让我们思考死亡的存在。
轻鬼片。
亡夫灵魂附体,如同拉拉在亲吻大腿。
对士兵冤魂的召唤。
帅哥加入广场舞,好可爱,手好柔软。
坐看少年玩土堆足球,如枯山水。
睁大眼睛,就一定是醒来吗?
三星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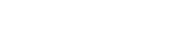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邦哥,我眼瞪得再大也真心伺候不了你。。。
看的自己都想睡着了,导演真行
探索时间与空间在电影中另一种打开方式应当的,但是电影不是这么枯燥的。导演的风格受蔡明亮影响很大,但是不得精髓,困意十足。
孔敬出生的阿彼,把伊森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交织进了本片,有强烈的政治隐喻和对这片土地深沉的情感。同样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后半部却呈现出与老挝女神出场前的前半部完全不同的魔幻现实主义意味。穿插进了一些装置和行为艺术等当代艺术
这是什么鬼?无聊到极致了…
阿彼察邦的电影里算是故事性比较强的了。
我还没文艺到看懂这部电影的地步,尼玛都是些什么东西啊?只记得有人拉屎和很漂亮的床头灯...
就是一装置作品。医院,教室,墓园,皇宫,美军,泰国士兵,嗜睡,梦境,大体来说围绕这几个概念打转怎么解读都可以。
重看,影史之选。阿彼察邦通过建筑空间的层积性构建权力拓扑,在现代科技场域与原始生命脉动的共生中创造双重性知觉装置。天空蠕动的草履虫颠覆了柏拉图洞穴喻的启蒙逻辑,将追求真理之光扭转为深入感官的混沌领域,唤醒被理性压抑的知觉潜能。环境音的沉浸式包裹、光影的催眠性律动、固定镜头的凝视惯性,共同编织成一套知觉扰乱系统,引领观者进入半梦半醒的意识状态。在此临界点上,历史与当下、生者与亡灵、真实与虚幻的界限不复存在,通感体验成为重构认知的唯一密钥。《幻梦墓园》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基于身体知觉的历史认识论。借由时空交错的知觉迷宫使电影媒介成为灵媒载体——既非对往昔的复魅,亦非沉溺于怀旧的挽歌,而是在清醒与昏睡的裂隙中,令被遮蔽的记忆经由震颤的肉身经验重获呼吸,孕育出超越二元的历史书写可能。
云里雾里有点意思
一部超现实的魔幻主义大片,竟然拍得如此迷离。挖掘机在足球场辛勤的劳作,为他们打造未来的住所,清醒的时候他们像是独立的个体,睡着的时候,他们在为这个国家服务,不知道军费够不够养一群沉睡的战士,这种职业也让人钦慕,睡着觉就可以拿到薪水。那路灯一样的呼吸灯就像招魂幡一样张挂在每个人的床头。沉睡的人们精神游历在四方,释放出无穷的张力,最终回到这个归宿,大夫和看护习以为常的做着工作,他们是被士兵带领走入梦幻还是,努力将士兵带入现实。片尾最后的交流有灵魂拷问之意,质问所有。都承受着战争的残酷,经历着与世隔绝,最终被压在病床上。一次次的婚姻并没有带来理想生活,美国人都是骗子穷鬼,怀揣心猿意马,这样的政治联姻没有未来。如果仅仅向单细胞生物,才能摆脱伤痕,自由遨游与阳光下,不至于变成坟墓还要干扰孩子们的游戏。
盯着风扇看十秒,然后水车一分钟,直接睡到
#Cannes2015#现实的皮肤下活着古老的灵魂,我明白啦,但是可不可以每场戏不要拍那么长!
一部讲睡眠的电影齐刷刷地看睡了三个观众氛围神秘故事离奇,应该是我喜欢的款式,但看完不明所以稍微了解了一下电影里的美泰背景,似乎很值得回味
这啥鸡巴。
装置艺术=治疗设备,在长椅上相拥的爱人/骷髅,旋转的吊扇/水车,上下的电梯。雕塑=宣扬佛教,因果轮回。医院/电影院/学校=乡愁/记忆。睁大眼=醒梦。观众一同患上嗜睡症。片末,摄影机轻摇,配乐显现。写实(视听)超现实 (天空不明生物)神秘主义(看不见的国王)。人物的兽性=舔舐大腿。
这片子正适合在春天到来的第二天早上带着极强的倦意看完。变色的梦,夜和失眠,阿彼察邦是懂失意的晚上和胡言乱语的。固定长镜,中长焦,什么都没发生,只有梦悄悄潜入。氛围和殡之森神似。只是觉得诗有点唐突,格格不入。
在《黑暗中的舞者》的重创后,阿彼察邦使我平静。
没看过的千万别看了,非常无聊,连个基本剧情都算不上有,莫名其妙的长镜头,莫名其妙的人,完全不知所云,看的人昏昏欲睡,真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当初看片名以为是恐怖片,结果完全不是,没看的千万不要下载不要看,纯粹霞耽误工夫,也不知道豆瓣这个7.1分是怎么打 出来的,这也挺梦幻的。
以为同样置身于同一纬度中做着同一个梦,感谢邦哥让我找回虚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