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之血》剧照
《萨米之血》剧情介绍
2016东京电影节影后&评委会大奖获奖影片。讲述一名生活在北欧北部的萨米族小女孩艾拉玛雅的成长故事。 萨米人,亦称拉普人,是生活在北欧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萨米人拥有自己的的语言(萨米语)及独特的民族音乐(Joik)及传统服饰等等,以饲养驯鹿为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瑞典挪威等国以强制其接受教育等方式试图同化萨米人,官方甚至禁止在学校和公共场合使用萨米语。(即本片背景)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温州女人罪证子弹2弹一下脑门对分手造成的影响黏土人斗牛士大山的儿子乐高蝙蝠侠大电影:DC英雄集结卡洛斯·巴利亚塔:冒牌先知丛林的鱼2福团·费斯特:好运旺旺来失忆融合WIXOSS一生特种兵归来3:绝密战场丑女无敌第一季爱情保镖恋爱迷宫Re: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第二季Part.2失落的大陆三月李花开假面骑士空我特别篇澎堤池爱吃拉面的小泉同学二代目模范生阿诺德醉拳苏乞儿金刚狼风中的花瓣金钱至上海伦·韦斯特探案集跑堂夫妻新年甜心
《萨米之血》长篇影评
1 ) 民族进化史&同化史
同化泣血而行艾乐米娅直到耄耋都不愿回到故乡,亲妹妹的葬礼她局促不安,迫切希望离开。
血缘里的同类视她为异族,她拼命想融入的一生都不会真正被接受。
主持葬礼的老人告诉她,妹妹一生都在为她标记驯鹿,她没法破除心中的障碍。
萨米族,获拉普族被瑞典人认为是愚钝,粗鲁,野蛮,喧嚣,甚至是尚未进化之物。
老人坐在酒店里,和旅途的瑞典人聊天中,她听到那句伴随了她一生的嘲弄:拉普人像野蛮人一样,追逐驯鹿大声喊叫,多么烦人。
她静静听着,沉默不言无法迈步的女孩女孩和妹妹就读当地的学校,50年代,在民族部落,学校里已经禁止萨米人讲当地语言,而是必须讲瑞典语。
艾乐米娅的妹妹读不来瑞典诗,而艾乐米娅却能悠扬的唱出瑞典诗,老师恩典她能够接待远方来的客人。
这时的她充满期待。
幻想太快被打破,客人拿她当研究土著民族的工具,即使窗子外面有男人在偷窥,仍然命令她脱掉衣服。
赤裸着,丈量眼睛宽度,鼻子高度,身体,她在高级的人面前只是一个研究标本。
之后被男孩们割掉耳朵的一部分,她就像驯鹿一样,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是蠢笨的。
所以舞会上遇到的男人对她来说就是天神一样的存在,穿着得体,笑容完美,接纳她,她对欲望的初级感受都来自这个男人。
她没法对男孩讲出自己是拉普人,对这个身份厌弃。
于是编出一个名字,第一次大声喊出肮脏的拉普人。
同化,是胜利的,从人对自身身份的厌弃开始。
艾乐米娅想接受更高的教育,却被老师告知拉普人不像瑞典人一样聪明,不能继续接受教育了。
同化,就是要你像我一样,但永远低我一等。
被嫌弃的克里斯蒂娜的一生编来的名字,偷来的衣服,却在一块蛋糕上漏了馅。
她走在瑞典的城市里,这里充满了高级人种的智慧,被修缮整齐的西式园林在街道上秩序盎然,喷泉,她对一切都充满期待。
来到那个爱慕的男人家里后因为不知道蛋糕上的蓝莓是否能吃,被男人的母亲一眼看穿。
男人的母亲不在乎是否发生关系会使她受到伤害,她只说:拉普人心眼多着呢。
在尼古拉斯一家的夜里,她偷偷起来,抚摸钢琴的琴键,不敢让它发出声音,抚摸电话,抚摸男人的身体,她拼命的想从触觉中感受这里的一切,融进这个社会,她笑容满足,做了个短暂的梦。
就像火柴划来的烤火鸡。
火柴熄灭一切都会坍塌。
用编来的名字,附上从书籍中看到的莱勒姓氏,假装自己是德国人,她看到瑞典的女孩,身材高挑,神态骄傲,无比羡慕,相比之下,她又矮又胖,头发粗糙。
她跟学校的太妹女孩混在一起,高兴的以为自己被接纳了,却在看到学费账单后被打回原形。
她回去找男孩的家庭,在生日会唱民歌,她明白,无论宴会上的女孩是善意的,还是捉弄的,此刻的她就是一只任人参观的低级动物,向男孩一家借钱后被拒绝的她只能回到嫌弃的家乡。
家乡如此原始,背靠高山,草原上是和驯鹿驻在一起扎营为生的同族人。
她的妈妈,同族人,在长久的隔绝和偏见里也获得了同样的东西。
正如瑞典人无法接纳拉普人一样,拉普人也无法融入一个所谓的文明社会。
全篇最温暖的一段就是她抱着妹妹洗澡,妹妹是始终信任接纳她的人,在她的拥抱下,安心的像水中仰去。
开心的时候唱起悠扬的民族歌谣,那是姐姐教给她的。
“割掉的耳朵”不难想象,当艾乐米娅拿着银腰带如愿回到文明社会学习之后,她会遭遇什么。
直到老年也不愿再回去故乡,这一辈子,听过了多少句,拉普人是肮脏的人,终于被顺利同化,得到的,不过是另一种无知。
她憎恨一辈子的民族称谓,转过头来,才明白不过是傲慢。
就像贫穷,我们一辈子都追求远离贫穷,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无论怎么想,贫穷都是被人造的词语,靠这个词语,实现阶级的分化,把罪恶都推给贫穷,让人对这个词深恶痛疾。
一种人凭什么去决定另一种人的生活方式,连语言都丢弃,抛弃人类的历史。
轻视同类呢。
当推行同化的时候,一定也是高高在上的寄予了美丽的希望,希望自己的国家走上更高的层面,人民实在大一统。
但孵化出的,尽是隔离。
把历史曲折的一步,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留下的,绝不是残缺的耳朵。
2 ) 这是一个通用的道理啊
抛开萨米族人的身体特征,通用一个道理:人类总是向往更高级、更强大的文明,并且多少会有些为自己曾经低级一些(相对而言)的文明而感到羞耻,并企图更多的脱离它。
回望我们的生活:农村向往城镇,城镇向往城市,城市向往省城,省城向往北上广深……所谓的关爱和保留,那是站在高级别文明的角度带着抚慰的心来做这件事。
这是一部细腻的电影。
不过老妇的一个细节出错了,少女时期的女主被割伤的是左耳,老妇试图遮挡的是右耳——我这烦死人的观察力啊!
当然,如果再加上萨米人的身体特征,这会让他们更加觉得世界之不公平了。
3 ) 歧视在她心中画了一个框,把她的一生都囿困其中
片子表达的很克制,可无处不能感受到艾拉玛雅的迷失与痛苦。
她深爱着家人和妹妹,可她憎恶这个族群。
她真的憎恶这个族群吗?
并不是。
他们的生活其实很美好质朴,可歧视在她的心中画了一个框,把她的一生都囿困其中。
她无法再认同自己的生活,她再看不见肆意生长的草原,再听不进婉转绵长的joik(萨米族的民族音乐)即使她挣扎逃离开了这样的生活,可这一切原本就是她的血肉,哪怕血淋淋地剥离开了,还是会生长出来。
人无法不爱自己,憎恶自己的人是很难生存的,所以她只能鄙夷诋毁整个族群,说他们“太吵了,爱偷东西,嘴里没有一句真话”等等。
艾拉玛雅对萨米族人的评价片中的老师对艾拉玛雅不错,但老师仍然认为拉普人(萨米族的另一种称谓)在生理构造上就无法适应“文明”社会,老师的好带着倨傲的怜悯。
老师会赠送她诗集,会给她分享自己青春时最爱的诗篇,却不相信她有能力适应“文明现代”社会的脚步,坚持不给她写推荐信。
老师给艾拉玛雅分享的诗歌,似乎也是艾拉玛雅一生暗喻
老师拒绝给艾拉玛雅写推荐信帅气的尼古拉斯会收留她,也会在她感到难为情的时候第一个安慰她,可尼古拉斯跟她的接触是掩藏在礼貌修养下的好奇,是新鲜感,是窥探欲,唯独没有平等的爱。
所以会在父母的要求下毫不犹豫赶她出门,也会在她索求帮助时残忍地揭开她的谎言和伤疤。
艾拉玛雅无助地拉扯着尼古拉斯的衣摆祈求帮助却被无情甩开礼貌克制的歧视尚且如此,更别谈她平日里遭受的嘲笑和攻击了。
攻击她的人甚至用标记牲畜的方法对她进行了割耳,当她被一群人压到在地上无法动弹,这时的无力感对是身份认同最惨烈的一击。
艾拉玛雅被一群歧视者按在地上如同牲畜般执行割耳不谈歧视者的语言和行为的攻击,哪怕是走在路上,没有恶意的陌生人投来探寻和戒备的眼光,会在她的内心放大无数倍,所有的笑声都是嘲笑,所有的窃窃私语都是编排鄙夷……她把别人的眼光内化,于是憎恶自己,然后憎恶又投射她的族群上。
记录萨米青少年的生长情况时让她们赤身裸体她带妹妹感受水流这段看起来特纯净美好,她帮妹妹挤干头发上的水,像她之前清洗自己时一样,其实是想挤掉身上可能说是“原始”的气息。
她想要把这种“劣等”的气息从自己的身上洗去,从妹妹身上的洗去。
艾拉玛雅帮妹妹挤干头发上的水她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她在别人的眼光构建的世界里无比憎恶自己的来处,可瑞典人生活的世界,她以为应当前往的去处,她也融不进去。
在迷雾里她与驯鹿搏斗也是在杀死自己体内所谓“原始”的那一部分,她太憎恶自己了,可她又不得不爱着自己和族人……
艾拉玛雅杀死父亲留下的驯鹿片中没有交代她逃离族群以后的几十年是如何度过的,可看她前往妹妹葬礼一路上对于joik和萨米族的评价,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在迷失和痛苦的一生中不断杀死自己的。
她必须时刻切除自己身上新长出来的属于过去的血肉,这太疼了,这太疼了……所以她连妹妹的葬礼都无法多待哪怕片刻,她必须切除,时刻切断,太令人心痛了。
最后爬上那座诞育她的山,走进那片释放她的草原,几十年前的风再一次轻抚过她的脸颊时,是否能吹散她内心对自己的憎恶呢?
老年艾拉玛雅爬上萨米族人生活的山
4 ) 那些消逝的
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不静静心心的时候根本看不进去,看进去了又觉好像胸口堵着一口干干净净的冷气,带着点草木气息带着点动物的味道,上不去下不来,冷冰冰的卡着,让人难受的厉害。
这种堵着的感觉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有几分相似。
看完影片我特意的查了萨米人的资料,他们被称作欧洲最后的土著,也是全世界人最少的土著。
和全世界所有的土著一样,他们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都和这个现代化的高科技社会无比的格格不入,就像当年的印第安人,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却又骄傲的昂着头颅,在夜色中的树林里狼一样的嚎叫。
最近不知道是我有心还是这个社会开始有心,我频繁的能看到各种关于语言消亡的文章,有英文的有中文的。
英语文章不多赘述,但是一串串数据一张张图标排列组合,再引用这个教授那个专家的采访,比言辞恳切感情充沛的营销号小文章更让人触目惊心。
我是一个标准的上海人,我的祖辈都是连普通话都听不太懂,看电视都想native speaker一样只能看那么几个频道的原住民,可是我作为他们的后代,没有办法标准的用上海话发出“我”这个音,也有许多俚语我都无法运用甚至无法理解,和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不同的是,我并不是因为抗拒自己的原生文化想要逃离原生家庭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只是因为从幼儿园开始,就生活在一个除了家人所有人都讲普通话的世界,我失去了吴地语言的语言环境了。
不光我,我高中里的上海同学们也经常被家里的长辈半是无奈半是玩笑说成是“洋泾浜”(外来人说上海话的腔调),连我们都是如此,遑论那些“新上海人”呢。
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对自己的文化抱有一种不认同的情感,和她以民族为骄傲的妹妹恰好相反。
瑞典似乎一直在似乎试图同化萨米这个民族,又好像不是。
他们一边禁止公共场合萨米语的使用,一边又告诉萨米人当他们的教育结束后等待他们的仍旧是帐篷和驯鹿。
这些外来者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认为萨米人天生低他们一等,像对待驯鹿一样对待着女孩,像研究标本一样研究她们的身体。
无怪乎玛雅,或者说克里斯蒂娜想要逃离,而其他地萨米人对“逃离者”抱有如此大的敌意。
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冲突与无法融合,如果瑞典政府对待萨米人,如果学校对待萨米人不是这样的态度,我想事情有可能不会发展到那样水火不容的地步。
语言是会死亡的,萨米语正在死亡,许许多多的语言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湮灭了声息,想没了油灯,像燃烧殆尽的蜡烛。
而语言的死亡,是文化的死亡,是种族的死亡,是历史最后的落幕。
那些消逝的,才是应该被记住的。
5 ) 杀死自己的少女
其实在看之前我就已经被剧透过了。
记得以前在哪个公众号里有提到过它,虽然具体情节早就忘了,但也依稀记得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少女叛逆的成长历程。
带着这样的预设,其实就少了许多趣味。
看到开头的老太太时,我大底就猜到了接下来应该就是倒叙回忆了,果不其然。
但是接下来,叛逆少女成长过程中心中的矛盾和斗争确是表现的恰到好处,真的让我惊艳了一番。
记忆回到小时候,身为萨米族的少女艾拉玛雅自小以来,便面临着来自瑞典人歧视和白眼,被当作动物一般的体检,被其他少年割去耳朵一角,这一切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想要摆脱这些愚蠢的生活,只有成为瑞典人。
于是她努力学习瑞典语,偷衣服去参加舞会,偷偷坐上火车去城里找尼克拉斯,改掉自己的名字,烧掉萨米族的传统服饰,去校园求学等等,经历着这样一段短暂而激烈的挣扎历程。
但其实,这时候的她多少还是有些矛盾的,虽然心怀着对瑞典人的向往,但是他也忘不掉在萨米族里的一切,一直都保留着父亲留下来的小刀,最后也是带着蛋糕回到家乡。
直到那一夜在帐篷里,当她说出“我不想再当艾拉玛雅了”“我不想再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不想像马戏团的猴子似的活一辈子”,这三个不想,她在心里彻底把自己和萨米族划开界限,第二天她下决心杀死父亲留下来的麋鹿,麋鹿倒下的那一瞬,克里斯汀娜也杀死了艾拉玛雅,自己萨米族的血统就如同这麋鹿的血一般,慢慢流尽。
直到母亲像是看着怪物似得扔下银腰带,回忆到此结束。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当时间回到现世,她就像在找寻着什么似的,远离热闹的人群,爬上高山,看着曾经熟悉的风景,最后回到自己出生的山寨里,山风徐徐,她站在阳光下。
此时故事戛然而止。
最后响起的歌声,就像她当时在静静的湖面上,对着妹妹唱的一样。
整部电影是相当优秀的,明明是导演的长篇处女作,画面、配乐、台词、隐喻等等都表现的很完美。
但是在剧情衔接上,总感觉处理的不是很好,不知道这是导演特意安排想表现出少女内心矛盾的状态还是难道我看的是删减版吗,剧情发展有些太跳跃了,尤其是前半段,感觉像是在看话剧一般,从这一幕到下一幕,直接省略了过渡。
虽然说要把一位少女的成长历程压缩到短短一个多少时的电影里还是困难的,为了情节发展省却必要的过渡,着实不太妥。
结尾虽有些突兀,但这样也或许恰到好处。
与其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少女叛逆的成长历程,我倒觉得这是一个觉醒的异族女孩,想要去掉自己的标签,融入主流的可悲故事。
6 ) 萨米之血
出生于那样一种独特文明中的人们有没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
当你看到艾拉·玛雅进退失据,手足无措但仍然坚定向前的时候,这个故事并就不再只是有关于狭义的“权利”,而是问向了更宏大的“命运”文/杨时旸本文首发于总第815期《中国新闻周刊》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逃离于原始身份——原生家庭、故乡或者原初的特定文化的桎梏。
人们奔赴远方,坚定地拒绝回头,这种逃离有时成就自己,同时也伤害自己,这其中的撕裂感只能默默消化。
就如同这部《萨米之血》中的艾拉·玛雅,突然之间就发现了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另一种可能性与未来。
她飞蛾扑火般地奔赴,哪怕不惜焚毁自己的一切过往。
其实,《萨米之血》讲述的是一个很冷门的故事,但它却反射出了一种普遍性的焦虑。
北欧地区居住着一群被称为萨米人的原住民,他们有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
在上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瑞典一直企图同化这个游牧民族,他们不能在学校使用自己的语言,必须讲瑞典语。
但同时,他们又被告知,接受短暂的教育之后他们就仍然要回到高山的帐篷里,继续与驯鹿为伍,因为当时的人类学家们在人种理论的蛊惑之下,固执地认定这个民族是低人一等的,而故事的主人公,女孩艾拉·玛雅却倔强地想离开高原。
《萨米之血》有着大量清冽、冷峻的自然风光以及稀疏的台词对白,它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犹如人类学纪录片一样沉闷,也绝没有俯视视角的猎奇,它平缓地叙述,从当下的一场葬礼开始,从最现代化的生活场景切入,然后迅速转回了数十年前,一个女孩第一次经历文化休克的瞬间。
它是一部被眼神、手势、细节等等一起丰沛细部共同成就的电影。
《萨米之血》的优秀之处在于不只呈现现象,而是始终注视着一种困惑和困境——姐妹俩一起去学校接受教育,姐姐突然爱上了崭新的生活,而妹妹却一直以萨米的血统为荣,拒绝做出任何改变。
这导向了很多疑问,比如,一个游牧民族的人遇到了一种更现代化的、更丰沛的文明,如果努力融入,算不算一种文化上的背叛?
又或者,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出生于那样一种独特文明中的人们有没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
而这种选择本身是否一定意味着某种意识形态?
当你看到艾拉·玛雅进退失据,手足无措但仍然坚定向前的时候,这个故事并就不再只是有关于狭义的“权利”,而是问向了更宏大的“命运”。
女孩整日穿着象征民族特征的衣服,却看到了其他人穿着时髦的衣裳,她看到了自己的老师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生活,而自己注定回到牧区驯养驯鹿,她知道自己身上的气味,也羡慕城市中炫目的舞会,所以,她才会偷偷穿上别人的花裙子,暗自模仿着翘起手指端着咖啡杯。
那个时刻,困境就出现了。
女孩被困在了两种文化之间,她奔赴崭新生活的行为,被同族的少女们鄙夷,而她却又注定无法毫无障碍地被瑞典人接纳,她在两边,都是异族,无从归类。
瞬间,孤独就尖锐了起来。
她的性觉醒和文化觉醒是一同生发的,但到后来,你很难区分那份主动到底是一种需求还是一种策略。
她和瑞典男孩的肉身关系成为她逃脱原生身份中最极端的一环,交换体液,交融基因,再没什么比这更决绝地叛离于自己的文化了,更何况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以封闭为特征的“纯洁”。
驯鹿成为了《萨米之血》中最经典、最直接的象征物。
萨米人要给小鹿用刀子割耳标,以表明一只驯鹿从属于某个主人,而艾拉·玛雅到了城市,在打斗中,有男孩儿夺过了她手中的刀子,给她割了耳标。
萨米人驯化鹿,瑞典人驯化萨米人。
而那些所谓的人类学家剥光了这群萨米孩子的衣服,测量身体指标,那动作都犹如人对待鹿。
在学校时,艾拉·玛雅故意给自己改名克里斯蒂娜,但在别人心里,她一直是玛雅。
多年之后,早已成为老师,在城市定居的她,儿子称呼她的就是克里斯蒂娜。
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争斗算是成功了。
但她去参加了妹妹的葬礼——在数十年都未曾返回故乡之后,她又一次回魂到了童年时的状态,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只不过这一次是倒转的身份。
她附和着游客对萨米人的抱怨,面对着同族人敌意的目光。
她逃离了一段还是一生?
或者我们又是否真的能逃离于过往和原初?
7 ) 逃离于血
(文/杨时旸)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逃离于原始身份——原生家庭、故乡或者原初的特定文化的桎梏。
人们奔赴远方,坚定地拒绝回头,这种逃离有时成就自己,同时也伤害自己,这其中的撕裂感只能默默消化。
就如同这部《萨米之血》中的艾拉-玛雅,突然之间就发现了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另一种可能性与未来。
她飞蛾扑火般地奔赴,哪怕不惜焚毁自己的一起过往。
其实,《萨米之血》讲述的是一个很冷门的故事,但它却反射出了一种普遍性的焦虑。
北欧地区居住着一群被称为萨米人的原住民,他们有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
在上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瑞典一直企图同化这个游牧民族,他们不能在学校使用自己的语言,必须讲瑞典语,但同时,他们又被告知,接受短暂的教育之后他们就仍然要回到高山的帐篷里,继续与驯鹿为伍,因为当时的人类学家们在人种理论的蛊惑之下,固执地认定这个民族是低人一等的,他们的脑容量不足以支撑起在文明世界生存的能力。
而故事的主人公,女孩艾拉-玛雅却倔强的想离开高原。
《萨米之血》有着大量清冽、冷峻的自然风光以及稀疏的台词对白,它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犹如人类学记录片一样沉闷,也绝没有俯视视角的猎奇,它平缓地叙述,从当下的一场葬礼开始,从最现代化的生活场景切入,然后迅速转回了数十年前,一个女孩第一次经历文化休克的瞬间。
它是一部被眼神、手势、细节等等一起丰沛细部共同成就的电影,那些交替出现的恐惧和希冀的微表情,那些努力模仿但终不得法的手势,一起见证了一个女孩发现一种崭新文明并且想投身于中的微妙的心路历程。
《萨米之血》的优秀之处在于不只呈现现象,而是始终注视着一种困惑和困境——姐妹俩一起去学校接受教育,姐姐突然爱上了崭新的生活,努力学习瑞典语,想留在城市,而妹妹却一直以萨米的血统为荣,拒绝做出任何改变。
这两个人代表了面对新文明的两种典型的态度,而这态度背后的观念却又与人们的道德判断相关。
这导向了很多疑问,比如,一个游牧民族的人遇到了一种更现代化的、更丰沛的文明,如果努力融入,算不算一种文化上的背叛?
又或者,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出生于那样一种独特文明中的人们有没有权力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
而这种选择本身是否一定意味着某种意识形态?
当你看到艾拉-玛雅进退失据,手足无措但仍然坚定向前的时候,这个故事并就不再只是有关于狭义的“权利”,而是问向了更宏大的“命运”。
女孩对于新生活的选择几乎出自于本能的觉醒。
她整日穿着象征着民族特征的衣服,却看到了其他人穿着时髦的衣裳,她看到了自己的老师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生活,而自己注定回到牧区驯养驯鹿,她知道自己身上的气味,也羡慕城市中炫目的舞会,所以,她才会偷偷穿上别人的花裙子,暗自模仿着翘起手指端着咖啡杯。
那个时刻,困境就出现了。
女孩被困在了两种文化之间,她奔赴崭新生活的行为,被同族的少女们鄙夷,而她却又注定无法毫无障碍地被瑞典人接纳,她在两边,都是异族,无从归类。
人是一种需要群体认同的生物,当两个群体都拒绝她的融入,孤独就尖锐了起来。
她有时像个英勇的战士,有时又只是个无助的少女。
她的性觉醒和文化觉醒是一同生发的,但到后来,你很难区分那份主动到底是一种需求还是一种策略。
她和瑞典男孩的肉身关系成为了他逃脱原生身份中最极端的一环,交换体液,交融基因,再没什么比这更决绝地叛离于自己的文化了,更何况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以封闭为特征的“纯洁”。
驯鹿成为了《萨米之血》中最经典、最直接的象征物。
萨米人要给小鹿用刀子割耳标,以表明一只驯鹿从属于某个主人,而艾拉-玛雅到了城市,在打斗中,有男孩儿夺过了她手中的刀子,给她的割了耳标。
萨米人驯化鹿,瑞典人驯化萨米人。
而那些所谓的人类学家剥光了这群萨米孩子的衣服,测量身体指标,那动作都犹如人对待鹿。
面对这样的耻辱,有人选择逃回自己的文化中,更确定地隔离,而有人却选择义无反顾地融入。
在学校时,艾拉-玛雅故意给自己改名克里斯蒂娜,但在别人心里,她一直是玛雅。
多年之后,早已成为老师,在城市定居的她,儿子称呼她的就是克里斯蒂娜。
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争斗算是成功了。
但她去参加了妹妹的葬礼——在数十年都未曾返回故乡之后,她又一次回魂到了童年时的状态,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只不过这一次是倒转的身份。
她附和着游客对萨米人的抱怨,面对着同族人敌意的目光。
她逃离了一段还是一生?
或者我们又是否真的能逃离于过往和原初?
8 ) 我又冷又孤独,她也是。
今年我看了70部影视作品,当然还是以电影为主,零星地看了几部电视剧记录片。
好的作品特别特别多,《萨米之血》不是最好的,我甚至都没打五星,但是是最触动我的。
所以我也不说推荐给谁看了,一千个哈姆雷特嘛。
我没想到这部电影会给我留下这么深的印象,看之前没想到,看过以后也没想到。
我在极地光影电影节看了六个短片、一部记录片和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唯一一部在大厅看的,因为太小众了,临时做的字幕也来不及加上,就在大银幕下临时加了字幕器。
看的时候特别难受,几次想逃。
我平常看电影费时间就是因为遇到一些画面我会逃避,暂停上半个小时才缓过来,或者好几天。
在电影院是逃无可逃的。
现在我脑海里都还能回想起悠扬的Yoik(萨米人唱的民谣);那个给人感觉特别像王菲的瑞典女老师;那个帅得我窒息的Niklas;还有女主角Ella Marja倔强的脸庞。
女主角拼命想摆脱自己的出身,正好撞上我的经历。
就像大沛沛最喜欢的三部电影之一,和《战争之王》、《肖申克的救赎》并列的是《Zootopia》,他朋友还诟病他居然把迪士尼和肖申克排在一起。
我一开始也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那动画片就挺欢乐的嘛,别的也没什么了,他说其实是和他去墨尔本读书的经历有关,这种刚到一个大城市受到许多冲击最后又自己努力调整过来的经历。
被社会歧视惯的少数族裔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个是沙文主义,一个是拼命想逃离。
这两年有关少数族裔的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了。
从边疆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来到北京,我发现其实少数族裔问题,就是差异问题,歧视与否,就是能不能接受彼此的差异。
班上的藏族同学对自己的身份经常有过激反应,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的时候她挑的刺我让我疑惑了很久,前几天我才明白,我成长的地方少数民族没什么特别的,但她一路走来,因为自己少数民族身份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但这是你身上流的血啊,这血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不仅是维持你生存所必需的氧气,还有你一生逃脱不了的宿命。
这个宿命在电影里的表现是萨米人的身份。
她又矮又胖,不能去正常的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被瑞典男孩霸凌,被瑞典医生扒光像动物一样被拍照研究。
Ella Marja很聪明也很努力,努力把瑞典话学好,有机会去到优雅美丽的女老师的房间,第一次触摸到精美的诗集,第一次用画着漂亮花纹的陶瓷杯子喝咖啡,这些花又美丽又脆弱,在她的家乡——极度严寒的北极圈附近,根本存活不下来。
但她根本想不到这么多,她只是兴奋,只是为自己能和从小向往的文明这么近感到兴奋,笨拙地模仿女老师拿杯子的动作,那微微翘起的粗粗的小拇指,让我看到刚到北京的我,带着好奇、胆怯和笨拙接触这样那样的新事物。
她太渴望改变命运了,像古今中外千百年来无数的懵懂少女一样,渴望外面的世界,渴望漂亮的衣服和英俊的王子。
她是灰姑娘,但她没有仙女教母,只能自己去偷花裙子,跑到湖边洗了洗自己的身子,混到了瑞典人的舞会上。
王子Niklas出场了,他太完美了,完美到让人觉得残忍。
身姿挺拔、英俊潇洒、谈吐风趣的他到底是为什么会看上矮胖胆怯的Ella Marja,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他们共舞的场景并不和谐,因为他们看上去一点也不般配。
如Ella Marja和她向往的生活一样不般配。
就像我高中喜欢那个男生,他在我的眼里也是身姿挺拔、英俊潇洒、谈吐风趣,反正喜欢他的这一年半我一直都怀着自卑的态度面对他。
这些少女小心事都是再普通不过的。
最后我表白失败也才是标准的结局。
但表白有千千万万种形态,打电话过去表白的时候表白对象在桑拿(凭我对他的了解,这里的桑拿二字可以诠释出很多含义)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了吧。
好在我在这一年半里因为他多多少少做出了一些改变,正面的也不少。
至于天天上课偷看他耽误的学业,应该也怪不到他头上。
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没有仙女教母,但有恶毒宿管,她被抓回去,她被毒打,她逃跑。
她和妹妹决裂,和族人决裂,但她有什么地方可去,她只能去找Niklas。
我之前发过一条微博说“北欧人真是天生长得一副well educated/我们不歧视你 你和我们呆在一起你自己就开始歧视你自己的样子”。
就是在这一段,太血淋林了,人家什么坏事都没做,人家还很礼貌的好心收留了你几天,你跑到人家生日宴会上借钱人家还邀请你唱歌。
但我觉得太可怕了,Niklas那些同学,一个个脸庞精致、匀称修长,在大学里念着人类学生物学种种看上去高大上的专业,却像围观动物一样欣赏Ella Marja唱Yoik。
太残酷了,太可怕了。
但这种出身、阶级的对比与讽刺,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主题,不仅在《萨米之血》里被残忍地展现,《芳华》也把这种残酷生生抛到你面前,当然,我们自己也天天面对这些。
我来北京以后,才发现,北京同学,卷子简单又怎么样,人家受的教育的质量就是比你好,人家就是比你有钱比你见识广。
有人大学以前从来没上过信息课,北京同学用电脑记笔记画图画表咔咔咔的,做出来又工整又漂亮;有人操着不知道哪里的口音讲着没人听得懂的英语,北京同学天天上课睡觉最后口语考试还是秒杀你;有人从小到大只穿一身校服,来了大学不知道怎么打扮自己,沉浸在幼稚土气大红大绿的衣服里不能自拔,北京同学高中拍毕业照穿的都是礼服。
落差太大了,但有的是更大的落差。
后面还有更多类似的镜头和描写,就此打住吧。
其实我和Ella Marja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相似之处,但我还是很感动,大概是因为北京实在是太冷了吧。
我又冷又孤独,她也是。
9 ) 一个关于身体规训的故事
萨米人,是北欧地区的原住民,今天瑞典的少数民族。
观影的多数人和我一样,在之前没见过甚至没听过这样的一个民族。
可是这个故事显然给了很多人巨大的触动。
是什么让我们对一个萨米女孩的经历产生的兴趣?
这个故事究竟触及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哪些角落?
来自来自不同背景的观众,似乎都在这个故事里发现了让自己有些困惑的问题,关于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或者说,身体的认同。
如何面对主流文化?
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
一个人又是怎样在强势文化面前逐渐的低头?
影片通过一个萨米少数民族女孩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关于身体的规训的范本,赤裸裸的展现了一个强权文化的身体规训的手段。
而对于来自异族的女主,一步步在屈服于这样一种文化,让故事弥漫着忧伤的味道。
身为萨米人的女主,童年在族群里用萨米人的方式生活,她割下驯鹿的耳朵,说‘它是你的了’。
这是驯服动物的仪式,通过对于身体的侵犯,来宣告自己的占有。
那时,女主大概不曾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
唱着优美的yoik (萨米人自己的歌曲形式),女孩送妹妹上学,用自己民族的歌曲安慰心里不安的妹妹。
岁月静好。
然而一旦来到瑞典人(主流文化)创立的学校,女孩不得不在各种提醒下回望自己属于异族的身体。
在学校,学生被要求讲瑞典语背诵瑞典诗歌,学习官方所规定的一切瑞典的‘优秀的文化’。
在这其中,成绩优秀的女主开始向往所学习到的那种生活,而离她最近的瑞典女老师,则是这种优越生活的符号。
她偷跑到瑞典女老师的房间,学着老师的姿势翘起小手指优雅的喝一杯热茶。
那一刻 ,她幻想自己成为那个老师。
她自己偷着溜去聚会一定要偷穿女老师的连衣裙,甚至声称自己叫女老师的名字Chissy, 在童年的这样一次历险中,她尝试成为那个老师。
她在聚会上遇到了帅气逼人的小帅哥,大概从那时候起,她发现成为一个瑞典人可以如此美好。
然而现实打破她的憧憬, 时时刻刻拉她回到现实,正视自己具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身体 的现实。
当检查团来访问,她拼命的洗自己的头发自己的身体,希望能够退去身上的驯鹿的味道。
可当她一步步地清洗掉了与自己民族的身体符号,检查团仍旧把无情的打上了异族野蛮人的符号。
他们用卡尺丈量萨米学生的头骨,蔑视他们愚笨。
甚至强迫女学生们脱下衣服,像审视动物一样检查他们的身体。
女主作为学校里的优秀的学生,被叫出来做第一个示范。
此时看得到她眼中的挣扎,同时也满怀渴望。
当她终于接受事实,毫无尊严的带头展现自己的身体,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和这样一个羞耻的身份告别。
而另一个重要的臣服瞬间,发生在和当地一群瑞典不良少年的冲突中。
一群男孩嘲笑她有着撒米人的身体,并终于找到机会围观霸凌,男孩们残忍的割下了她的一块耳朵。
血肉模糊的她站起来,脸上有着比屈辱更复杂的内容。
此刻,不知她心中是不是浮现了她在族里割下驯鹿耳朵的那个瞬间,是不是像对驯鹿审判一样,也对自己审判说“我是你们的了”。
对于弱势族群(驯鹿)的占有驯服,萨米人选择伤害身体而强行标记占有符号,而当更“优越”的民族对的身体进行伤害和占有,她心中最终承认了被驯服的结局, 向一个优越的民族俯首称臣。
自此以后,拼尽全力,要向主流民族低头,即使被当成异类,即使得不到尊重。
女孩心理有种神奇的力量告诉她,自己想要过那种看起来优越的生活, 自己想成为那样优越的身体。
只身逃到瑞典人的城市,是她自己的一次选择, 这一路走的艰辛决绝。
而对于自己身体的审视从未停下。
瑞典人的大学看上去那么美好,女孩们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而她身材矮小敦实,站在一群白天鹅一样的女生中间,从没上过体操课的她对自己的身体大概无限惭愧,而改造自己身体的决心也空前的强烈。
女大学生们笑着让她唱 Yoik,可以体会到她心中的那种纠结。
那毕竟是一个作为异类的身体符号。
当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唱起小调,她喜欢的小帅哥就提醒,或许不需要唱那么长呢。
我想,那时候女主打定了主意要和过去的一切作告别的。
与自己民族有关的一切,在别人眼里不过是exotic的,用来戏弄取乐,却毫无尊重。
然而不知道这是不是反而激发了她的心气,宁可要去套一只驯鹿,去卖掉父亲的遗产,也要进入瑞典人的学校改造自己?
女主后来的生活不得而知,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她真的如自己所愿改造了自己的身体吗?
真的过上了那个优秀民族的优雅生活吗?
一切不得而知。
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开头和结尾的那个眼睛里写满了故事的老人。
当她垂垂老矣,回到自己的故乡,虽然还保持着拉一拉头发掩盖耳朵伤口的习惯,可是这时她心中的认同感却已经与年轻时有了差别。
几乎没有什么对白,但是她眼睛里面的幽怨与坚定却透露出太多的故事。
当她最终回到族群,她远离了瑞典人优雅的聚会,却独自来到属于萨米人的山里,奋力向山顶爬去。
当头发散乱,身体颤抖,一直拘束在异族身体规训中的她好像忽然得到了神启,在那一瞬间找回了自己属于萨米人的身体。
她矮小,她一生都在仰望。
需要仰望学校里的女教师,仰望聚会上的小帅哥,仰望大学里的女学生, 仰望关于瑞典优越民族的一切身体。
而到最后,当她回到自己的故乡,她终于她终于俯下身来奋力攀登。
仰望了一生,好像终于找回了一种尊严的生活的姿势,场外听故事的我们,最终总算感受到了回归与解放。
福柯在他精彩的《规训与惩罚》里讨论了现代社会规训‘身体’的‘高明’手段。
而影片中随处可见的身体规训正是充满了隐喻。
如何改造他们的灵魂?
只需从规训身体开始。
如何规训身体?
只需从‘自我规训’开始。
女主一生都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凝视自己的异族身体,感到低劣,感到羞耻,感到厌弃。
一系列关于身体的规训最终转化成为女主的自我规训。
年幼时那些关于身体的污名化,对于身体的物理与精神上的侵犯,都奠定了她一生向这个更为“高贵文明”的民族臣服的基础。
抛开自己曾经的一切印记,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新的他人,这是主流文化想要看到的幸运,却造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大的不幸。
个山2017年6月11日2017悉尼电影节
10 ) 萨米之血
看完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寻找自己的电影。
大地辽阔而深远,天空下,是萨米孤单的灵魂,她的一生,都在寻找,成为一个理想的自己。
可是,我们的内心,不管你走在多远,走到哪里,内心都是有归属的。
不管你承不承认,你记得的,不记得的,都是成为现在的你的一部分,我们存在于骨子里的倔犟,固执,会引领我们回归自我。
萨米是她,也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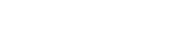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青春时,我们总要离开家乡,带着憧憬和希望;老来后,我们却要回归故乡,带着回忆和倔强。疏离的影像,失落的民族,女性化的叙事角度,伴随着歌声深入人心。
的确不是很新颖(少数派迫害,西方价值观的吞噬或者后殖民等等),但仍意义非凡
像大多数处女作一样,中后段很遗憾地失去了控制,作为period piece年代感也不是很强,不过女编导柔软的表达和前半段少数民族女孩成长的心境拍得还是相当好看
随缘下了一个片子,这个BD自带英语硬字幕,但是也学了几个新词:yoik/joik:吟唱?calf marking:给小动物剪耳朵;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题材的,看了好大一段都以为是类似于寄宿学校题材的,原来是讲北欧的racism,这个和前两天看的《苏莱曼山》类似,都是拍主流观众不会关注的群体而且确实很深入能给人带来很独特的体验,虽然有的地方还是不够流畅,特别是开头结尾,最后呼应起来发现感情很丰富但是还是铺垫不够;感觉主人公换成印第安人从“学校”跑到大城市就能直接搬到美国了;那边的大城市就是乌普萨拉,这个学校我印象很深好像总有人说这个学校性价比高北欧高福利云云,但是欧洲人反正基本上不歧视学历(英国除外),那还不如去个不那么冷热闹一点的地方好像;坐火车是不要钱吗;种族歧视哪里都一样,越偏僻的穷地方歧视越赤裸裸,到了大城市反而感觉
过程太平凡,假大空了。主题我很尊敬仅此而已。
是种平静但内心深处深深的震撼。以至于莫名其妙在互动平台连续滚动看了两遍。这种种族间、阶层间的普遍性,女性觉醒和想挣扎并深深抗拒的相似性,演员平静却极富表现力的表演,尤其是演员的先天外形条件之对比,剧情的设置,从家庭、亲情到爱情再到独立成长,没有一处不真实、自然而令人信服。看完完全被裹挟了
剧本不够扎实。
薩米人的dilemma
身份认同、意识觉醒的成长期撞上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隔阂,斩断自己,出走半生,归来时一片寂寥,这是更真实的现状。
3.5急于长大,摆脱,最终年迈回到故乡爬上山顶,镜头由老人脸上满脸的沟壑随风飘扬的白发,回望山脚下坚守了不知道多少世代的游牧族群,歧视在每个人的心里,讲的是回归、和解。
只有北欧才能拍出来的电影气质。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却没有年代感,大概童话之地不会老吧。题材新颖深刻,小女孩和老妇人双重视角下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归属问题,沉重而又安静,在所谓“进步”民族试图同化异族文化时,这究竟是人类的一种良性进化还是恶性侵略?当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响起,而确实是意料之中的那首时,我真正为萨米之血动容。拼命想要“切断”这种血脉、融入瑞典人的姐姐没有任何错,而留守故土、驯鹿为生的妹妹也做出她认为正确的选择。人类的心理是匪夷所思的,歧视问题更是复杂的,我们常常认为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口音总会因“刻板印象”而吃亏,实际上哪怕是“刻板印象”又何错之有。
倔强,抗争
好無聊⋯小朋友成長這種類型真的完全無法欣賞⋯我有罪⋯
非常北欧...克制...温吞...什么都是点到为止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故事反而没有拍透
种族歧视下的青春期叛逆少女
主题着眼于文化沙文主义,故事却略显单薄,留下来诸多想象空间/主角没有一般的曲折路径,而是拿主角妹妹做个对比仅此而已;无关人物过多,在女主之外的时间较为碎片,也许是篇幅限制;部分对话镜头和风景镜头是本片亮点。
全球的少数族裔都一般惨,但“逃离”族群身份的心态是普世的
说不上来,觉得差了一点东西……
对民族的不自信 萨米人也是悲哀 被社会当成异类真的很可怕。萨拉这一辈子就活在阴影之下 知道老了才能卸去伪装 她也没什么错 错的还是大环境。
哎啦妈呀扭啊扭啊扭啊 年老部分和回忆的转折太生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