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之子》剧情介绍
身为纳粹集中营“特遣队”队员的犹太人索尔(Géza Röhrig饰),是一名被迫负责处理死尸的囚犯,某日在例行清理毒气室遇难者尸体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儿子”的遗体,他从此改变了苟且度日的生活,做出了人生中最大胆的决定——拼死夺回“儿子”的尸体,并找到一位犹太牧师为“儿子”下葬。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亡骸游戏荒岛甜心浴血记者黑子的篮球冬季杯总集篇~影与光~理发店情缘破毒海诗行动俗女养成记2极限17滑魂街角少年第二季新网球王子OVAvsGenius10晚上10点到凌晨3点父子神探之千年咒赛艇男孩戏剧世界鬼太郎诞生:咯咯咯之谜华颐:吞噬怪物的孩子失眠男女爱我中华塞涅卡烈火男儿之队长的故事魔法禁书目录茵蒂克丝炭爱情顾问老将新生普尔万蒂人类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毒练歌房深海蛇难滚动吧小齿轮
《索尔之子》长篇影评
1 ) 《索尔之子》我的灵魂我做主
昨天无意中从电视上看到这部电影,可能换做几年前我是看不完这部电影的,整个电影由于全是浅焦镜头,再加上嘈杂的吆喝对话,没有背景音乐,从视觉上和听觉上几乎无享受可言,沉闷、沉闷、一直沉闷,看到一半时我突然感觉这部电影恐怕没有大部分电影的甜蜜结局,至少主人公可以逃脱,但我丝毫看不出导演要放主人公一条生路,我所要做的是做好准备面对所有的希望破灭。
既然有此想法,当然欣赏一个电影的角度必须发生改变,既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欣赏死亡吧,整个影片据说都是手持摄影机拍摄的,焦点都是在索尔的前脸、侧脸、和后脑勺上,而焦点之外的模糊背景中发生了无数的故事,有无数的犹太人或被诱骗以让他们工作的名义或被强行赶入毒气室,有枪声和哭喊声,有特遣队忙碌的搬运尸体或搜集衣服中的钱财,有特遣队的人暗中勒索金钱贿赂警卫,有军容整洁仪容气扬的德国官兵,有特遣队员把堆积如山的骨灰忘河里锹,这些镜头都被索尔偏执找拉比给他”儿子“安葬的故事串联在一起。
索尔其实是一具死了的活人,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纳粹需要活人来处理死人,而活人其实也是死人,只是需要他们能动而已。
索尔是纳粹集中营中杀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所谓零件就是随时可以被替换,在此我不想讨论索尔是否是自愿干这事,反正不干随时可以换人干,在他机械般的被动中,出现了两次有人在毒气室里未被杀死的情况,第一次是一个女孩,第二次是个男孩,被抬出后随即被军医掐死,这个过程正好被在边上的索尔看到。
于是索尔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找个拉比给这个男孩一个正确的下葬方式。
在犹太教中拉比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职责是主持礼拜,参加婚礼、受诫礼、丧礼、割礼等。
但是要在集中营中要找个拉比来给这个男孩下葬谈何容易,何况这个男孩需要被解剖并且资料要归档,退一步说即使不被解剖也轮不到下葬,烧掉才是允许的归属。
索尔找到了第一个拉比,然而这个拉比不答应帮忙索尔,随即走向河中准备让纳粹开枪打死。
这个场景有人评价是索尔害死了他,我倒觉得有另外一种理解,这个拉比既然能从容走向河中被打死,索尔救了他上来他面无表情拒绝回答问题,感受不到气愤、害怕,而是像一个活的东西,即使是有些动物在这种情况可能也会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在这个拉比身上看不到,说明他已毫无求生欲望。
但他为什么宁可现在就死而不帮忙索尔?
他作为一个拉比,有义务也有资格为犹太教徒举行下葬仪式。
拉比已经放弃了信仰,不再相信上帝。
在寻找拉比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收集纳粹集中营杀人的证据,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另一件是暴动越狱的事情,他被要求去女工集中营拿包裹(炸药),这是一件求生的事情。
然而索尔至始至终都是个局外人,他全身心在做的事是寻找拉比。
很不幸第一件事没有成功,第二件事情他弄丢了包裹。
看到这里,我还是抑制不住生气,心里在怒骂他是孬种,他搞砸了一件又一件事情,是猪一样的队友,是个自私的人,是个失败者。
他从女囚那里拿到包裹时,女囚拉了一下他的手,并喊了他名字(不知是不是他老婆,但是他们没生儿子),他还是面无表情,很快就离开时,离开的时候纳粹警卫嘲笑的说了一句“这么快就完事啦”,不知这段是不是对亲情的描述。
终于在一群即将被处决的人中找到一个拉比,为了救出拉比,他将自己的工作服给拉比穿上,而自己差点被拉去处决。
之后因为一份70人的待处决名单,集中营发生了暴动,在第一视角的杀戮和逃跑镜头中,索尔扛着尸体,逼着拉比举行仪式,第一次在集中营内,因为暴动而放弃,索尔扛着尸体逃到树林继续寻找机会给“儿子”下葬,在拉比失言的诵经中,假拉比的身份暴露了,这时纳粹警犬逼近,索尔只好再次扛起尸体走入河中逃走,然而不幸的是尸体却随飘走了,索尔试图去拉回尸体,但是被假拉比救上岸,之后假拉比像拉着痴呆者一样拉着索尔逃亡。
他们最后逃到一个建筑物中,在讨论怎么办,有个清楚的声音,要找到游击队,他们有武器,有食物,要战斗,在其他人的讨论中,索尔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从门缝看过,之后就跑开了,之后索尔脸上出现了全剧第一次表情变化,慢慢展现了笑容,少年跑开后,一群纳粹荷枪实弹的纳粹士兵走向建筑物,枪声响起,结局可想而知。
我想解读一下索尔最后的笑容,是不是因为看见了少年或者看到了幻觉中的少年呢,我觉得是对他”儿子“尸体的解决方式的满意,虽然没有按照犹太教的方式让拉比指导正确的下葬,但是也没有被烧掉,而是随河水中飘走了,从某种意义来说已经获得了自由。
很奇怪,随着最后结果毫无悬念的枪声响起,我似乎得到了解脱,内心期盼的英雄没有出现,期盼的奇迹也没有发生,只有死亡的结局。
我觉得索尔是我、是你、是我们身边可能的每个人,蝇营狗苟的活着,偶尔为某件在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的事情疯狂的执着,甚至伤害到其他人,而自己的结局也是如同猪狗一样的死掉。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英雄,很多人名垂青史,但是更多的人是索尔,所以那最后的枪声是悲怆的,我们的每个人无时不刻在经受着失败和死亡。
但是,即使全剧都弥漫着死亡,仍能看到希望,有身为囚徒的医生,有努力保持某种平衡的警卫,有努力求生的暴动者,有假拉比的水中救援和路上搀扶,在我看来全局最给人的希望是那件最无意义的事情,索尔冒着各种风险历经千辛万苦想要举行下葬仪式的尸体随河水飘走,以及索尔那超然的微笑。
即使死亡无法逃脱,我依然保持理想追求的尊严。
导演拉斯洛·杰莱斯是勇敢的,没有背景音乐,没有英雄、没有雄伟场面、而且是没有生的结局,然而就这样一部电影却让人不禁细细回想品味,越是回想越是佩服导演的勇气,感谢《索尔之子》。
2 ) 《索尔之子》的正确打开方式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颁给了匈牙利的新锐导演拉斯洛•杰莱斯的影片《索尔之子》。
这部影片讲述了二战时期,发生在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一个故事,剧情非常简单,男主角索尔作为特遣队的一员,在一次执行毒气屠杀的工作之后,清理尸体之时,意外的发现了自己“儿子”的尸体,接下来影片便围绕着索尔如何运出尸体,并想尽办法找到一位“拉比”完成葬礼的仪式这样一个内容来展开。
为什么《索尔之子》能够获奖?
影片大部分片段都采取第一视角的跟拍手法,并且对于主角视野之外的景深做了浅化模糊处理,加上压抑的气氛、嘈杂的背景声音,以及晃动镜头,整个影片呈现的观影体验极为让人不适。
另外,剧情上的晦涩,逻辑上的难以理解,都严重影响影片的接受程度,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部影片会获奖?
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一部犹太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么?
确实有这个因素,大屠杀的题材作为一种在极端的环境下探讨人性的方式,很值得关注,也很容易赢得评委会的欢心,例如1999年第7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美丽人生》以及鼎鼎大名的第66届金像奖得主,《辛德勒的名单》,都是这样的例子。
但是也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珠玉在前,我们不禁要问,同样的题材,《索尔之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能够冲破前人的藩篱,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探讨和反思这场人性的浩劫?
简单的说,如果把《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定义关于“生”和“希望”的探讨,那么相反的,《索尔之子》则探讨了关于“死亡”和“信仰的破灭”。
这就是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并不打算在其中寻找光明和意义,挖掘人性中的美好,只是无声的,压抑的,向观众展示面对着死亡的绝望和人性的空洞,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后的挣扎。
是的,绝望,只有绝望,泯灭人性的绝望。
如果我们去查一下数据就会发现,在二战期间,纳粹所屠杀的犹太人总计有700多万之众,但这还只是不完全的统计,还有更多的屠杀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资料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确定。
而最终生存下来的人数呢?
和这个触目惊心的700多万相比,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少到连让整个人类回望历史的时候感到些许聊以安慰都是不能够的。
所以,如果将这场屠杀比作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黑洞的话,所有没经历过的人在讲诉这一段时候,都应该慎之又慎,问问自己,有什么资格替那些遇难的冤魂在这无边的黑暗之中寻找光明?
黑洞就是黑洞,它能够吞噬掉一切,包括希望,包括光明。
在一段根本不存在任何光明的历史当中讴歌人性不灭,不过是自欺欺人,是给活人的慰藉。
而只有正视残酷的真相,承认上帝的死亡,才是对遇难者们应的祭奠。
出于这一点,应该说索尔之子能够获得最佳外语片奖,实至名归。
很多人在观影的时候会觉得看不懂,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索尔为了安葬自己的“儿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同胞,耽误反抗者的逃跑计划,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换一位“拉比”的性命,只为完成犹太人的葬礼仪式。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影片的后半段,有人拆穿了索尔的谎言,说他没有儿子,那个男孩根本不是他的儿子。
这就更加让人不解甚至气愤了,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孩,为什么要这么做?
红色的十字首先,让我们先暂且把这些疑问搁置,谈一谈影片当中的一个细节,索尔身后衣服上的红色十字。
这个十字在影片的一开场便出现了,并且在之后大量的跟拍镜头下反复的出现,在影片灰暗沉闷的色调中尤为触目和明显。
那么这个红色的十字是什意思呢?
其实,这个红色十字画的是一个靶子,目的是一旦有人逃跑,能够便于党卫军军官瞄准射杀。
不只是索尔,所有特遣队的人都穿着这样的衣服。
这是一个巨大的,恐怖的标志,在他们的身后如影随形,不断的提醒着他们这摆脱不掉的死亡阴影。
麻木的脸那么索尔畏惧死亡么?
我想是的,至少在一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是畏惧。
所以他甘愿成为特遣队的一员,成为纳粹屠杀自己同胞的工具和帮凶,只为了换取多四个月的生命。
但是现在呢?当四个月的期限逐渐逼近,当亲手处理过了成山的尸体和骨灰,索尔剩下的只有一张麻木的脸。
这种麻木可以说是人在极端环境下的一种应急自我保护机制,为了避免自己的崩溃,他关闭了自己的情感。
影片镜头的视角便是索尔的视角,所以我们看到,远处被拖着运走的一句句赤裸死亡的肉体,都是失焦的,这样的人间炼狱是如此令人难以理解,所以他选择了不去想,不去看。
神迹!
救赎!
可是,麻木的索尔毕竟无法关闭自己的全部人性。
他只是想要逃避,而现实有的时候却不允许他逃避。
被迫的听着毒气室里面的哀嚎,不动声色的表情下难掩那死亡的寂静在心里造成的巨大空洞,而且这空洞会在索尔的人性殊死抵抗的刹那传来一阵阵哀嚎的回响。
也就是在这一时刻,神迹出现了。
那个男孩,在毒气室中幸存了!
犹太人相信人死后可以复生,不管这男孩是神的启示还是幸免于难,这一刻索尔都认定了这是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的机会。
不过男孩还是死了,被纳粹党卫军捂死了,这时候我们看到索尔麻木的表情第一次有了变化。
也是从这一刻起,索尔的人性开始苏醒,他要安葬这个男孩,用犹太人的方式,因为这男孩并非死于自己之手,他有这个资格!
到底是不是索尔的儿子分析到这里,我想可以回答这男孩到底是不是索尔的儿子这个问题了。
我的答案是不是的。
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就像我以上所说的,索尔安葬男孩的行为是一种自我救赎,即使男孩不是他的儿子,他的种种行为也能够说得通;其次,影片中后来当有人提出质疑说那根本不是你的儿子,索尔辩称是自己的私生子,而当那人继续追问他上一次见到“他儿子”的时间时,索尔却沉默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个谎言太经不起推敲;再次,索尔对于男孩的称呼也说明了问题,如果真的是他的儿子,他就直接称呼为“我儿子”就好了了,而不是影片中的“这个男孩”那样的称呼。
偏执的仪式那么,为什么索尔对安葬的形式如此偏执,甚至耽误了革命者的逃跑计划?
这是因为索尔根本就没想过要逃跑,后来他跟着大伙一起跑出来也不过仍然是为了完成那个死亡的仪式。
在整个影片中,索尔对于逃跑计划的态度都是漠不关心的,甚至主动要求完成偷拍任务也不过是为了找机会出去寻找“拉比”。
为什么会这样?
是什么让他放弃了求生的本能?
我想是因为在本质上,他对自己,甚至对所有特遣队的人都是厌恶的。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可以体现这种厌恶:当有人谴责说他“为了一个死人牺牲掉活人”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们早就已经死了”。
是的,在索尔的心里,他们这些人早已经是行尸走肉了。
他们是受害者没错,但同时也是刽子手,是纳粹的帮凶,为了苟且偷生,屠杀自己的同胞,他们作为人的道德、尊严,早就在处理那些成堆的尸体和骨灰的时候,别烈火焚尽,随风飘散,消逝在河流的远方,不见踪影。
所以,生,对于索尔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侥幸逃脱了又如何,到处都是纳粹的统治,根本就无处可去,即使找到栖身之所,灵魂又该何所依归?
唯一的救赎,就是通过那一场葬礼的仪式来洗刷自己的灵魂,找回自己的人性,让自己在死亡降临的那一刻找回作为人最基本的东西。
仪式是是情感的宣泄,是悼念的表达。
人类,是唯一为死亡举行仪式的生物,这也是索尔所能做的唯一能将自己和动物区别开的一件事,所以他重视这个仪式,如此的偏执也就不足为怪。
所以他不关心活下来,只关心死的救赎。
得不到的救赎借用戛纳电影节对这部影片的评语,“影片努力呈现着死亡葬礼和死亡工厂的对比、仪式和机械的对比,祷告与吵杂的对比。
当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在这个地狱的最底层,索尔心中的声音告诉他:你必须活下去,完成这个对你来说充满意义的行为,这是一种属于人类的、绵延已久的、神圣的意义。
这种行为处在所有人类和所有宗教的起点,那就是--祭拜死者”。
然而,索尔的救赎实现了么?
并没有。
“拉比”是假的,男孩最终也没有入土为安。
结尾中出现的男孩不过是索尔的想象,这黑暗中的一丝丝光亮不过是一场幻像,当绝望的枪声响彻树林,男孩也带着人类获得救赎的希望消失在密林深处,不见踪影。
3 ) 索尔之子:换一种揭露历史疮疤的方式
当揭晓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是电影《索尔之子》时,特意瞄了一眼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不是实至名归就是不出所料,好像身为局外人的观众比初出茅庐就一鸣惊人的拉斯洛·杰莱斯 (Laszlo Nemes)还要胸有成竹,问题是颁奖前国内99.9%的观众想必压根就没看过这片,都眼巴巴的盼着下崽,那为何能如此笃定?
首先这片是匈牙利导演杰莱斯第一部正式的长片作品(去年涌现出了很多令人惊艳的处女作,有种井喷的势态),从去年开始就在电影节和颁奖季一路过关斩将,将68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73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妥妥的收入囊中,在赞誉声和质疑声的“轮番轰炸”下,赢得不少知名度的同时,以轻松的姿态毫无悬念的杀进了奥斯卡(当然,对手的实力整体也不是太强)。
有过良好教育的杰莱斯在大神贝拉·塔尔( Béla Tarr)拍摄电影《来自伦敦的男子》时,也跟着学习,受教了不少,掌握了什么才是电影的真正价值,起点较高,对他会抱有一定的期待。
重点还在于随着热度的提升,观众对这片都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二战的背景,集中营的环境,受害的犹太人,被调动起兴趣的大伙会好奇杰莱斯会以何种方式或手法处理一个容易惹上麻烦和先入为主的敏感题材,这明显是一个很多资深老将都不敢轻易尝试的烫手山芋,更可况是一个影坛新人,加上之前还有过不少经典的成功先例,而杰莱斯并没有照搬前辈那套具有思想导向、趋向正确和理所应当的拍摄模式,而是通过别具一格的形式,以绝对单一主体化的设定和具有内部精神审视的构思走进了当年那段黑暗而惨烈的历史。
<图片1>杰莱斯完全不好近年来大热的“炫技镜头”这口,而是以一种近距离随身跟拍的独特方式(难以诱发好感的观感),跟着索尔的脚步和身影游走在集中营的里里外外,感受暗无天日了无希望的炼狱处境,见证他和大量犹太人的不公遭遇,直视当年惨不忍睹的死亡流程,索尔是片中第一也是唯一的视角,全片基本围绕他前后视角的切换进行(撇开最后不谈),没有刻意放大残酷而壮观的悲剧性色彩,但“虚设”下赤裸裸的场景(血迹、尸体等)和压抑紧绷的氛围足以让人揪心难耐,加上紧密相伴带有强迫性的牵引感,受周遭环境的影响,杰莱斯有意将镜头做虚恍和模糊上的视觉化处理,带有一种死期将至富含悲剧因素的不安定感和危机感,看着很煎熬,这片才107分钟,却显得很漫长,中途好几次选择暂停,喝口水才能继续,杰莱斯有效的将观众和索尔捆绑在了一起,具有引领性的带着我们,仿佛经历了一场被动而异常不爽的观影体验。
这片完全摒弃了配乐的渲染和烘托,取而代之的是真实而直接的音效,受难的犹太人凄惨悲壮的喊叫声,以及枪林弹雨制造出的混乱决绝的声响,杰莱斯利用很多画外音的庞杂介入来丰富被局限起来的情境,影片一开始不久就上演了一段将大批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戏码,门内传来了惨烈痛苦的呐喊声和本能求生的敲打声,站在门外的是麻木的索尔,那一刻足够以“先下手为强”为形容,强烈的震慑了观众一把,画面的效果的确是只有采用胶片时才能体现出的质感,在规整的画幅比例中包裹着一种持续膨胀的难受劲,凝重深沉的色调契合影片的主题,使全片始终沉溺在一种深刻绝望的意向中,可能也是受到塔尔的影响,对数码完全不感冒甚至有点抵制倾向的杰莱斯,避免了电影先进的技术层面会对影像本身形成的必然干扰(资金也有限),将观众的关注点全身心的聚集在剧情本身和历史背景上。
<图片2>可能让观众有点万万没想到的是扮演索尔的并非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而是匈牙利的著名诗人格扎·罗里格(Géza Röhrig),戏里戏外联系起来捉摸一番会感觉挺有意思,片中有不少索尔的特写镜头,令人印象深刻,坚定刚毅的眼神,雕刻般冷峻的面部线条,僵硬木讷的神情,嘶哑的声线,他自然形象不求什么高超演技的表现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影史上也有不少大师级的导演早已用牛掰的作品力证过了业余演员的好处,一种对影像整体诉求更为有利的塑造性和存在感,罗里格参演的初衷主要是对索尔一意孤行地举动和个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这也是让很多观众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就像片中索尔的同伴说的:“你居然为了一个死人弃活人于不顾”,光看一句话含糊带过的剧情简介,让人很难想象杰莱斯别具匠心的大胆意图,可能不少人会觉得这或许又是部类似于《美丽人生》将背景设置在特殊时期讲述感人至深父子情的故事,非也,恰恰相反。
在毒气室发现还有一口气最后被弄死的男孩是否是索尔的儿子,可以从后来影片给出的线索(索尔和同伴的对话)中找到答案,而影片的主要故事脉络就是围绕着索尔抱着难解的执念一心一意近乎极端的想要埋葬“儿子”的过程展开,对索尔的举动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而我从索尔身上看到是纯粹以当局者的角度出发,体会更多是失去所有希望后的一种自我麻痹,是在什么也不可能实现完全丧失了生存活力的决绝境地中,在弥漫着杀戮的血腥味和死亡气息的空间中,借由一种合乎道理的情感理由(维系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牵系,即便也许是索尔一厢情愿给臆想出来的关系),抓到一丝“力所能及内还能完成的神圣使命和目标”,捕获关于活着的微薄知觉,而未曾经历过的我们以现实的目光投射过去,或许会觉得索尔的做法是荒谬而愚蠢的,但对于他来说这是时日不多中的他所能触犯的权限中唯一能出于自我意愿的行动力。
<图片3>身为纳粹集中营囚犯分遣队的一员,给予索尔的唯一权限不过是能多活一些时间而已,它的作用就像是镶嵌在这个屠杀犹太人的机械大本营中一个等死的运转零件,集中营囚犯分遣队要做的就是无限循环的将同胞送进毒气室,处理他们的生后物,清理他们裸露的尸体、斑斑血迹和焚烧后的骨灰,然后自己也会陆续走上相同模式的死路,这片其实可以分为两路来看,一边是想要走体面流程神圣埋葬“儿子”的索尔,从解剖室偷出尸体,近乎疯狂的到处寻找拉比,不惜丧命也要从万人坑里拉回个冒名顶替的拉比为“儿子”念祷文,即便最后大难临头也要偏执的将埋葬进行到底,而另一边则是囚犯分遣队欲计划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冒死杀出重围,需要借助索尔的帮助,结果却被一门心思葬“儿子”的他给搞砸了。
问题就来了,为何索尔要这么不可理喻的死脑经?
在我们既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评判标准中会觉得分遣队的行动目的才是合理的,但在这个人性逐渐消失殆尽和终日与死神打交道的环境中,面对完全不合理地残忍对待又怎么会有产生合理性乐观结果的可能?
就像我之前写的索尔这种行动力的驱使或许能让他感受到仅有的呼吸和存在,在这个浸透了死亡气息的大熔炉中还能体会到自己的潜在作用,寻获从纳粹杀人如麻的机械式运转中挣脱出来得以短暂喘息的机会,那为何索尔不卖力的为同伴效力,反倒拖他们的后腿,基本没怎么上心的索尔就像是从一种被黑暗扭曲的麻痹状态过度到了另一种被自我麻痹的驱动中,尽全力不管不顾的完成他认为还能体现出丝丝内在价值的计划,记得片中索尔被同伴派去拿包裹时,回避了女孩主动的双手,他就像是在有意的隔绝和避免人与人(活)之间会触发更多没必要的动容和建立过多的感情牵连。
他内心其实也明白,同伴想要活、想要获得自由的目的不过是种自欺欺人犹如泡沫般的希望,以卵击石的后果只会是提前和死神打照面,一种怀有虚幻奢求的徒劳,一种反绝望的不切实际,看上去很鼓舞人心但本质上却毫无意义,因为至始至终摆在他们的眼前的只有一条路—死亡,最后“葬儿”不成的索尔在同伴的帮助下走进了那片开头他们从模糊的镜头中走出来的森林,看到小孩的索尔,失魂落魄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一笑,寓意深刻,仿佛在没有边际的黑暗中收获到了一刻慰藉般的闪光,伴随着枪声,结局我们了然于心,前后呼应的那片森林就像一个吊诡而绝望的轮回,最后画外音的袭来,在纳粹无情的抢下宣告着他们生命的终结,一股浓厚的悲伤气息弥漫开来,震撼过后留下的沉重余味一直萦绕在心头,久久未散。
4 ) 奥斯维辛后诗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想评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屠杀时,阿多诺的名言是注定绕不开的,他的论断,毫无疑问是复杂的,且给所有“妄图”评说大屠杀的浪漫主义形式作品们打上了不道德的标签,即便姑且暂不从同一与差异的层次来论说的话,这一论断也是对大屠杀之后关于大屠杀认识的一种侵袭。
而想评说《索尔之子》这部电影,或者说评说任何电影时,又需要从作品本身上抽离出一定距离,但《索尔之子》的形式和故事之间恰恰是缺少的就是这样一段距离,只是从电影最直观的构成方法论来说,是可以被解析的。
美学上,电影最突出的视觉母题就是长焦、虚焦搭配的小景别和浅景深跟拍,目力所及范围之内,只有在焦点处的人才能被准确识别,在故事片定性下的屠犹工厂中,死去的犹太人与大多数纳粹军官在这种形式下显然是没有被清晰拍摄的必要,摄像机紧紧地跟住犹太人派遣队中的主角索尔,影随身动,在开篇第一幕也就强调了这点,从景深处走来的索尔,直至焦点处才停下,随后摄像机才开始跟随移动。
如此的小景别和摄像机的寸步不离,潜在的理念理所当然地可以理解为观者是从索尔的内部视点来看待故事世界,也就是观者与索尔视点上的统一,即内聚焦叙事或带有其属性的叙事。
故事展开后,索尔也就是观者的“我”即与情节发展同呼吸、共命运,观者移情至索尔,进而深度共情,索尔之经历就是观者之经历,也即全知,这其间不应该存在任何索尔与观者或其中任何一方未知的事情,否则就会冲击内聚焦赖以成型的封闭性。
而形式的第一个悖论即在此产生。
因为随着故事展开,不难发现,索尔之所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与观者之所见相同,因为摄像机紧紧跟随拍摄的,只是索尔对情节中各种事件的反应,无论场内或画内发生了什么,摄像机正对角色、侧对角色亦或跟拍,受限于视觉母题形式上的景别与景深,物理形式上的空间都被压缩成观者不能亲见索尔之所见,而只见索尔。
这种十分严格地将叙述控制在人物外在言行,不透露任何外在评价,几乎毫无感情地只叙述由索尔的行为和言语所构成的一幕幕场景则又是典型的外聚焦。
于是,内聚焦的封闭性在此收到冲击,故事中必然存在着索尔知晓而观者不知晓的事情,即心理空间的不一致,两者因为形式而强行形成了视角差,也就形成了信息差,观者小于角色,也就直接促成了神秘张力的形成,归结到角色,也即索尔所谓执意“葬子”等一系列行为的动因。
而外聚焦作为一种戏剧化的叙述,又与整体形式产生另外的分裂,在《索尔之子》的视觉母题下,其焦点处索尔的必然存在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因为只要索尔在故事行进过程中出现任何意外,无论内聚焦(主观化)/外聚焦(客观化)都会立即因为失焦丧失整体视觉母题形式的合法性(跟拍构建的体验),从而导致形式崩塌,叙事与故事面临全面失位而彻底完蛋大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观者对索尔在开始阶段自然而然的移情与共情,会随着故事的逐渐展开而逐渐消减。
简言之,随着毒杀又一批犹太人的开场一幕后,索尔直到结尾其命运最终显现前都会存活的必然性跃然影像之上(这与《1917》的弊端同理),这一方面使戏剧性不在存在于人物命运的形成过程,反而转向了命运落点;另一方面因为共情消减,观者与索尔逐渐抽离,形成了离间的客观审视效果而不再戏剧化。
这两个走向中,最终命运的落点进一步直接暴露了隐藏作者的不当显形与操控,客观审视的抽离效果则形成了反讽张力,两者合起来同样也指向了索尔一系列行为的动因。
神秘张力和反讽张力都指向索尔整个系列行动的动因,也即第一幕中被毒杀的犹太人里侥幸没有马上死亡的小男孩,他让索尔回想起了怎样的过往不得而知,不过为小男孩举办一场犹太葬礼却在小男孩被德国军医扼死之后,成为了索尔首要想完成的目标,其优先级甚至高过集中营内密谋策划想要逃出生天的造反计划。
一为死的仪式,一为生的努力,我们当然知道故事的结局是并非索尔真正的孩子的小男孩沉入了湖底,索尔们虽然逃出了集中营,却也被追赶而来的德军尽数杀死在仓房之中,无论怎样都难以逃避,亦无法幸免,这就好像人即便不进集中营,也注定会死亡的命运般,这道出了大屠杀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注定死亡的旅程。
故事中的索尔无疑是理性的,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进入了集中营的人们其实早就已经死了,在一群“死了的人”之中,索尔选择为一位真正象征未来的孩子举办一场犹太葬礼,又毫无疑问是他的自由意志。
如果说身为平民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被纳粹侵占的匈牙利,不得不进入集中营是既定的命运的话,那么选择怎样死且见证怎样死则是先于这份注定的命运,那个冥冥之中身处高效率杀人工厂,侥幸晚死一会的小男孩,就仿佛是被上帝命定的先知,来告诉索尔暂且先不要着急赶赴最终的终点,他还有尚未完成使命的选择自由。
情节中索尔所作所为拖累同伴计划,甚至延误重要弹药传递等不能靠正常逻辑理解的出格行为则处处彰显着这一先后理念。
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之子》如何面对向死而生的选择才成为故事的解读肯綮,危机四伏、苟且偷生的环境中,自由意志才是索尔理性尚存,执意葬子故事的闪光之处,观者们兴许可以站在今时今日,视集体主义目标(活命)为最高的合目的性的角度,从而对索尔大加指责,却也可能从心底里里默默接受索尔所作的一切努力,这也间接证明了,实践理性正是以自由意志为先验原则才存在的,因而电影的整体主题在此呼之欲出,故事的纯然性也在此体现。
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索尔之子》极具风格化的视听语言,在形式上就直接形成了两种无法流畅转换的聚焦-内聚焦(主观化)和外聚焦(客观化),而两者的成立基础又同时指向了故事中的小男孩所引起的“葬子”行为作为源头。
可以假设,故事在此如果以神秘张力为主进行下去,观者不知道索尔行为的因由,其共情基础因而不牢靠,且会不断因为其乖张行为而降低,最后全面解构,沦为客观化的纯粹反讽,而更接近对角色愚蠢行为的直接辛辣讽刺;而故事如果以反讽张力为主延宕开展,索尔行为的因由虽然一样不得而知,观者却会客观审视的原因,渐渐意识到一系列人为阻隔的戏剧性故意作戏的尴尬之处,且反讽张力越强,神秘张力越弱,直接后果就是电影表意的自由意志沦为隐藏作者直接出手操控的失衡主题,神秘张力瓦解,结果沦为主观性的纯粹反讽,破坏了故事整体。
所以,《索尔之子》的形式总是会不自觉的自我解构,而虽然在解构之下,表意可以流露出故事本身自在的震撼,但这也实在是颇属意外之意。
且反观现在的《索尔之子》,在片尾处出现的金发日耳曼小男孩,带给了索尔极大的慰藉,摄像机跟随着这个神迹一般的小男孩离开了索尔进入了既可以收束灵魂、又能承接生命的树林,在死的仪式上,给与索尔和索尔们充分不被目睹死亡本身的挽尊,和生的努力上,小男孩延续着生命可以继续下去的救赎。
这当然是形式和解构本身赠予故事可以被最大化的浪漫主义,虽然我们很难在此给作品就打上阿多诺论断下不道德的标签,但不难想象同样的故事假设用最平实的视听语言叙述,其感染力与反思并不会有丝毫的减损,甚至会因为平实而更添现实气息,并阻隔那一丝死亡仿佛是救赎般强行关联的注脚,直面理性的核心,死亡既是虚无,生命才是实在,这其间应该有向死而生距离的同一,更应该有存在主义根基式的差异,以此观,《索尔之子》故事与形式之间越是紧紧结合的严丝合缝、毫无距离,则越是时刻证明着故事之强与形式之短。
5 ) 寓言故事
每个人对电影都有个人的理解,对于我来说,这电影小男孩的死,就像上帝的死。
男主索尔不顾自己和其他囚犯的性命,一定要为小男孩寻找牧师下葬,这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达到救赎,然而结尾的时候,其他人在水中抛弃了死去的小男孩,也即是抛弃了上帝,也导致了己方的灭亡。
以我简单的理解,这是一个寓言故事。
我觉得电影拍摄方式挺好的,我喜欢。
但我总感觉不出震撼,如果有像《钢琴家》带给我震撼,相信会更加好。
但说不定导演就是想着电影平平淡淡的好,结尾也给了人耐人寻味,都挺好。
6 ) 不可经验的经验,不可信仰的信仰
“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阿多诺这一著名的论断拒斥了一种试图用语言来简化乃至替代人类极端经验的轻巧努力。
换言之,难道有任何文字、影像可以重塑那个罪恶滔天、不可理喻的死亡屠宰场吗?
任何对奥斯威辛经验的一种虚构化模仿和创作,难道在本质上不都是一种对死者恐怖经验想当然的亵渎吗?
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可跨越经验裂缝,在此端是战后艺术家们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提起笔;而在彼端是时刻笼罩在死亡阴影中的绝望处境。
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是不可描绘、不可书写、不可重建的经验。
即使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也在无形中因褪色记忆的歧义性替代大屠杀最原初的经验。
于是,在奥斯威辛面前,所有艺术家不得不面对艺术本身的不可能,回到柏拉图摹仿论中对艺术是“绝对理念”影子的影子的流放中:似乎人类最终极的精神体验,都如禅宗当下直悟,不假文字,不落图像,不借譬喻。
而这或许也部分解释了匈牙利导演拉斯洛·杰莱斯处女作《索尔之子》的融资为何如此的困难,即使他几乎拥有一个电影界新人的完美简历(电影世家出生,法国名校毕业,贝拉·塔尔助理,三部短片在欧洲拿了一堆奖,剧本进了戛纳电影基石的写作计划)。
当然,制片人们肯定不会矫情搬出阿多诺来拒绝杰莱斯,对他们来说,大屠杀作为一个敏感题材的最大风险来自于,在“克劳德·朗兹曼恢弘巨作《浩劫》以及像《辛德勒名单》这样的奥斯卡级史诗大片之后,电影人还能如何讲述奥斯维辛?
再现这场现代人类社会的原罪呢?
”拉斯洛·杰莱斯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用摄影机重现了这种不可能。
即使你再不喜欢《索尔之子》形式,再不认同这个剧本叙事逻辑,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深思熟虑且野心勃勃的处女作,导演用一套成体系的视听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视角,重新打开了这扇地狱之门,引领观众回到那段幽暗历史之中。
《索尔之子》全片基本由长镜头构成,除了间歇性地回归到男主人公的主观镜头稍作休整之外,摄影机至始至终地聚焦在前景的男主人公头部,肩扛摄影机长时间的运动跟拍,使得整部电影演化成了一天半在集中营内部毫无喘息的暴走。
观众就像是深入了一场第三人称的射击游戏,成为了一个跟随在主人公身旁同生共死的集中营队友。
40毫米镜头下浅焦点的使用,人为地取消传统意义上景深,但这种取消,这种有限度的清晰和可见性却反过来更为尖锐指向了背景深处所发生的罪恶。
换言之,历史在镜头模糊的边缘处涌动,在镜框之外被撕开。
正是在这样一种浅焦点运动长镜头美学引领下,影片在有限的制作经费下达到了另一种震撼,它从一种极度贴近个体知觉经验的方式出发,以看似最狭小的视角却达成了最逼真的观影体验。
观众所见证的不再是上帝视角之下,一个秩序井然的屠犹工厂,而是一种从渺小个体出发的血腥记忆。
事实上,早在杰莱斯为贝拉·塔尔做助理时,他就已经开始酝酿这样一种他所谓的从恐怖“内部”观察恐怖的美学。
一本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分遣队(Sonderkommando)亲历者的回忆《灰烬中的声音》激发了他重新反思人们“观看”大屠杀的方式。
这本书是如此事无巨细描绘集中营内部的世界,他们吃饭,睡觉,领着犹太人进毒气室、万人坑,搬运、火化尸体,处理骨灰,就像是活在现代社会一个封闭的血汗工厂里,麻木而又惯性的一日又一日的挣扎下去。
直到死亡变成了存在的常态,活着反倒是一种例外。
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的规模,其组织性、系统性和批量性,也只有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发生。
但真正吸引莱杰斯恰恰是这种系统性和理性秩序反面,也就是从一种个体性、主观性的视角去重新组织这种大屠杀工厂的日常,从一种人类生存极限状态里去反思存在的深度。
而从一本回忆录出发,而不是高屋建瓴做历史的宏观陈述,似乎也正暗合历史学发展中越来越强调回忆史的趋势。
换句话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又有哪个现代人有资格高高在上俯瞰这段历史呢?
甚至更进一步说,奥斯维辛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吗?
还是每一个人此刻且在未来都将身负的芒刺,一刻不停提醒着我们人性中最恶的部分随时有可能脱缰而出。
诚然,这种视角化的确立,为影片成功奠定最坚实的形式外衣,但却并不足以真正勾勒出导演在存在意义层面所欲叩击的深度。
正如导演一再强调,像《辛德勒名单》那样的大屠杀电影,恰恰讲述的是这一历史的反面,也就是那些幸存者,那些有关于“生”的记忆;而他则试图道出大屠杀的本质,也就是“死亡”。
因为奥斯维辛没有希望,在奥斯维辛寻找人类的希望是一件一厢情愿、矫情乃至可耻的商业行为,是在抚摸人类最疼痛伤疤的同时还不适时塞给观众一颗颗化解伤口灼热感的糖果,一个背对历史乃至背叛历史的陈说;相比于几十万尸体,辛德勒的名单并不足以拯救乃至为这人性最深处的黑暗投射出任何光亮;奥斯维辛只可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黑洞,绝望蔓延其中,吞噬一切。
所以,在电影里,索尔对同伴,“我们早已死了”。
而这个死人在电影里却要冒着害死另一群活人(死人?
)的方式去安葬另一个死人,这是《索尔之子》的故事,也是身处在奥斯维辛这座活死城中唯一可能叩响存在深度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即在最不可能、最绝望的深渊也要相信拯救的决心(克尔恺郭尔)。
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之子》的重点并不在索尔为什么或如何葬子,更不在这是不是索尔的儿子,而是索尔葬子这一行为所见证的信仰之光,是在一个人类不可能存在的境地仍旧怀有信仰的圣徒列传,是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地方寻找信仰微暗的火苗。
因此,死去孩子不可能是索尔的儿子,因为任何用血缘逻辑来强化索尔行为动机的企图,用理性逻辑来指责索尔行为对其同伴的“法西斯性”,都是在用世俗理性的相对性来玷污宗教信仰的绝对性。
如果说德勒兹最具洞察力表明电影镜头具有超验主体和经验主体的双重性,而具有一种从“我”之外视角凝视世界的方式。
《索尔之子》在提供叙述历史新视角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种根本性困难。
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历经着生死考验,让人筋疲力竭的电影里,观众是作为跟拍男主人公的摄影机而进入这个地狱的。
如果说,观众买票来看电影,已经表明了他主动介入这段记忆的决心,那么创作者势必还要为摄影机运动,也就是观众视角提供某种意义上论证。
既然摄影机时刻地跟随着这个执意要葬子的索尔,这种跟随就已经潜在地要求观众对索尔行为的认可乃至于同情。
一般电影需要相当篇幅剧情来建立观众和叙事主体之间的共感。
但《索尔之子》却只是把观众十分狼狈抛到这样一种处境上,并因其形式上的要求,而导致剧作层次和深度难以充分展开。
其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已经习惯了理性思维的现代观众,通过如此有限的信息去体认电影的信仰主旨变得极其困难。
更多的观众会一二再三被世俗想法所困扰,会纠结于血缘以及索尔拖累导致同伴被加害的行为,并在这种困惑且被隔离在信仰之外的观影状态下,仍然以一种惊心动魄方式,狼狈地见证了一种微观的历史。
但对于电影里的索尔来说,当影片末尾那个看似日耳曼血统的金发孩子(波兰人)活生生出现在他的凝视中时,神迹最终得以见证,正如那个在毒气室中幸存的孩子本身所昭示的神迹一样,真正的神迹最终超越了敌我、民族乃至信仰本身,索尔得到了最终的救赎。
然而,也就是在这里,摄影机视点第一次从索尔身上移开,我们跟随着这个金发孩子的行动洞悉了故事真正的结局,也就是从信仰的世界放逐回了“上帝已死”后,理性所打翻的这个性本恶的现代社会:微茫的信仰火苗在理性荒原上顷刻覆灭,而镜头最终指向了一片空无的森林,人的痕迹最终被抹去,点滴的细雨打在树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想,这或许是前人类的自然(the nature before the human),不,这应该是人类之后的自然(the nature after the human)。
参考阅读:《正册》 x 《索尔之子》导演杰莱斯:我想讲述的是死亡「深焦」(Deep Focus)是一份成立在巴黎,成员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迷影手册,提供欧洲及北美的最新电影资讯和批评。
同时,我们也是全球各大电影节和电影工业的深度观察家。
无论您是见解独特的批评家,还是精通外语的翻译家,亦或是推广维护平台的公关好手,「深焦」都欢迎您的加入,一起雕铸最好的光影文字。
我们也会竭诚把您的劳动成果推荐给华语媒体!
欢迎订阅微信公众号 deep_focus,如有合作意向请直接在公众号留言。
7 ) 没资格谈人性,就聊聊信仰
关于二战,关于纳粹,关于集中营和屠杀,有太多艺术作品展示了。
即使是这个被反复创作的主题也依然会产生一部荣获各大奖项殊荣的作品,原因是什么?
它有什么不同?
我抱着这样的心情点开,然后经历了一场进两个小时的沉默,我突然懂得随着时代的推移,大家对战争的展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部电影讨论了一个关于埋葬和信仰的事情。
男主为了用宗教的仪式埋葬一个男孩(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是他的儿子),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一个拉比,逼他念经进行仪式。
过程中他惹了麻烦加速了同伴的死亡,最终全军覆没。
故事不算复杂,全程也没什么台词,不交代前后文,镜头就像第一视角一样一直跟着男主。
大特写,虚化背景,偶尔的环境展示都在叙述这这里就是地狱,而男主是挣扎在地狱边缘的缓刑犯。
压抑的气氛和僵硬的表情都在叙述着这里的人早就泯灭了人性扔下了道德。
但这个情况下,唯一放不下的,竟然是信仰。
犹太人和欧洲其他人的区别是宗教信仰,并非是外貌区别,所以这些饱受折磨的人的厄运来自于信仰。
也正因如此,他们愿意承受也坚持在监牢里死撑的理由也都来自于对民族的坚持和对信仰的坚守。
这是一个很难用语言描述的事情也是没有信仰的人很难共情的部分,但对信仰的执着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电影整个贯穿的就是慌乱拥挤和压抑,最令我难忘的是男主唯一的一个表情就是在结尾看到了那个男孩,他笑了一下,然后男孩跑掉了。
也许是他终于见到了神迹终于能够释然的放下包袱,找到表情的同时也找到像个人一样的自己吧。
他用技术竭尽所能的去展示的就是黑暗本身,没有美好也没有反转,颠覆大家对人性和同情的理解,刻画的是一个“反常”的人物和“反常”的行为。
但也许这才是合理的,他们本就在这样反常的环境下求生,难道还能指望里面的人几个月几年之后还正常吗?
也正是在对死亡和人体的麻木的衬托下,才显得这一刻的信仰有多执拗吧。
8 ) 失败的救赎
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看的最一头雾水的一部电影。
不是什么专业观众只觉得各方面都不算惊艳,完全是为了得奖而这么拍的一部强行装逼的片子。
个人理解故事就是一个被送到集中营干活的囚犯在四个月的集中营的生活里,精神和信仰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看到毒气室中活下来的孩子依旧被纳粹执行了死刑意识自己终究逃不过死刑,所以急于寻找拉比给孩子也给自己寻找精神和信仰的寄托的故事。
所以主角从头到尾到不关心同伴的起义、不关心他人的死活、不关心除了拉比外的其他犹太人受害者,他自己已经疯魔了。
是个无法苟同主角价值观的电影,最后他的执着没有帮助他找到真的拉比,只是加快了同伴的死亡,只能寄望于别人或者来世。
电影整体压抑,从拍摄手法上,大量的浅焦和跟随拍摄看的眼晕;看评价很多评价里说背景和背景对白都赞,但电影节完全没有翻译,呵呵!
只是集齐了二战、纳粹、剑走偏锋的拍摄手法来召唤奖项的片子,而且,没有看懂结局,差评!
👿
9 ) 索爾之子:俱足力量的形式
在這之前,這部電影的預告片用了亨利.普賽爾的音樂"What power art thou?
"你是什麼力量?
那麼,是什麼力量讓索爾正視/行動/導致這一個作為?
這部電影發生一個行為,一個行為發生在這部電影:一個猶太人在集中營中,找到了自己的兒子,他決定為他辦正式的葬禮。
就這樣,故事兩三句即可交代。
不過導演已經提示了,故事中正式葬禮為最終目標,而這是一只形式,所以這是部形式先行的電影(不過有趣的是這形式大膽地最終沒有被完成)。
那麼,回到上述的問題,是什麼力量?
其力量就藏於他的形式上/表現手法。
其實我認為時間空間在這部電影比較中庸點(不過當然還是有他的歷史寓言),《索爾之子》實是在叩問著我們:是什麼力量驅使著我們?
為什麼我們要受苦?
【宿命與歷史重現】 影片一開始,就出現了一個專有名詞「集中營工作隊」他們一般由猶太人組成,被德國編為特別分隊,重點在後面這句:「他們比一般囚犯多工作幾個月,然後被殺。
」,這已經點出了結局,死亡本是全體存在的宿命,而在生與死的中間更是苦難,苦難中,歷史之輪仍在轉動。
接著畫面模糊地出現,接著漸漸清晰,記憶著歷史的構成,我們觀眾追隨索爾的視角,他的歷史,就是當大量哀號從毒氣室湧出,人已不再身為人而死。
【調度與影像】 通常場面調度算是角色做出了選擇,進入下一個空間觀測,但可怕的是在這集中營中,這部電影的自由意志只是種假象,納粹不過是一種環境,索爾不是壓迫著生存,就是被自己的執念所擾。
調度在扭曲的群像與歇斯底里的個人行為中。
而鏡框之內能看到模糊的地獄,之外是一種抹消,像是屍體、文件、衣服等等。
長鏡頭、手持皆是一種不斷受難、不安之旨意。
最後索爾的凝視與特寫的放大,我猛然讀到兩個訊息:「他將死去,他已死去。
」,這臉孔說出了歷史,過去的事才正要發生。
【人性】 其實看到最後,不是救人者(拉比或神)的問題而是被救者的問題,一開始,索爾依人性評估得下葬自己的兒子(或許指的是一種人性的光),然後尋找救贖時,劇情推演讓他加入逃獄集團,一個最正視群體欲望的組織,後來以為自己找到了拉比,結果他只是人性底下想活的人,最後出現的小男孩非神也非人,是死後復活的基督。
回到這樣的人本主義的力量,從受苦步向尊嚴。
雖然個人不太喜歡此風格,但整部片被認為是藝術的話,我想這也是好的。
10 ) 艰难的《索尔之子》
我知道《索尔之子》很difficult,只是没想到这么difficult。
故事发生在地狱中心——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一名囚犯分遣队(Sonderkommando)成员索尔在一次毒气清洗后,认定了一名尸体是他的儿子,并在之后的一天半内,执着地在集中营中穿梭,试图寻找犹太拉比为之进行下葬仪式。
《索尔之子》剧本来源于一本名为《灰烬中的声音》的书。
和《辛德勒名单》的“幸存者”视角不同,《索尔之子》来自分遣队亲历者的内部视角,是已死之人的现实。
在集中营中,死亡即是日常,犹太人被集体毒杀,尸体被焚化炉烧毁,骨灰被撒进河流中。
分遣队承担了流水作业,机械式清洗着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直到几个月之后,他们也会被清洗,周而复始。
建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故事,你很难对其说不。
背上画有分遣队标识的索尔是一具行走的尸体,对一个已死之人发出批判的声音,是无理且残忍的。
因此,索尔寻找拉比的偏执,是一趟无法被驳斥的寻找救赎的旅程。
于是在电影中,就算索尔置医生安危于不顾带走尸体,或者为了一个冒牌拉比丢失同伴求生必需的炸药包,观众也只能对这种被赋予了救赎意义的行为集体失声。
本质上,这是一场居高临下的大型价值观绑架。
谁有资格去论断究竟什么才是在大屠杀中存在的正误?
我无法认同这种追求救赎的方式,因为引起这个行为本身的执念实在是难以引起我的共鸣。
失去了共鸣基础,又在戏剧冲突上表现薄弱,就电影观赏性而言(先不论及价值观),实在是无法推荐。
影片在逻辑空间上以索尔为中心进行扩散,经常以多种符号化的人影、声音重叠交替,来表现奥斯维辛内部的混乱无序。
通过肩抗摄像机拍摄,利用多组长镜头和中近景别尾随索尔,成功营造了处于“恐怖”中心的主观视角。
导演选择放弃上帝视角,通过1.33画幅比、40毫米胶片形成的狭小局促的视角空间,来逼使观众接受和认同作者视角。
在整个过程中,观众只能艰难跟随,而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参考《阿黛尔的生活》)。
在观点先行的情况下,加上手持拍摄本身引起的消极生理反应(晕眩、恶心、呕吐等),像我一样本来就持怀疑态度的观众,观看过程真的是相当痛苦。
粗略估计,在1小时47分钟内,我睡着1次,大概看了8次进度条,产生沮丧、抑郁、愤怒、掀桌等综合应激反应27次。
《索尔之子》是导演拉斯洛·奈迈施执导的长篇处女作,入围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斩获第88届小金人最佳外语片,可算是一鸣惊人。
早期拉斯洛从安东尼奥尼(意大利现实主义导演,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代表作《奇遇》《蚀》《红色沙漠》)、塔可夫斯基(俄罗斯导演,对电影语言的诗性叙事有杰出贡献,代表作《伊万的童年》《乡愁》《牺牲》)等导演的“作者电影”(Auteur Cinema)中学习。
在著名电影大师贝拉·塔尔(匈牙利导演,代表作《都灵之马》《鲸鱼马戏团》《撒旦探戈》)剧组中担任助理期间,受到不少塔尔的美学风格的影响。
拉斯洛从塔尔身上学会思考电影的方式,并在三部短片的实践中逐步摸索了自己发声的视角,最终在《索尔之子》中呈现出隔离、现实、冷静的美学风格。
当然了,《索尔之子》只不过是拉斯洛的第一部长片,说美学风格已经成型仍然言之尚早。
于我而言,《索尔之子》还显得过于形而上和符号化,来自这种语境下的表达,可能来得太过轻松了。
我比较好奇未来拉斯洛是不是会选择一个聚焦于个体的冲突来发声,想知道他在抛弃了大背景和脱离了厚重物料之后,这种糅合了Dogme 95式的粗粝现实美学是否还凑效。
观望吧。
参考阅读:《正册》 x 《索尔之子》导演杰莱斯:我想讲述的是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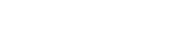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去电影院看的睡着了三次也是累。。。
绝望而自私的偏执。
反空间-影像
空洞。
不懂他偏执的含义意念是什么。因为始终处于他的第一视角,所以好像也看不见别的事和人就执着于找拉比安葬儿子。好多人的愤怒我能懂但是好像也没有意义了。可能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逃不掉所以愤怒也没那么多……
崭新的角度切入和背景虚焦跟随摄影,将大屠杀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这是影片的匠心之处。但作为一部处女作,电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生硬,无论是剧情承接,动机设置,甚至演员表演,都有一种设计感,比较机械,难以让人产生共鸣,好在电影纪实感很强烈,多少掩盖了一些缺点。总体成片质量可以,但不招人喜欢
我不喜欢这部影片,纯粹个人因素,抛开视像音响剧本主旨等宏观而专业的角度,我只觉得这样偏执,太自私。在惨绝环境中的非理性固然可以理解,为“儿子”祈祷往生的意念也固然充满人性,但他也完全不顾他人安危,强迫拉比和所有相关的人,那种强迫性,和犹太人整体被迫受到的灾难,在此类比且对比。
一句话:Saul saved the soul of his son to failure, the only possible success for him in Auschwitz. 索尔拯救儿子的灵魂终至失败,却是他在奥斯威辛唯一可能获得的成功。. 请看长评
要不是这个题材的缘故,你们会不承认这个故事其实超级无聊又毫无条理、经不起推敲?我反正是不信的。
最受不了这种无来由的执念。看到最后可烦了
#丝绸之路电影节#所有人在索尔的镜头里,都是虚焦的,只有小孩不是。全程手持摄影视角,前三十分钟不吐的话,就能亲身体验到一场残忍的集中营一日游
其实有点无感。问题在于形式上浅焦4:3的高概念是逼迫观众进入主角的,但人物动机的非理性又让观众想要远离,二者难以匹配。
其实这个题材才适合鸟人的一镜到底
看不懂这故事,不喜欢这种形式,不爽这种人,所以也只能打低分了。
主人公很蠢,为了一个死去的小孩,冒着生命危险,非要把这个小孩埋了……问题是你不认识这个小孩啊,动机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做
执念太深
死亡笼罩的集中营中男主在一个男孩尸体上寄托了所有的哀思,仿佛为这个“儿子”下葬就是解脱,在毫不停息的执念中本该有的抗争成为了插曲,没有希望的暴动和逃脱终于在一个突然出现的活生生的男孩向树林中的奔跑中延续。尽管观影过程颇难,但本片独特的近身拍摄视角和长镜头确实带来不一样的观影感受。
聪明的处女作,一箭多雕的影像风格(跟拍长镜头+浅焦),有意味但不堪回味。有处女作容易有的问题:从整体来讲没有情感内聚力,故事讲散掉,细节的串连,仅试图用影像风格粘连出情感冲击力是无法达到动人的级别的。
【7.9】男主的执念有点过头了吧。。我是没法理解。全片摄影很有特点,手持的镜头一直跟着男主,淡化了周围的事物,但是实际上感觉则更加真实压抑了。而且加上全片没有配乐,以及看上去非常真实的处决场景。。确实有些地方看的真是非常压迫。不过剧情上有点弱_(:3」∠❀)_
视觉空间上的缩小,听觉空间上的扩展,感官时间上的拉长。 8.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