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剧情介绍
1948年,凭借智利共产党支持而上台的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与共同执政的共产党人不和,进而宣布共产党非法并展开大规模的逮捕和迫害行动。诗人与参议员巴勃罗·聂鲁达公开撰文讽刺冈萨雷斯·魏地拉总统,并置自己于危险之中,不得不在国内辗转避难,最终于1949年成功逃往墨西哥。 帕布罗·拉雷恩的这部独特的传记电影聚焦这段历史,巧妙地将史实与虚拟情节混合在一起。电影中,聂鲁达被一位叫做奥斯卡·佩鲁乔诺的警探追捕,后者誓要将诗人捉拿归案,他的叙述以画外音的形式贯穿全片。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黑钱胜地第一季黑暗集会爱国还是爱我两个恋爱小茜当家冬季战争非道缉恶恋爱写真校花的贴身高手2反诈风暴我的淘气天使灵魂摆渡之风华绝代我开始自慰的那一年州官传奇一仆二主月明三更识骨寻踪第四季草莓棉花糖OVA3卷双子座计划青春时代末日之果兄弟天竺鼠车车学车篇丝路少侠上部三缺一极限父子俗女养成记邻家美人托斯塔纳天堂美丽生灵
《追捕聂鲁达》长篇影评
1 ) 诗意影片来展现聂鲁达的气质风格
【风格】难能可贵的诗意(风格)影片。
以这种诗意气质来展现聂鲁达的风格。
【视角】写人物传记,视角/切入点特别重要,影片截取了他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他被当局通缉并追捕的那一段时光。
因为电影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时间只有两小时,所以要讲述他的整个人生是不可能的。
好多传记影片,就是因此而导致失败。
“追捕聂鲁达”是的确发生的历史事实,但故事中发生的“追捕”,相信是虚构的,是个极有创意的“故事”。
影片的亮点之一,就是尽管影片选择了这么一小段经历,但是并没有因此削弱了对传主人物描述。
而是见微知著地展现了他的个性特质,价值观念和丰富多彩的个人世界:展现了作为历史名人的他,对美食、美酒和美女的享乐主义的态度,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真诚向往。
尤其是他对诗歌、爱情和革命——浓缩他整个人生的三个主题——的激情。
【人物设置】设置警察这个人物相当精妙,事实上,警察这个角色,就是聂鲁达的镜像,或他的第二人格。
通过警察(这个人物)和聂鲁达(他的追捕对象)以互文关系——相互映照、对抗和诘问——塑造了聂鲁达这个人物。
不仅通过警察对“追捕对象”的视角和认知,甚至直言这个追捕游戏本身这就是诗人创作的故事的实际演绎。
在好多侦探影片中,有此种“猫鼠游戏”,但将这种“把戏”用到‘真实’的人物传记影片中,的确是种很好创意。
【幽默讽刺的场景】影片开头,议会大厅内设置的小便池,议员们一边辩论一边小便。
以此来表现肮脏的议会政治。
【人物塑造和故事】当然,影片出彩之处,是在于它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诗意”人物,以及围绕这个人物发生的故事。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亮点——影片视角、人物设置等,都是为这个人物和故事服务的。
【真实与故事】回顾真实历史。
聂鲁达一生中,至少有过2次重要的被追捕经历,都是被当局追捕,然后被迫逃亡他国,一次是在1949年,一次是在1973年。
影片故事讲的是49年的那场追捕,是并以他最后离开智利(1949年2月),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作为结局。
影片讲述的是这次追捕事件,整个过程富有相当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但另一次,发生在1973年的那场追捕的结局,不仅没那么幸运,简直是相当血腥——以聂鲁达的死亡而告终。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由美国中情局策动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美国相近解密的文件真实了这点),当时的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政变中壮烈牺牲(相当悲壮)。
诗人态度鲜明的反对政变并准备出逃,但就在计划出逃的前一天,他“被送往”圣地亚哥的圣玛丽医院,随后就在那里去世(9月23日,即政变后12天),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前列腺癌”。
从事发当时起,对他死因的质疑就不绝于耳,更令人怀疑的是,聂鲁达在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记录完全消失,甚至连他几年前担任法国大使时的医疗记录也找不到了。
独裁政府被推翻后,当局进行过对此死因调查,2017年,智利政府表示,非自然死亡的怀疑“高度可能”是正确的。
不久,由16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终于得出结论——一致否认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百分百肯定不是。
”而此前有关媒体报道说,根据智利政府发表一份关于聂鲁达的内政部文件:“诗人被注射了一种令心跳停止的止痛药,可能导致他的死亡。
”【历史重现】影片中展现的革命浪漫主义,共产党人和底层人民(甚至土著及其领主)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
影片中对共产主义深入人心的描叙真实可信,以致远超上世纪的苏联影片和中国主旋律影片对共产主义软实力的促进、提升或增益。
2 ) 你想要的就是一场盛大的逃亡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接触到聂鲁达,都是因为上面的这首李宗荣翻译的诗。
这首诗出自聂鲁达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第十五首。
国内有一首歌,叫《分手在那个秋天》,高中的时候很火,歌曲开头有一段旁白,就是念的这首诗的一段。
似乎在某部电影里,刘亦菲也曾念过。
我初中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首诗,当时把这首诗和泰戈尔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抄在一起,前后页挨着,在那个我最最珍视的笔记本上。
后来进了大学,读了很多诗,顾城、海子、林赛宁、泰戈尔、济慈等,却不记得有再看到过聂鲁达。
刚好可以借着这部电影,去补一下。
这部影片里,频繁出现的,是同一部诗集里的第二十首。
“今夜我可以写下最哀伤的诗句 去想我并不拥有她感觉我已失去她 去聆听广阔的夜因没有她而更加广阔……”整体来说,讲述了聂鲁达的一段逃亡。
略沉闷,有些幽默,文艺味儿很足,没耐心的就算了吧。
影片从开篇的惹怒总统,总统召集警长对他实施追捕,到后来的聂鲁达逃亡,先是搬到朋友找的一个隐蔽住所,再是坐船逃到一个偏远的小镇,最后翻越雪山、一直在讲逃亡。
就像保护聂鲁达的那个小哥说的,他想要的,就是一场盛大的逃亡……开场,是一个极度混乱的场所,撒尿和喝酒在一个地方,律师和罪犯一起起舞,也许是在说明这些所谓的上层阶级,十分奢靡秽乱吧。
聂鲁达十分受人欢迎,被众人围在中间,众星捧月,大家都让他诵诗。
另一边总统因为他在媒体面前侮辱自己,找来了帅气的警长,对聂鲁达进行追捕。
聂鲁达就一直逃啊逃,警长就一直追啊追。
一开始看到聂鲁达时,觉得接受无能啊,这个肥肥胖胖的秃头胖子,怎么会是能写出那么多浪漫情诗的诗人呢?
我拒绝接受!
那个警长,保护他的那个小哥,哪个都比他帅啊!
可是看到后面,就不知不觉接受了这个设定!
警长和小哥是帅,可也正是这样,才不接地气,无法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写不出深沉的深刻的对人民的爱。
看到聂鲁达在众人之间诵读《漫歌》时,我仿佛看到了鲁迅先生,两个人同样都是作家,一个是写杂文,一个是写诗,都是在工农阶级间诵读,激起大家的斗志,为了共产党,为了民主与平等而奋斗!
两个人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做着相同的事,遥相辉映。
以前上课的时候,背鲁迅的简介,语文老师总会说,他是无产阶级战士,当时不太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战士,聂鲁达和鲁迅不就是吗?
为了共产主义,为了工薪阶级和底层人民争取权利!
片中的总统那句话说得很好,聂鲁达只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万名工人就会安静下来。
那是因为要倾听他的诗句啊,因为那一行行诗,凝聚的都是他们自己心中的疾苦!
一开始追捕的时候,聂鲁达不愿意逃跑,是啊,为什么逃跑,无产阶级光明正大,为什么要去床底下躲着?
可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传达给更多无产阶级,他还是选择了逃跑。
警长找到聂鲁达家的时候,被他们家的漂亮房子迷住,是啊,那么漂亮的房子,多少人幻想着拥有啊。
日光柔和,满屋的书架,狗安详地坐在,你在画板上涂描,我在窗前写诗,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刚刚好。
警长一次次追捕,一次次扑空,每一次聂鲁达都会给他留一本小说,上面还写几句话。
其实我也觉得,三百个士兵找聂鲁达,不可能会找不到,而且是总统下令找的,怎么会找不到?
我宁愿相信餐馆那个女侍说的那句,重要的是追捕他,而不是抓住他。
重要的是追捕的这个过程,这个追捕,让世界各地人民都知道,聂鲁达在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着。
片中的聂鲁达,常常像个孩子一样,趴在老婆怀里,让老婆为他擦拭身体,穿衣服还要调皮地吸着肚子。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大多数诗人都像是孩子,比如海子,比如我最喜欢的顾城。
因为有着孩子般的赤诚,才能写出那么真诚的诗句。
片中警长找到聂鲁达前妻,让她在广播里讨伐聂鲁达,结果前妻却一直在说聂鲁达的好话,这也说明,聂鲁达的确是个让人无法去恨的人,就连分开了,也始终念着他的好。
后半段,警长找到聂鲁达现在的妻子,妻子告诉他,他是聂鲁达虚构的,让他一直追捕聂鲁达。
也的确,他一直在追,一直追不上,直到最后。
有句话说的好,警长不可怕,就怕警长有文化。
警长自己说的,自己也有可能的艺术家!
所以他对于聂鲁达的追捕,更像是对文学对艺术的追逐。
而全片大部分旁白,也以警长的口吻娓娓道来,两人追捕与被追捕的关系也十分有意思。
至于妻子说的,聂鲁达写的小说,我暂时查不到更多线索,查到的小说只有《邮差》、《居民及希望》,似乎都不是讲追捕的故事。
最后警长死在雪山上,让人很无奈,结果最后警长又醒了过来。
警长从一开始,坚信自己是最高贵的警察机构的创建者的儿子,到后来承认,自己有可能是最底层的妓女或者工人的儿子,也是从资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的象征。
另外从开始吟诵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到后来吟诵的《漫歌》,其实聂鲁达也在转变,从爱情,到民主,从小我,走向大我。
其实我在想,是否真的像保护聂鲁达的小哥说的那样,聂鲁达想要的,就是这么一场盛大的逃亡,好让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传达到更远的地方。
影片大量旁白,显得有些杂乱,剧情很弱,有点意识流的感觉,就像是一篇散文,我看得有些不太懂,可能有些地方的理解也有误吧。
不过整部片子调色十分朦胧,如梦如诗,和影片的基调很像。
整部片子用滑稽戏谑的方式,展现了二战后,聂鲁达为无产阶级奔走的这一段动荡。
欢迎关注纯原创图文:鱼纹
3 ) 说出我的名字
这部电影的前二十分钟由于自己昏睡过去了,大致问了一下朋友前面的剧情,所以影评在完整性上肯定是不够的。
整部电影的高潮和反转就是结尾部分,所以应该不会差得太远。
诗人聂鲁达被通缉之后开始有组织的逃亡,更是作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被保护,而他本人却经常寻找某个空隙出门溜达,每次都被爱护他的人民所掩护,期间有一名执着的警察每次都只差一步就能抓住他,而聂鲁达仿佛也知道他的存在,故意在离开前留下一本自己的诗集。
前半部分气氛还是严肃紧张的,逐渐地仿佛也感受到其中一种隐隐的荒诞,从旁人之口说出聂鲁达借一场逃亡塑造自己圣人伟人的形象,也听到底层民众的质问,真正实现所谓共产主义后,是大家的生活变得和他一样,还是他变得跟大家一样。
要知道这位诗人的生活既是文艺的也是荒淫的。
一边是共产党人真实地被屠杀,另一边上演着他虚虚实实的大逃亡。
后半部份呈现一种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即将翻越雪山离开的聂鲁达忍不住高呼,附近追捕他的警察激动地呼喊着他的名字,警察被两位本地山民出卖打昏后只剩一颗子弹,在雪山中孤独死去,伴随他死亡的是大片的鲜血,还有音乐。
聂鲁达将他带回然后埋葬。
故事到这里结束的话那么就是老老实实的人物传记了。
反转在于当聂鲁达在异国他乡吟诵自己的诗歌,谈论自己的故事时,警察的旁白不断响起:说,说出我的名字。
当聂鲁达说出警察奥斯卡的名字时,棺材中的他打开了自己的双眼。
他原本就是一个存在于诗人字里行间的人物,是诗人塑造了他。
而他也不再是妓女和某个不知身份的人带到世上的孩子,他开始觉得自己是诗人的儿子,是人民的儿子(或许是说自己是一个艺术形象)。
聂鲁达的价值在于他的那些诗歌确实能够鼓舞那些在黑暗中前行的人,虽然我们无法去评价这位诗人的品行和道德。
电影精彩之处便是将诗人笔下的一个人物形象赋予真实的身份和行动,明里与诗人展开追逐,暗里却是在于之不停地对话,他阅读诗人的作品,感受到自己已经被写就的配角的无力感,注定要死去,注定要被人们所忘记,连死去的孤独和寒冷都被诗人描述得如此那么详尽,然而当诗人说出他名字的时候,他复活了,他将永远活在无数阅读者的心中。
4 ) 天真的和伤感的诗人
单纯的传记易沦为流水账,人物,特别是艺术人物的作品亦很难在作品中得到凸显。
那么对一位写情诗写到极致的诗人而言,最浪漫的表达方式无疑是让他在种种交锋中完成对自己敌人的书写,带有同情与愤怒,蔑视与慈悲,畏惧与调戏,挑战与无奈。
与爱情不同,这场追捕从开始就注定了你死我亡的结局,聂鲁达活了下来,而这个警察,妓女的儿子,国家警察头目精神上的儿子,大雪中茕茕独行,最终他倒在了这场旅途的终点,殷红的鲜血印在皑皑白雪上,恰如皓鹤夺鲜,白鹇失素。
《追捕聂鲁达》港译为《流亡诗人聂鲁达》,两个翻译也恰似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300个警察在全国搜捕一个著名的共党诗人。
追捕是站在政府的角度,非常官方。
流亡诗人多多少少有几分知识分子的傲气与洒脱。
这是我在香港电影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匆匆从九龙塘又一城赶到,在门口的摊位花掉身上最后的110元港币买了一本108元的杨德昌特刊,然而忙了三天到现在还没翻开。
刚刚落座电影就开始了,香港文化中心这个剧院挺大的,和上海的大光明相差无几,香港电影院大都屏蔽手机信号,这点真的值得学习。
在看电影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里面其实也蕴含着一种追捕,继承人对得到名画的饭店大堂经理一行人的追捕,同样一方有钱有势,一方相对弱势但得道多助,比如他们的酒店联合会。
南美的老爷车,粗粗的眉毛,古铜色的皮肤,弥漫在空气里的燥热和香气,复古华丽的服装,对欧洲拙劣的模仿,印加人的彩织披风,统一的宣传画,夸张的彩色广告,这一切的一切属于那个时代的智利,这个不像国家的国家,如同拍打在安第斯山脉上的凝固的波浪。
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意义,警察给这场追捕附加了更崇高的意味,是承担个人自我价值的所在,如果成功捕获聂鲁达那么他将功成名就,完成作为国家警察头目精神上的儿子的责任,成为总统维护国家稳定的得力助手。
在政府看来,追捕活动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他们并不希望真的抓获聂鲁达,所以总是相差一步,倘若抓获这个国民诗人他们将成为整个智利的敌人,甚至成为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敌人,但是介于聂鲁达的共党身份又必需做出追捕的姿态。
聂鲁达本人也是渴望这场追捕的,他希望这个活动成为一个盛大的全国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将成为他最伟大的诗作。
诗人成为注意力的焦点,他的声誉随着一次次追捕失败而日益高涨,自恋的诗人在即将通过边境时主动讲出了那个战斗的名字,他无法抛弃这一切,他注定要完成这场浪漫的追捕。
在原住民农场主看来,这场追捕不过是游戏一场,站在政府对立面要有趣得多,所以他们选择帮助聂鲁达,其实应该是政府倒行逆施不得民心所致,但是幽默消解了危险性,为这大胆的行为增添了几分任性与洒脱。
最好的诗人都是孩子,一身新衣的聂鲁达在街上偶遇了一个破落的小乞丐,诗人一无所有,他唯有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离开后孩子身上多了件洁白的不合身的新衣,而诗人也借此金蝉脱壳。
一如这场追捕,天真的诗人总因为自己的纯净而轻盈地逃脱。
5 ) 我本来自于字里行间,而现在我已成为有血有肉的人
如果你不喜欢《第一夫人》,那你可以试试看这部《追捕聂鲁达》。
虽然出自同一个导演帕布·罗拉雷恩之手,同样都从政治背景切入人物,同样只截取主角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同样有着灰暗的色调和别致的镜头风格,两部电影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第一夫人》仍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人物传记,除了娜塔莉·波特曼的演绎过于喧宾夺主之外,剧情显得过分平庸。
但《追捕聂鲁达》却在传记片的形式上走得更远,让这个深入人心地历史名人跳脱出书本、传记、百科地描述而不拘一格地呈现。
电影开场,镜头旋转推移跟随着聂鲁达进入参议院的洗手间。
这位共产党参议员同时也是人民最热爱的诗人对背叛左翼支持转而投靠美国的智利总统大加伐挞。
共产党受到当权派的清洗和压迫,公开批判总统的聂鲁达更是遭到总统党翼的弹劾和追捕。
总统先生对他的受欢迎大感嫉妒:“这个人只要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万名工人就会安静下来听他用那种特殊的声音朗诵这首诗”。
西装革履严肃紧绷的警察佩卢恰努适时出场。
这位自认为是警长之子的年轻人一直对聂鲁达穷追不舍,从妓院到街头,从熙攘的城市到荒芜人烟的安第斯山,却又总是让狡猾的诗人在最后关头逃脱。
所有历史都记录下聂鲁达在这段故事中不可推翻的结局——他成功逃往阿根廷,并流亡欧洲,继续歌颂他所热爱的世界。
而电影则给予佩卢恰努一个意义模糊的结局——死亡或者重生。
一个意义丰富的聂鲁达——热情洋溢的斯大林主义者,人民的宠儿我们所熟知的聂鲁达,是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者,是曾经流亡海外的政客,是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拉雷恩镜头下的聂鲁达则赋予这个人物更丰富的意义,他既热爱人民——他曾为异装成女人的男妓朗诵诗歌、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披上外套,同时也是人民的宠儿——共产党人保障他逃亡途中衣食无忧、妓女贫民替他隐匿行踪、甚至是农场主也愿意庇佑他逃脱追捕。
但他也是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捍卫者——斯大林的“情人”。
他认为只有苏维埃民主制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即使这样总统府将铺满碎花生壳和碎酒瓶,律法尽是拼写错误,但“墓地里再也不会充斥着被处决的政治犯”,却浑然不觉古拉格的噩梦真相,这是他作为诗人的天真无邪和盲目热情。
聂鲁达也是一个沉湎于酒神精神的狂欢者,从不拒绝女人们的追捧和物欲享乐。
他是舞会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轻抚白马深情朗诵“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
他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内所拥有的特权,在与醉酒的女党员的争论中以玩笑化解质疑:共产主义实现后,所有人都将与他一样“在厨房里进食,在被窝里私通。
”他是第一任妻子口中的善良人,以亲昵的口吻将第二任妻子Delia叫做“小蚂蚁”,却也经常耐不住隐居的寂寞与妓女彻夜纵酒狂欢。
拉雷恩对诗人并没有太多政治和价值偏向的判断,既没有颂扬,也没有同情,亦没有贬低,而是忠于表现他极端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诗意精神。
电影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更多是出于对这个人民宠儿的爱。
这样一个聂鲁达距离历史教科书越远,越是具有大胆而犀利的意义。
创造和被创造的佩卢恰努——在诗意上接近聂鲁达,在叙事上接近博尔赫斯然而聂鲁达并不是这部电影的唯一主角,它创造了另一个主角:追捕者奥斯卡·佩卢恰努。
这也成为电影超越传记片格局的一个突破。
在这个人物正式登场前,他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作为画外音就伴随着聂鲁达的出场一同响起,并贯穿电影始终。
来自于警察的独白动摇了以聂鲁达为主角的地位,这既是一场虚构和真实人物之间的博弈,也是虚拟和现实的共振。
佩卢恰努既是追捕事件的参与者,是捕杀共产党人的压迫者,也是画外音中冷静克制的旁观者,而成为狂热而追求自由的诗人的对立面。
他的自叙并不存在任何局限,仿佛来自于一个预知事件前因后果的幽灵,总是与先他行动一步的诗人同在,把未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以冷眼观看的讥诮观察聂鲁达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逃脱、每一次朗诵。
由佩卢恰努的画外音所带领的叙事创造了一个诗意的迷宫,让跟随他的视角探索故事的观众在观看中迷失方向。
电影通过Delia之口宣布聂鲁达对这个追捕故事的创作主权,同时也宣布警察这个人物的虚构性:“在他的剧本里,我们都围绕着主角转……他创造了你,把你写成一个可悲的警察”。
而佩卢恰努则对自己的虚构和配角属性表示不服,他说:“在我的故事中我抓住了他,我把他关进了监狱。
我会让他入睡,然后看着他做梦”。
这个故事的创作署名权究竟属于谁?
是导演和剧作者安排了主角们的命运?
还是热衷于追捕游戏的聂鲁达设计了这场盛大的逃亡?
还是立志于留名历史的野心家佩卢恰努正在改写历史?这个故事的阅读者又是谁?
是正在观看主人公命运走向的观众?
是酷爱侦探小说的聂鲁达?
还是被塑造成总统走狗,却在精神上越来越接近诗人的警察?
这场盛大的追捕和逃亡在智利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到达高潮。
从汽车到摩托再到马匹,从三百名警察的大规模搜捕到单枪匹马的追逐,佩卢恰努的境遇陡转直下落入势单力薄的劣势。
在濒临死亡之际,佩卢恰努在雪地里大声呼喊聂鲁达的名字:“巴勃罗!
巴勃罗!
”而他内心的独白却是“我一直在追逐雄鹰,却始终不会飞翔。
”聂鲁达则循着枪声,朝着他的追捕者的方向走去。
最终他们相遇了,聂鲁达这样描述他的追捕者:“是的。
我认识他,他是我的警官,我的迫害者。
”此时佩卢恰努的独白同时响起,与诗人的话语重合:“我那穿着警服的幽灵。
我梦见他,他也梦见我。
他观察我,调查我。
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你写下了雪和马匹。
你塑造了我。
”佩卢恰努的独白充满聂鲁达般的诗意和暗喻,而这个人物被创造出来的方式则在文学的意义上更接近雨果和博尔赫斯。
就像雨果笔下最伟大的逃亡者和最执着的追捕者冉阿让和沙威一样,佩卢恰努和聂鲁达彼此成就了彼此,彼此塑造了彼此。
沙威从小生活在苦役营,对警长父亲的耳濡目染与父亲的不断“言传身教”,使这个人物被打上守护制度执行命令的烙印,正是他所摆脱不掉的宿命。
沙威对于制度的维护和隐藏的恻隐之心成就了冉阿让在苦难之下的光芒,冉阿让的屡次逃遁和宽容善良,断裂了沙威作为政府工具的意义,而完善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人性意义。
而佩卢恰努则在沙威的宿命之上更进一步,开始书写自己的命运。
最初佩卢恰努身上被打下这些反派人物所共有的烙印:政权和制度的走狗、残酷而不苟言笑的警察。
然而在观察、追捕诗人的过程层中,他开始阅读诗人故意留下的侦探小说和诗集、亲吻诗人的第一任妻子、紧紧追随诗人的踪迹来到智利南部,而不断探索并丰富自身的意义。
如果说聂鲁达的政治立场和浪漫多情还有历史记录可以追溯,那么佩卢恰努则像一块空白画布一样可以被任意涂抹。
他的母亲是无名的妓女,而他父亲则有各种可能,既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既可以是仅有几个硬币的农和工人,也可以是拥有至高权利的警察局长。
佩卢恰努出身的暧昧和无迹可寻正如这个人物的虚构性一样,充满流动的意义和不确定的认同感。
他的觉醒就好比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些参与观看自己命运戏剧的观众,和那些把自己放入小说文本成为主人公叙述自己经历的听众,僭越虚构而进入现实。
在死亡之际,佩卢恰努终于挣脱了传统叙事中他应遵守的角色:伟大诗人的对立面、权力机构的抓牙、残酷无情的执法者,也跳脱聂鲁达给他设下的角色陷阱:一个局限于自我认知的可悲警察,而是亲自参与、书写、导演自己的命运悲剧,并意识到自己对于聂鲁达这个人物的反哺,而成为诗人逃亡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佩卢恰努的独白在最后道:“我本来自于字里行间,而现在我已成为有血有肉的人。
”这是导演和编剧背后的野心,他们像博尔赫斯一样想方设法让人物变成作品中虚构的读者和作者,而这种虚构终将延伸向一个更大胆的入侵现实的尝试,将虚构人物引向现实,而将观众引入小说/电影。
电影阴沉的灰蓝色调,轻快旋转的镜头和不断变换的对话场景更是促成了这种虚构和现实混淆的迷幻气质。
6 ) 在风格化和实验叙事下的传记类型突变
▲《追捕聂鲁达》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假如让王家卫来改编拍摄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大抵就会像这部《追捕聂鲁达》的模样,甚至觉得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在影片里的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极了梁朝伟。
帕布罗·拉拉因在凭《神父俱乐部》在柏林获奖后,转向人物传记题材,在2016年一口气接连推出两部作品《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并先后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和威尼斯竞赛单元。
两部作品都出其不意地获得好评,前者代表智利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者更为纳塔莉·波特曼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尽管都是以著名历史人物为描述对象,但这两部都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而是在风格化和实验叙事下的类型突变,为未来的人物传记题材开创出新的表现形式。
这部《追捕聂鲁达》跟2012年同样入围戛纳“导演双周”的《智利说不》有着类似的混淆纪实/虚构感,只不过这里不再有历史档案资料或新闻片段的嵌入,而是将人物的真实细节和虚构情节融为一体,让观众难以分辨出其模糊的界线。
▲影片中警察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酷似梁朝伟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一个黑色犯罪类型片的格局,讲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遭受政府迫害与通缉,然后走上逃亡之路的故事。
影片在开场不多久就开始陷入犯罪追捕类型片的氛围,聂鲁达被告知政府通缉的消息,介绍警察主角出场,以及到聂鲁达家中搜捕。
然而,不知不觉地这种悬疑紧张的气氛被一种魔幻迷离的诗意逐渐淡化了。
这个犯罪悬疑类型消解的关键在于用警察的画外音旁白进行叙事,让观众以为这是追捕者对逃亡者十拿九稳的猫鼠游戏。
但事实上,警察每次抵达现场却扑了个空,更对聂鲁达故意留下的一本小说着迷,情不自禁陷入到诗人的虚构世界里。
与此同时,在警察的视角叙事里,却不时浮现出聂鲁达的内心独白。
追捕者以为自己是主角,在掌握追捕的主导权,却不知已成为逃亡者的配角。
这种彻底颠倒追捕者与逃亡者的关系转换,令这场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浪漫化的细节和诗意十足的情节。
譬如聂鲁达在妓院与变性妓女唱歌跳舞,在港口城市登船时遭到警察跟踪,这些统统使得故事看起来像是诗人笔下的一场虚构的经历。
▲各种风格化的手段令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帕布罗·拉拉因偏好的逆光和滤镜、围绕人物旋转的摄影,以及在对话时的跳跃剪辑,之前已在《智利说不》和《神父俱乐部》里有所尝试,这次在作品里同样延续不变,体现出他对美学风格的统一与掌控力。
这次更出彩地透过剪辑创造出行云流水的节奏感,令情节在警察和诗人两个人物之间悠闲徜徉,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亡命追捕,而更像是读者对作家的倾慕追寻。
在高潮雪山一幕,追捕者与逃亡者在现实层面上的关系已消弭不见,警察对诗人从原本的仇视而逐渐变成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着迷;诗人原本对警察的不屑一顾,也变成像对待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般深情,并最终喊出了追捕者的名字,令其不再是配角。
在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里,两者的关系竟然是互换可逆的,这种庄周梦蝶式的设计相当惊艳,再次提升了作品的诗意空间,并与主题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契合度。
7 ) 追緝你個頭!——記《追緝聶魯達》
派來追緝聶魯達的奧斯卡探員又在喃喃自語了,在深夜陽台上露出一副愁眉苦臉,HOTEL的霓虹閃爍,他穿著整齊,叼煙。
偉大的警探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幹了什麼、要幹什麼,以及最重要的,為什麼要這樣幹。
正反兩個鏡頭,利落,有敗者的坦白,算是這部電影少數有效的畫面。
電影放完,前座阿姨冷冷抱怨我不斷磨蹭她後腦勺的膝蓋,我確實看得有點坐立難安。
阿姨抄起包走了,我定在座位上,剛落幕的電影很快顯得偏遠,和安第斯山的亂石堆一樣陌生。
根據可靠的資料,聶魯達顯然是智利的傳奇,詩歌界的南美教主。
除此之外,他還飲酒、好色。
然而這大概和眾多的藝術家甚至人類作為整體沒有巨大的差別,我更想了解的,是一個完整的聶魯達,他的決定,他的任性,他怎麼就那麼大聲驕傲,而不是他飲酒作樂的影像而已。
這部電影的癥結在於,聶魯達的詩性和他的理性是斷裂的,政治任務和詩人兩個角色交替出現,卻很少重合。
這也許就是導演所理解的聶魯達,但若真是如此,這也是就是一個本身困惑,寫一手好詩的共產主義者罷了。
聶魯達在狹長的智利版圖上逃亡,動機當然是躲避抓捕,問題在於,他本人的決心來源和抓捕的熱度完全在影片中失真。
少數無足輕重的配角必須和我們發福的聶魯達互動,卻唯有建立在預設的“聶魯達寫的詩全國人民都喜歡,他真是我們的寶貝”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才會感到劇中人捍衛聶魯達的熱情,影片沒有解釋聶成為詩人的過程,他是已經風流的詩人,而我們好像必須嚥下這口氣。
好比不知道蝙蝠俠成長史的人看自然會困惑他怎麼那麼富裕。
一個英雄的誕生是需要扎實的劇情推動的,寥寥數筆描繪聶魯達作品受愛戴之深,戰士讀、上流讀、工人讀的群像是直白的風光本身。
智利出了個如此有號召力的詩人,這點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感動,但這種感動像是感受事件本身,並非多在乎熒幕上的聶魯達,就好像如果沒有照片,聽敦刻爾克大撤退也可以讓人覺得可歌可泣一樣。
在這種情緒之,Luis Gnecco的聶魯達完全叫人提不起興致,他像是一個偉大靈魂的載體,眼眸、臉皮、身子骨都太滯塞了。
可以詬病的還有不少,比如影片明顯採用Kodak 250D這類日光底片拍攝又不進行調色的操作是完全的干擾項。
如果一部電影需要用“紫羅蘭般溫情的畫面”來還原一個充滿戰鬥性的詩人的話,攝影部門顯然是有點黔驢技窮了。
過度的光線效果和對於淺景深的迷戀使電影本身變得不方便觀看,一切都太耀眼,人物互動常常處於一種不合時宜的輝煌氣氛里。
僅有一些對聶魯達的特寫是有效的,但剪輯又把持不住一刀下去,於是觀眾沒辦法看穿聶魯達私人的一面,這和今年早些時候《使女的故事》採用淺景深作為敘事元素的做法是有根本性的區別的。
當然,剪輯的弱勢在許多場景切換中也難以忽略,最後雪地追逐的詩意就經常被通俗、簡單的畫面扯得瑣碎,情節瑣碎地嘮叨了半天,還不如就讓奧斯卡在雪地裡一個人掙扎、囈語來得透徹。
導演的意圖了不得的明顯,他要還原詩人和群眾之間的互動,并以此塑造聶魯達和奧斯卡之間相殺相愛的故事(如果導演真的認為相愛相殺只有在警探和被抓者之間才能產生的話,真是就是在裝傻了)。
但聶魯達和奧斯卡都演得太生澀:聶魯達不願意演出來、剪輯師不給他演下去,奧斯卡又感覺太稚嫩、太無病呻吟,或者說,就是太演了。
奧斯卡這位電影毫無疑問的二號主角需要更強的性格。
到頭來,我不能理解一個瘦弱、文質彬彬、缺乏手段的探員會被總統指派追緝頭號通緝犯。
這是人設的問題,追緝聶魯達突破不了它,就成了不尷不尬、氣喘吁吁的影像詩。
8 ) 最喜欢他的这首诗
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戴着灰色贝雷帽,心绪平静。
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
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
你象藤枝偎依在我怀里,叶子倾听你缓慢安样的声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
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我欢乐的亲吻灼热地印上。
在船上瞭望天空。
从山岗远眺田野。
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旋舞。
(王永年 译)
9 ) Una poesía para Neruda
Puedo escribir los versos más tristes esta noche.Escribir por ejemplo, un niño perdido, un espíritu vacío, la niña pobre, la plaza y la montaña nevada.Escuché que el aire decía que sígueme, sígueme.Sueño contigo y sueñas conmigo.Yo te quise, y a veces tú también me quisiste.Nunca nos hemos encontrado, pero te reconozco.Por las letras, por tus poesías en el cielo, sobre la tierra.Escapa, escapa, voy a capturarte.Después de encontrarnos, cántame 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Te quiero preguntar, ¿quién soy yo?Un hijo de policía o un hijo de poeta.Como una página blanca, vengo a buscar mi huella.Quiero cazarte, pero al final, entró accidentalmente en tu laberinto.Camino por donde has pasado. Huelo tu olor, tu aroma en el viento.¿De donde vine?¿De tu poesía o de nada?¿A donde iré?¿A muerte o eternidad?Llámame, llámame el nombre.Me creaste, me completaste.El viaje siguiendo, pero tú serás solo.No, estoy contigo, para siempre.
10 ) 是聂鲁达书写了警察,还是人民书写了聂鲁达
是聂鲁达书写了警察,还是人民书写了聂鲁达不止两三位珠玉在前的大批评家们强调了聂鲁达的”幼稚“,论据是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另外就是强调电影里“没有什么政治,把聂鲁达换成一个摇滚明星也一样”云云。
这只能再一次证明德里克对中国的“后革命氛围”的准确刻画。
后革命的认识装置足以把所有大写的革命都给过滤在大脑之外,不仅可以用来改写中国历史,而且还保证脑袋里装了这种安全阀的人可以把一切“政治”与“政治”的对抗压抑进潜意识,表现为“政治”与“远离政治”的张力。
电影文本的核心其实就是“叙事”。
第一层叙事是聂鲁达如何叙述警官,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警官被“抓捕”了,被叙事彻底改写了,他最后一方面承认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警长的儿子”,一方面欣慰于自己被承认是故事里和聂鲁达一样的“主角”而非配角,含笑而去。
另一面是“党”以及党所象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叙述聂鲁达。
看起来,党员、人民和毕加索代表的国际左翼文化运动都只是聂鲁达诗歌的读者,是聂鲁达和警官猫鼠游戏的观众,尽管是明显倾向聂鲁达一方的观众。
聂鲁达写诗,传到他们手里,他们阅读,感动,聊以慰安自己。
但其实,聂鲁达才是这对关系中被动的一方。
这不仅是说,整个逃亡过程离不开党组织的谋划、安排乃至牺牲,也不仅是说,逃亡中聂鲁达一再受到人民的掩护(在妓院、在照相馆、在南部阿劳坎地区原住民的农场里),而是说,影片中,男妓、青年党员、中年女党员,以及国际左翼文化舞台上的毕加索,他们都对聂鲁达进行了“叙述”,就像聂鲁达对警察做的那样。
聂鲁达在电影里一再要求自己不要僭越为“主角”;一方面他确实有着强烈的这一自我戏剧化的冲动,他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追求逃亡过程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倾向随时被党的声音打断,不论是聚会上中年女党员对他特殊地位的揭露,还是保护他的明显有印第安血统的年轻党员说”你只是想要盛大的逃亡“,虽然他在当时都好像只是开个玩笑或沉默,但之后却都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和路线。
所以,警官最后的含笑而去,其实依然是一种”误认“,他以为得到了聂鲁达的承认,承认为”主角“,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主角“或主人公,也就是说,没有英雄(都是“hero”);因为真正的“英雄”,是党和它团结的人民。
让聂鲁达有力量的,不是他的诗本身,而是能静静地听他读诗的那“一万名工人”。
而只是追逐着聂鲁达,想得到他的承认,当然也就不可能真的抓住他。
这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翻转,重要的是,请看这场追捕的“观众们”在做出怎样的选择!
他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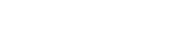























智利议员聂鲁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通缉,警察追捕,被聂鲁达的手下打死,聂鲁达安葬了他,然后逃到外国。
警察与罪犯的双向奔赴。
挺无趣的电影。除了后面半小时稍微好一点,全场都是那个警察的旁白,听的很烦。聂努达的生平也没有阐释多少。一部靠台词撑起来的电影,情节真的很弱。
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
佩卢恰努在物理上追捕聂鲁达,聂鲁达却在心理上追捕佩卢恰努。镜头和台词的文学及艺术表现升华了整部影片,虽然只从这部一直在造神电影中你并不能看出聂鲁达到底如何成神。一个诗人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分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结合:可怕的高傲态度、煽动能力以及本质的腐化堕落。
上课用
虚实结合
#69th Cannes#导演双周 一场极具诗意的追捕
这个剧情看的我不知所云
奥斯卡这不正是波拉尼奥最想成为的侦探诗人么!
詩人通過虛構創作假想(或真實)的追捕來論證文字的意念和迷惑性。更深一層,創作的動力是否都來源於政治的壓迫?導演似乎在鏡頭後面說,所有藝術都是不純的
6/10。四周布景的灯光使画面有种透明复古感,以黑色喜剧的乔装手法解构聂鲁达多面性格:在化妆舞会和妓院打扮成女性,最后戴大胡子变身阿道克船长、雪地骑着马终结了对手,开场在小便池与政客争论、被餐厅女招待质问享乐主义与共产信仰背离;伴随内心独白的碎剪叙述令人一头雾水,人物和故事毫无火花。 @2017-04-17 01:04:55
追捕者与逃亡者之间的关系形成美妙互文,如同诗句的韵脚在一次次扣响。
一首追逐暗恋的迷幻诗歌(伪)。再次深深体会到诗歌作品只有用原版语言唱诵才最好听。@cinematheque
不喜欢这种调调。片中呈现的女性身材真实这点挺好。
不错无感
文学与电影的诗意衔接,异色流动的人物传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近乎痴迷的追捕——那时候人们不追星,追的是拥有旷世才华、人格魅力的巨匠:聂鲁达、毕加索、爱因斯坦...最后15分钟逼格上天。
三星半。非传统传记片,而是走进聂鲁达的作品,他的精神,他的自大,他的愤怒。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重要,他无处不在,只要有人的地方,有反抗,有爱,有悲伤的夜晚。他的诗歌翱翔于天空,他的精神潜入大地,监牢,痛苦。悲惨世界式对照般的人物,他们互相追逐,互相观察,互相成就,互相书写
【台北金马影展展映】以诗意的方式拍摄诗人逃亡与被追捕的经过,而且身为追捕者的警察,要么是爱上了聂鲁达,要么是爱上了他的诗,要么是爱上了追捕聂鲁达的过程。总之故弄玄虚,神神叨叨。中间睡了好多次。结尾雪山上阳光打在镜头上的光斑太多了,反而破坏了流畅的摄影
虚构即真实